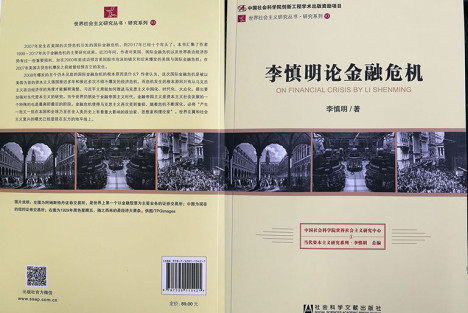廖子光谈经济危机:缩小两极分化进展甚微
廖子光谈经济危机:缩小两极分化进展甚微
【AC会客厅】廖子光谈金融危机(中文)
主持人:各位网友大家好,欢迎来到AC会客厅,我是本次会客的特约主持人,我叫简练,我们本次会客邀请的是著名的爱国侨领廖子光先生,廖子光先生是国际著名经济学家、金融专家,有着丰富的经验,我们欢迎廖先生的到来。
廖:谢谢,很高兴能有机会和大家谈谈。
主持人:好,由于廖先生长期以来与华尔街之间有所来往,所以我们本次会客欢迎他谈一谈这两年来金融危机的情况和最新的发展。好的,很高兴见到你,廖先生。
廖:谢谢。
主持人:大家都看到,金融危机已经持续2年了,自雷曼破产引发金融海啸也已经长达一年。我们这两年来也因此经历了非常多的大事,特别是最近一年。近几个月,国际金融形势也有了一些新的进展。所以我们很期待能听到您对未来局势可能发展的见解。
第一个问题也许和近两年来中国非常流行的一个观点有关,这个观点在美国已经流传了超过100年了,也就是崇拜金本位的思想(“金”龟子)。我们都知道有一位作者,叫宋鸿兵的,写了一本《货币战争》并且成为近两年来国内的畅销书,到今天为止他的观点和想法仍然在中国很受欢迎,很有影响力。你能否对此作一些评论呢,据我的了解,在您的作品中您是很反对这种思想的。
廖:这样,我更愿意先谈一谈我对目前世界金融-经济局势的看法,我倒不想去评论、批判其他的作者,因为读者他们会有自己的判断。
你可能记得2年前,我到北京的时候,(当时危机以次贷危机的形态爆发),我就指出这一金融危机不会是一个短期困难。当时很多人都认为在两年内就能完全复苏,现在事实也证明了他们的错误。其实,这场危机不可能在两年内复苏这一点结论其实是非常显而易见的——这是由过去十年间发生的事情决定的:美国通过爆发累计的债务,使得借贷消费和金融过度发展和膨胀。由于美国具有美元霸权的优势,所以他们能够以债务的方式“发行”制造出美元货币来购买他人制造的产品,而这些钱并不是他们通过生产东西挣过来的。所以美元本身就是一种债务,一种债务工具,形成债务泡沫。当这种债务泡沫累计到一定程度的时候就会破裂。在破裂之后,在通常的经济周期里,经济过度繁荣下的投机泡沫破裂,一般来说会进入萧条期,价格——消费品、资产品的价格会下降,人们会以更低的报酬方式多工作,然后再逐渐复苏,重新起飞。(过去通常来说政府货币政策如果此时放宽,能够加速这一复苏过程)根据这一通常的原理,目前的美国政策制定者认为,如果发生股灾、危机,那么他们要做的就是通过发行更多的货币来防止危机更加深重。这种想法看起来似乎有点像是凯恩斯主义,但其实上不能算。因为就正统的凯恩斯主义来说,需要政府在经济运行繁荣的时候能够有政府盈余,然后再在经济下行的时候将这些累计盈余主动的通过财政支出花出去,再加上一点赤字,把经济从底部给提振起来。
但是,过去20年的美国经济,在经济繁荣的时候是通过债务实现繁荣,无论私人或者公共均是赤字,所以政府持续的有财政赤字。所以其实政府的财政赤字本身也是美国债务泡沫的一部分,增加了债务泡沫。然后,到现在发生危机,美国政府想要转向凯恩斯主义来解决危机的时候,他们没有过去积累下来的财政盈余。所以,他们所做的,只是通过制造更多的债务来撑起开始破裂的债务泡沫。所以他们现在所做的,其实是把出现违约的私人债务转换成公共债务,途径其实是通过实际上的发行货币来认购这些坏帐,也就是扩张中央银行的资产负债表,把坏帐放进去。另一种方式是去购买那些被认为太大而不能破产的企业发行的新债券和新股的方式给这些企业“注资”。这样做的结果是用国家资本主义(state capitalism)来代替过去30年放任自由的市场资本主义(market capitalism)。当然,美国民间、智库的近30年来的主流观念一直是对国家资本主义口诛笔伐(批判“大政府”,赞同“小政府”),但最近两年来他们却事实上在走国家资本主义的道路。
国家资本主义在某些情况下,不是什么坏事。所有的经济体都在某种程度上算市场和政府共同参与的“混合经济”。但在美国,从传统的意识形态上,特别是最近30年,他们特别反对任何形态的“政府干预”。而且美国的很多活跃的思想库跑到全世界去宣传“小政府就是好政府”的意识形态。现在他们可以说是在扇自己的嘴巴,因为他们现在等于是公开承认放任自由的市场资本主义,特别是毫无约束的放任自由资本主义已经失败,而拯救者是政府,并非他们崇拜的“市场”。对于现在的中国来说,过去许多年,我们都屈从、跟随着美国的宣传压力、意识形态,去私有化我们的国有企业。到今天为止我们仍然在继续,特别是当美国开始国有化部分他们的企业,特别是所谓的超级巨型企业和重要企业的时候,我们还在继续私有化。所以我个人建议我们在中国要重新考虑考虑政策的意识方向。
当然,那些美国思想库的人,知道政府干预和他们的意识形态立场是完全相悖的,所以他们会反复强调:哦,这种政府干预只是暂时的,只是一种在紧急状态下的挽救。但就和怀孕一样,不可能“怀孕一半”就中止,或者搞“暂时的怀孕”,一怀孕就要怀到底。政府也是一样,政府进入市场很容易,要退出就相当困难——特别是在美国这种进入金融市场进行挽救的例子。
由于市场失败的原因是缺少政府对其进行调控规范,所以现在去解决这一失灵的办法,就是政府重新回来。不过现在即使如此,经济仍然没有复苏。现在周围所传言的“复苏”只不过是下滑的速度得到减缓而已。当然,他们(政客、央行行长、华尔街)可以说,哦,这是不错的消息嘛。所以这次在2009年9月份的G20伦敦财长会议上,美国财政部部长盖特纳说,我们这些政府,不但需要执行经济刺激方案,还应该要准备进行逐步退出经济刺激,至少要有一个计划,实现在经济一旦复苏的时候能够理解从经济刺激计划中撤离(因为根据传统理念如果经济复苏仍然在刺激-投放大量货币会引发通货膨胀)。
但问题在于,现在经济有所谓“复苏”(减缓衰退速度)的迹象,是因为政府插手干预,一旦政府抽手离开,经济又会濒临崩溃。所以这次在伦敦财长会议上,尽管所有参会国政府都同意政府的刺激干预应该有朝一日结束,但是他们都说现在不是结束刺激政策的时候。他们说应该要等到“资本市场交易更活跃、更复苏稳固”的时候再来撤离。不过我看市场(股市、债市)恐怕永远都回复不到一个足够让政府的刺激干预能够离开的水平——因为目前之所以市场有所稳固,正是因为你政府的干预,你的干预支持一停止它就崩塌。所以想让市场稳固而政府又撤离,其实已经是一个逻辑上的悖论。
既然知道政府难以撤离,那么他们为什么要一直谈论这套“逐渐停止公共干预刺激”的说法呢?因为如果他们不谈论“退出刺激计划”,那么这些国家的货币——以美元为首——就会崩溃。因为政府向经济体注入货币的时候,这些货币不是任何人通过生产产品挣来的(然后通过税收上缴),而是基于未来偿还的债券的(政府发行新债券,中央银行发行新货币购买之),当你在社会实物生产不变或者萎缩的时候注入更多的无中生有的货币,那么净结果很可能是通货膨胀,以及货币的贬值。所以他们陷入两难的境界,或者你硬着头皮经历货币贬值,或者你维持货币的价值,但是让经济继续下滑。为了应付这种两难局面,所以他们在搞“说一套,做一套”,向媒体传递一个欺骗性的信号:即,我们的确打算从市场中撤离退出经济刺激计划,但是要等到时机恰当的时候我们才会退出,所以,请你们不要在外汇市场和债券市场上卖空我们的货币,要对我们有信心和耐心。但现在经济的真实情况是,经济尚未复苏,而失业率持续新高,在美国已经超过10%——这只是一个总体的统计数据。如果具体到特定的人群(如黑人或某些地区、行业),失业率高达28%-30%。除此之外还有非常严重的“半失业”问题,也就是说那些仍然就业的人口,很多人的薪水被减半。因此,也就没有购买力来支撑经济。
此外,当政府给公司们援助送钱的时候,这些公司如此挣扎,仿佛“活死人”一样,为了公司的生存他们继续不断裁员。结果,在表面上他们仿佛重新回到“赚钱赢利”,但这种“赢利”是靠削减支持、裁员实现的,而且他们收入的钱其实是政府提供的营业外收入,而不是来自市场的主业收入。(主持人:政府送的免费午餐)。对。所以在我看来,他们被困在这种螺旋向下的恶性循环里了。除非他们的头脑、意识形态得到转变,弄明白解决问题的办法——也就是不是去送钱救公司,而是要把钱直接给贫困下层人民,创造消费需求——如果弄不明白这一点,危机就不会结束。
不过,不管危机按哪种局势发展——不过是你继续糊涂的送钱给公司还是明智的给老百姓,这场危机都要用5-7年才会有所扭转,因为经济体系里还有一大堆债务没有解决——这些债务大概要花那么长时间才能解决。而他们解决债务的时间拖得越长,经济萧条就会延迟多长。而这里的关键一点,就在于过去两年里面他们没有消化解决任何债务,他们做的所有事情只是将债务从私人部门变形到公共部门。所以黑暗的隧道尽头曙光未亮,更不要说长期的复苏了。
主持人:好的,廖教授,您已经提到了您关于经济危机的最近局势和所谓复苏的很多看法。我可否这样概括:目前美国的问题,包括欧洲特别是英国的问题,是一种“结构性的问题”。而这一问题的根源,来自于实体经济的空心化。他们不再像二战结束后的黄金年代那样有足够多的生产性的部门,许多普通人只能在商业渠道部门,比如像沃尔玛这种提供低薪工作的地方找到工作。他们很难再在制造、生产东西的企业里找到工作,所以他们消费的东西大量需要依赖于进口品。这也是为什么凯恩斯主义的刺激方法很难实施奏效的原因。或者说尽管他们自认为自己是凯恩斯主义者(最起码开始认为自己不再是新自由主义者),但事实上他们所做的只不过是简单的印钞票送给那些金融机构、金融公司。
廖:是的,他们其实是破产了的货币主义者,而不是(凯恩斯主义者)的赤字财政刺激。
主持人:所以,最近有一个事情在中国吸引了大家的眼球,就是轮胎特保案。奥巴马总统已经签署法令对从中国进口的轮胎征收特别加关税。中国官方对此作出了强烈的反应,说:奥巴马总统,你“走错了道路”,“你在走向贸易保护主义”。从这种措辞看来好像贸易保护主义是一个“坏东西”,特别在这些年来的国际论坛上都是如此,在中国媒体的宣传里也是如此。您能否对此谈一些您的想法,以及谈一下在经济史上贸易保护主义曾经扮演的角色。
廖:好的,贸易保护主义是一个帽子,它最早诞生于18世纪末英国国内反对重商主义的一次亲自由贸易的思潮运动(即亚当斯密为典型)。重商主义是对那个时候争夺贵金属的贸易政策的一种描绘。当时每个欧洲国家在其国际贸易中都力图实现以黄金为实现形式的贸易盈余,黄金是当时世界通行的货币。对于大英帝国尤其如此,他们向国外出口工业纺织制品,(从欧洲大陆和美国)进口农产品,同期卖得多买的少,就实现黄金形式的贸易盈余,他们得到的黄金越多,他们就越“富”因为当时的环境下黄金不会丧失价值。他们用这些黄金来采购、制造设备,建造更多的工厂,雇用更多的人,推动技术的进步,然后进口更多的农产品。所以,亚当斯密说,重商主义其实并不好,因为这样长期以往,黄金越来越多,最后物价会上涨。但亚当斯密的有些话被误读了——有些人把他说成是反对任何政府的干预,其实亚当斯密并没有说不应该有政府干预,他说的几乎相反:政府需要干预以反对重商主义。
在这套思潮流行后,出现了德国的经济学家弗里德里希·李斯特,他检查了亚当斯密的思想,说自由贸易不是普世真理,只是对于英国有利的一种政策思想、一套国家策略。英国之所以鼓吹自由贸易是因为自由贸易对大英帝国有利。对于德国来说,由于我们处于经济不发达的落后状态,唯一能够抵御大英帝国当时锋芒正茂的经济扩张帝国主义的办法,就是执行贸易保护。因为如果你在对方的尖锐攻势下不保护自己的幼稚萌芽阶段的工业的话,你就永远不可能成长起来。这可是有历史数字支撑的,为德国在19世纪早期的经历所证明。弗里德里希·李斯特不赞同自由贸易(free trade),他谈论更多的,可以算今天所说的公平贸易(fair trade),通过国家保护主义来实现的公平贸易。弗里德里希·李斯特深深影响了孙中山,三民主义政纲里有大量李斯特的遗产。当美国最早以强大经济的面貌出现的时候(南北战争结束后,19世纪后半期),他们大肆贯彻了所谓的保护主义。直到二战后,由于美国已经取代了大英帝国的地位,他们就取代了大英帝国,成为自由贸易的鼓吹者并跑到全世界去推行。但他们干的更糟糕。因为大英帝国至少是在金本位基础上的自由贸易,(你有实力才能获取黄金这个货币),而美国则是从1971年起在纯粹法币(他们自己发行的法币)的基础上去搞自由贸易。当然,在二战后,美国就开始在布雷顿森林体系下鼓吹自由贸易了,不过布雷顿森林体系还是建立在和黄金挂钩的美元基础上的。到1971年,由于美国之外已经流通、持有了那么多的美元,法国、英国就开始要求将这些海外美元向美联储兑换成黄金,于是尼克松就中止了美元和黄金的挂钩,因为美国已经没有足够多的黄金了。
今天所发生的一切,在克林顿时期的财长罗伯特·鲁宾曾经道破天机。他曾是高盛的一个债券交易员。他搞出一套办法,使得美国可以持续产生贸易赤字,但却以纸币白条来支付。当时(90年代前半期),这些纸币还有点价值,相对稳定,因为美国在地缘政治上还很强大。拿石油这个典型例子,自从1973年以后,美国以石油以美元标价为条件接受容忍了石油输出国组织欧佩克的存在。而当石油用美元标价的时候,事实上美国拥有了全世界的原油——我们可以用纸来换你的原油。而这些美元纸在世界任何地方都无法大量使用——因为如果你在任何其他国家花费,你首先要将美元兑换成当地的货币。而如果你真的那样做(将向美国出口所得到的美元换成本国的新货币使用,同时国内生产规模不变),那么你将发生通货膨胀——因为你的当地货币背后的“真实财富”送给美国消耗掉了。这就是我所说的美元霸权:因为你向美国出口,得到的以美元形态的外贸盈余越多,那么你就越需要将美元送回美国,去支持他们的经济,为他们的经济融资。
当世界进入这个阶段的时候,就出现了全球债务泡沫。于是美国说,很好,这对我们是很有利的安排。于是他们不仅鼓励外国去通过贸易盈余来积累美国国债(美国联邦政府成为债务制造者),而且他们开始推动他们自己的人民也开始借债来买房买车——从日本进口小汽车,从中国进口家具、日常消费品,银行不管你是否有收入都让你借钱,所以,在十年内这个泡沫就破裂了。格林斯潘下的美联储不断去增发越来越多的货币。格林斯潘的一句名言就是如果你要制止一场泡沫崩盘,特别是在泡沫破裂后进行拯救,那么你要制造另一场泡沫。所以每次,每十年一次泡沫破裂的时候,他都注入更多的货币,但他这样做的结果是让问题越来越严重,问题的规模越来越大。2007年夏天,一些像我这样的经济学者都已经预见到又一场泡沫的破裂已经不可避免,而另一些主流经济学家则说不要担心崩盘,中央银行会出手相助的。不过最后还是破裂了。而中央银行也不可能反复过多的出面拯救——否则人们会对你丧失信心,你的信赖度会受损。
所以当08年9月雷曼兄弟破产的时候,当时的财长亨利·保尔森说:让它破产去好了。从他们一贯的自由放任的意识形态上来说,这种表态是站对位置了。但是在此前美林遭遇大麻烦的时候,他(让美国银行出面)拯救了美林,就被保守派猛烈的抨击。所以他在雷曼的案子上说:OK,我接受大家的批评,让雷曼自由落体。但雷曼破产的冲击波是全球性的,如果你仔细读过我写在我个人网站上的文章的话就会知道--现在没有时间深入讨论了。这个冲击剧烈到冻结了全球金融资本市场流动、运转的地步。所以此后,当AIG集团和其他大银行比如花旗集团、美国银行出问题的时候,政府都出面拯救了。他们所做的就是拯救这些公司,防止他们重蹈雷曼覆辙。但很显然,现在来看,拯救的代价极其高昂。而且有让美国联邦政府财政出现周转危机的可能性,或者至少让金融危机延续很多很多年。
主持人:所以,在廖老先生看来,首先,保护主义是一个中性词汇,因为它在历史上为幼稚工业的成长起到了护航的作用。另外您也提到了今天美国陷入的很多困境。我仍然想询问一下奥巴马保护主义政策的有效性,因为从目前局势来看,奥巴马在贸易上的保护方针很可能会继续乃至扩大。我在美国的一些朋友说,也许保护主义政策能够真的让美国“重建”实体经济,实际的大众生产能力,还有创新能力。当然另外一些我的朋友则说这种期盼是徒劳的,因为现在很多美国人都变得很懒,他们也不想费脑子去学习接受工科技术类教育,只想去读商学院。你对此有何看法?
廖:这个问题相当复杂。但首先,在美国,特别是主流民意,仍然有很多人认为世界贸易对所有人都有利,特别对美国有利因为他们自信“美国是世界上最强健的经济”。这种大众思想,其实很大程度上来自于弗里德曼,米尔顿·弗里德曼,他在里根执政的80年代特别流行,向大众灌输了这套理念。
在1929年的股市大崩盘爆发后,我们经历了一个大萧条。这个大萧条最后是通过二战的军需拉了出来。弗里德曼,在战后搞了一个非常冗长的研究,然后写了一本很有名的书,叫做《美国货币史》,他的结论是如果当时美联储这个中央银行能够更加积极及时地采取货币扩张政策,那么大萧条就能够被制止。这种结论叫做“无事实依据的结论”,我叫它“虚拟结论”、“无依据结论”。你无法证明它是正确的还是错误的。因为历史只有一次,历史的事实是大萧条是为二战军需所拯救的——但弗里德曼只要说“如果……那么……”就完事,这种话和“如果耶稣没有诞生那么就没有基督教”这样的废话一样无意义,我们不知道其真假因为历史从来没这样发生过。这种“无依据结论”相当危险,(对社会)具有非常大的潜在破坏力。所以上述是弗里德曼的“无依据结论”之一。弗里德曼提到的另外一个东西,是说大萧条的原因是世界贸易在当时保护主义和贸易战下的中断,这又是一个“无依据结论”。因为我们不可能知晓其是否是对的,因为战争后来就爆发了,我们不可能知道,也永远不可能知道,如果大战在1940年没有爆发,简单的“重启”世界贸易能否挽救经济。我们只能说,理论上说,也许可以。
第三个弗里德曼很危险的“无依据结论”是中央银行有能力去阻止萧条的继续,这又是“无依据”的。就好像说如果斯大林没有死,俄国的面貌就会不一样一样——这可能是真的也可能是假的因为我们无从认证。我不晓得在汉语里“counter-factual conclusion”对应的准确翻译是什么,但是我们中国人要明白这是一个很重要的概念。很多知识分子制造的理念,正是因为陷到这里面去所以走向了危险的方向。所以弗里德曼的这三个“无依据结论”就变成了美国主流民意的智力基础。在这场危机里他们做了三件事情:第一件就是他们让中央银行“猛烈的干预”;第二件事情是他们继续大肆鼓吹世界自由贸易以防止贸易停顿;第三件事情是呼吁所谓的“国际合作”——大家要站在一起。这又是一个“无依据结论”。在萧条里就是有些国家要比另一些国家结局好一点。我们并不都是一起往下沉的。所以上次希拉里跑到北京来,告诉我们中国人“我们在同一条船上”,这相当荒谬,我们根本不在同一条船上,我们在不同的船上!可能我们在同一个惊涛骇浪里面共同颠簸,但他们的船比我们的船沉的更快。所以如果我们在现在的经济环境上,通过国际贸易使得相互之间的联系更加密切,那么我们恐怕是把自己弄得更加依赖于美国的需求,更危险。在这种意义上,我们减少对外的依赖其实将拯救我们自己。如果我们在这个时候还在金融方面完全打开市场,我们会陷入更加可怕的境地。所以中国的那些希望、鼓吹金融开放的先生们必须站出来回答这个问题,回答他们的错误——事实和他们当年的主张相悖,这已经不是一个理论争论了。回到轮胎特保案上,这是一个小问题,但却是一个具有标志意义的问题——如果他们在轮胎上能够这样干,那么就意味着在所有事情上都可能这么干。
美国在与外国的外交关系的操作上,比我们聪明、先进的多。他们搞出这么个阵势:政府出面说我们想和你中国政府建立很好很好的关系,但是因为他们有“国内政治争论、议题”,而这些“议题”“阻止”了他们政府去采取他们本来会去采取的“友好”“自由贸易”立场。所以,这就不能算他美国政府的错了,这只能算是“美国政治的属性”天然决定了这种“遗憾的事情”。所以中国政府每次都说“是,是,是”,“我们明白、理解”,我们要做出一些让步让你们的国内人民更加满意……而我国,由于中国传统的原因,我国的政府总是表现出一幅“全国人民都100%完全无条件支持政府”的姿态,结果我们就丧失了选择的能力,这其实是一种劣势。每次我们做一些他们不喜欢的事情的时候,就变成了“中国政府的过错”,没有缓冲啊!我们应该做的,是给美国政府说,我们的用心是非常友好和体谅的,但是我们的国内政治议题有诸多不同意见,其中有些意见不允许我们做某些事情,很遗憾,你要知道,如果我们强行推进,那么我们政府官员会丢掉饭碗。但我们就是不懂得玩这种牌,这也是为什么每次我们都在谈判中失利的原因。我向我在外交部的朋友建议:他们应该认真考虑、研制这种策略,好让我们在外交布局上能够获得优势。
所以,现在,世界经济的实际问题,基本问题,是放任市场经济,或者说放任市场资本主义,无法实现财富的合理分配和收入的公平——在哪里都是这样。在中国更明显,因为我们是从一个社会主义国家作为名义起点开始改革的,而作为一个社会主义国家,理应的主要目的是实现公平、大同。但由于为了参与全球化经济,我们在这一点上做了让步。当邓小平最早启动经济改革的时候,他的立场是“让有些人先富起来”现在我们有一些人,想把“让某些人先富起来”中的“先”字去掉,变成“让某些人富起来”。所以我们现在如果不当,就会制造出一个乃至回走向革命的社会局势。所以我们的“和谐国家、稳定社会”不可能建立在不公平的基础上,这两者是基本的对立。现在中央政府、党中央不是不明白这一点,他们在尽力进行制度性的纠正、调整,比如有很多项目和政策。但是有一些人,通过过去30年,形成了既得的立场、地位,而且在目前分配不公平的社会中具有十分有利的地位,他们有权、有办法,有力量、有“理论”来为他们的这些既得利益辩护。但事实和局势发展都在不断敲打他们,因为只有中国把财富、收入的分配公平作为发展目标而不是仅仅一个副产品的时候,中国经济才可能得到真正的发展。如果不这样,我们不可能复苏。我们可能会在这种不利的经济局面中维持10年、20年。
在这其中,党很重要。我个人不是共产党员,但我会说党很重要,因为需要有一个组织出来代表人民行动。人民确定国家的目标和方向。在美国,有共和党民主党,但他们其实本质上是一个党,一个党两个分支而已(例如民主党克林顿其实是有史以来最好的“共和党员”)。他们的党实质上是代表了各类富人和精英阶层的。而我们的党——我们曾经有另外一个党,国民党,这个国民党镇压了自己的左翼,成了一个代表富人、权贵的党。历史已经告诉我们结局如何。
但目前来说,我们的党,至少从其章程、意识形态起源来说,还是一个致力于公平、建设为全民幸福而奋斗的党。但我们的政策,经常与此原则相矛盾。举一些例子,我们已经谈了非常非常多年,开了非常非常多的大会,都在谈如何去缩小财富、收入的不平衡,但在这一点上好像我们进展甚微。如果说这种不公平、贫富分化的现象还是一个“理论争议问题”的话,现在都成了活生生的经济现实问题、麻烦了。如果我们不去提高人民的工资水平,收入水平,如果我们不去实现全民就业,我们的经济——因为我们的经济结构被搞成高度依赖于出口,就会崩溃。也就是说,我们的政策,将经济结构从过渡依赖于外需——出口占GDP70%的结构转变为内需为主的政策效果,永远不会实现,除非我们的人民有收入,大家都有购买力。而我国现有的经济结构,总体说来,只有很少很少的财富,向下“渗透”到了人民大众的手里。你可以看看北京,这周围全都是高高漂亮的公寓高楼——就是人民大众中没有什么人能够真正买得起,全都是外国人或者投机者在购买。
主持人:是的,很多晚上都是黑不溜秋的,你都看不见灯。
廖:对,所以这些漂亮公寓有什么意义呢——如果人民买不起,住不起有什么意义呢?所以,实现社会公平的经济政策,已经从一种意识形态上的信念,变成了一个必须的经济必要条件。两年前,当我们讨论此类事情的时候,好像还是一个“理论探讨”。今天,现实数字已经冷冰冰的驳倒了那些新自由主义者。但他们还在硬拗。两年前我在这里的时候,我参加过一个研讨会,不少中国金融机构里的基金经理说什么这场危机会在两年内结束,世界上什么都不会改变,我那个时候点出来——当然我不是针对某个个人,我说中国有一群人,这群人总是说什么两年内危机结束,这些人真实的目的是在两年内捞到足够的巨额收入然后拜拜退休——等两年后经济就算没有起色,那也不是这群自私者的问题了——那是国家的问题。
主持人:很好,这真是对政策和危机应对办法的精彩评论。下面让我们谈谈有关人民币的话题。我记得我们上次见面的时候,您提出了一个解决贸易问题,也就是所谓中美之间贸易不平衡问题的办法,那个问题当时已经很严重了。很快泡沫就破裂,雷曼就破产。您当时提出来的建议是贸易的人民币结算,也就是与中国外贸时启动人民币清算系统。
接下来,我们就见到这项政策在您提议的几个月后就开始启动。从2008年底到2009年初启动了。不过我注意到在中国媒体上,一些学者开始把这点提法转变成了“人民币国际化”,而且他们进一步提出,OK,如果你需要人民币国际化,我们就需要人民币汇率自由浮动,人民币与外币在任何领域的自由兑换,你可以在任何时间,把任何数量的人民币换成任何的外币,在贸易帐户和金融资本帐户上都是如此,您对此有何评价?
廖:我所提议的建议,原文的意思是:在现有的国际贸易条件下,用我们的过量出口换来的美元其实从本质上来说是没有用的,这一点显而易见。所以,我的建议是我们的出口要对方支付人民币进行结算(而且这个人民币不能是他们到我们这里简单兑换得到的,而必须是他们向我们的出口挣来的)。我已经反复强调过,这并不是说我在鼓吹所谓的人民币国际化。我仅仅是主张在和中国有关的双边贸易中,中国方面只接受人民币作为出口的支付、清算货币。对于那些和中国无关的贸易,尽管让他们使用美元或其他任何他们愿意使用的货币。因为,如果我们让发生在与中国无关的两个国家之间的贸易使用人民币结算,目前的条件下既会带来风险,也没有必要。首先,我们的经济虽然说增长很快,但目前在全球GDP中的比例还不能算特别的大,美国的GDP占了全球GDP的大约35%。所以,直到中国的经济的全球比例份额也达到类似的程度,在此之前简单的认为人民币成为国际政府(央行)外汇储备币种,基本上是奢望。
假设,你在自身力量不够强大的情况下,去让你的货币走所谓的国际化路线(不仅指作为任意的国际结算货币,更意味着货币自由兑换,成为国际货币汇率市场上的一类金融游戏币种),那么你就将把自己暴露在金融投机和攻击的枪口下面,而对此你又无力去面对。如果这样做,就会和日本一样,日元,很大程度上可以被纽约的金融玩家所拨弄影响操控。这也是为什么在过去的15年里日本经济一直垂死挣扎在向下螺旋下降的恶性循环中——这是其中的主要原因之一。相比之下欧盟的情况略有不同,稍好但有问题。欧盟加起来和美国的经济规模相似,甚或更大一点——特别是在目前美国经济在衰退的情况下。但欧盟有一大劣势,那就是它是一个仅有货币统一但政治不统一的经济体。所以欧元也不够格成为基础的国际货币。所以,如果我们不接受美元的话,就没有其它候选的国际货币,这也是为什么尽管美元在不断贬值,但仍然是国际储备货币的原因。但我们可以在美元圈之外来主导我们的对外贸易。在某些情况下,我们还需要美元,但在出口问题上,我们不需要依赖美元(继续接受美元作为出口支付),事实上如果能够将其转变为主要以人民币进行那将成为我们一大优势。如果能够实现这一点,那么我们就可以和更多的国家进行贸易,扩大规模。有些国家和我们之间现有贸易额很小,主要原因是他们没有美元来买我们的东西。如果人民币能够主导我们和他们之间的贸易,那么我们就可以用人民币来购买它的资源如石油。那么能很快给我们带来优势。因为只要我们让人民富裕起来而不是仅让某些企业富裕起来,那么在不远的未来中国可能会是世界第一大消费经济体。那个时候,在国际贸易中,例如自然资源,我们将会是世界的主要购买者。在市场交易里面,主要有两个主体:生产者(卖家)和消费者(买家)。当某个消费方在市场中占有的比例足够大的时候,他就拥有了驾驭市场的能力。当然这也是历史上操纵价格和对应进行管制的由来。如果你这个购买方足够大,你有市场力量,你事实上可以裁定、制定价格——因为如果你生产者不卖给我,那么无人买你的产品,你的卖价实际为0。所以你还是要卖给我,至少能换得某些东西。值得指出的是,近来我们中国有一个政策,鼓励我们的企业走出去,使用那些过剩的无处可花的外汇储备去购买外国的资源型企业。在表面上看来这似乎是一个非常理想的政策方向。但如果你仔细想想我刚才所说的对市场的分析(主要两类人,一个买家一个卖家等),如果我们最终真的成为这些资源生产企业的所有者,那么我们内部自己就出现分歧了:某些中国人会更倾向于资源价格走高一些,有些中国人则会更倾向于资源价格走低一些,谁会赢得国家的政策倾斜?好吧,那么就看这两拨人在国内政治较量了,这就成了一个政治问题。但这是本可以避免的政治问题——我们为什么一定要拥有这些外国资源性企业呢?当然于是会有人说出于国家安全的考虑我们应该去掌握拥有他们,因为我们需要安全。好吧,如果我们真想实现这一点,那么除了拥有这些企业的所有权以外,我国还需要一个具有强大的军事力量投放能力的远洋海军。目前而言我们并没有这样的海军,而且似乎也没有未来建设拥有这样的海军的计划。而如果你在中东拥有油田,而又如同二战中的日本那样受困于他人之手无法将南洋印度尼西亚的原油运回本土,那么你的所有权也就没有任何意义了。
此外,我们和外国贸易的目的,是通过贸易,老老实实支付自然资源的合理价格,我们不打算去占有它们,因为占有它们是一种帝国主义传统的做法。当年,外国资本跑到我们的土地上,收购我们的资源,我们很愤怒,今天如果同样的事情发生在那些第三世界国家里面,为什么他们就要欢迎我们呢?这也是为什么在世界上,已经有美国人在批判我们,说,你们和我们其实一样,也都是帝国主义嘛。所以我们应该再考虑、三思这种收购海外资源公司的政策。当我们需要自然资源的时候,我们只要保障能用合理价格支付得到即可。而得到资源后我们的获利,是在于将这些资源经过我们的加工,成为带上附加值的产品,而资源出口国也相应得益,因为他们可以用出口资源得到的人民币向我们购买我们的价值附加值产品,比如电视什么的。
主持人:也许这里还有一个因素可能要加上去。在自然资源、商品市场上,不仅有消费者和生产者,还有渠道者、中间交易者,特别是在成熟的国际商品市场上,据我所知,国际商品市场常常着落于纽约芝加哥和伦敦。这些地方制造了资源产品价格的大部分波动。而就我所知道的,在80年代以前,对自然资源产品的交易买卖机制还不是这样的,那个时候主导地位的是生产者直接和消费者或商业渠道者之间的长期合同,但到80年代以后,随着金融市场的自由化,带来了更多剧烈的波动。
廖:这种局面只有在这些中介交易者能够控制市场的时候才是存在的,这也是为什么国际商品市场会变化到落到这些人手里的原因。但国际商品市场变成这样子以后,对于国际经济的健康就相当有害了,甚至在美国,有关部门也已经开始对前一阵剧烈卖空石油的投机者进行调查。但即使伦敦和芝加哥的国际商品交易所继续存在,我们中国也可以通过和生产国发展长期合同来规避他们,只要我们越来越大而影响力扩大,那么这些国际商品市场上交易的实际商品数量会越来越小,比方说到90%的商品都不是通过这些交易所交易的时候,(那么他们的影响力就消失了)。这是一种解决办法。当然这是一个非常复杂的道路,因为你不可能在一夜之间改变这么多年形成的交易所结构。国际交易所、金融市场的确扮演过一定的正面作用,但如今,英国官方通过调查认为,英国的金融市场——伦敦城过大,事实上有违英国的国家利益,因此需要进行限制。而在我们这里,却打算继续把上海和深圳交易所扩大。我们恐怕要对此三思。
主持人:您是说对目前中国在这方面的方向进行再考虑?
廖:是的。
主持人:让我们再谈谈其他一些金融市场之外的东西。和中国未来的发展道路有关。一个话题是最近中国日益兴起的思潮,就是中国应该转变“中国制造,外资生产”,比如说苹果的iPhone(加州设计,台资鸿海组装)变成“中国创造”,您对此有什么看法?
廖:很好!这很重要,因为这种转变不仅是中国未来最好的出路,而且也是唯一的出路。当然,在某些限度内,我们应当欢迎苹果进入中国,因为他们在这里,通过合作,尽管其创新和设计还在美国,但我们会获得某些好处——但要记住这不是说我们就依赖于他们去创新了,我们自己就不需要创新了。我们需要自己创新,并和iPhone竞争(如魅族M8),当然,只有在摸清iPhone构造后才可能进行创造,并与之竞争。
除此之外,从政策整体上来讲,应当限制外资公司进入中国,但我们应当高度欢迎外国的人才、团队以个人加盟、合作身份到我国工作、创造。这两者之间有重大差别。我上次说过,国内有些专家,无论左右,持一种所谓“国际主义”的观点来看待资本。这种看法说资本就是资本,它是外国的还是本国的没有关系。这是不正确的。国内资本至少能够明白:如果你给员工、工人的报酬高,那么他们就会有钱,有购买力来买你的产品——这种想法叫福特主义,福特汽车创始人亨利·福特发明的,这种想法很好。而对于外国资本来说,因为他们的产品在国外销售,所以他们没有动力去增加你国内在其生产线工作的工作人员的工资,因此你就没有购买力,反过来也和他们不会有购买生意关系,所以他们更依赖于在美国的销售——这些外资企业甚至在美国,在过去多年里也拒绝提高美国国内的工资水平,所以他们在你国内肯定是要压制收入提高的。所以说,资本是不同的。这也是我要反对外资进入中国的原因。这不是出于什么情感,而是因为外资,从本性结构上来说,不会支持提高中国人民的收入水平。
主持人:把你当成一个成本来处理,而不是主动把你当成购买力。
廖:在这一点上,很多人,特别是那些新自由主义者,只懂得一知半解,非常危险。他们只知道关于资本的某些非政治方面的属性,但是如果深入看待资本,特别是深入到政治层面,你就知道,贸易、货币都是政治产物。
主持人:好的。那么下一个话题我们谈谈气候变化问题。
廖:等等,在我们谈气候之前,我还想多谈一点东西。因为你提到了我们在中国未来应该走的方向。我在新华网上曾经提过,政府要明白财富分配不平等的害处。我们有(宪法里写的)政治权利上的平等,但是却没有经济权利上的平等。造成这个局面的原因倒不是政府不在乎,其原因是很深层次、结构性的:因为过去几十年的发展,由于搞了所谓的经济的金融证券化,让我们从简单的市场经济进入了金融市场经济,(很多人通过企业上市证券化一夜暴富)。在这个体系下,那些没有能力,没有政治权利去组织资本的个人和组织,将成为社会的受损人群,输家。我们搞革命,是反对资本主义。所谓资本主义,就是一小撮人控制了资本去剥削大部分没有能力获得资本的人民——即使这些资本本来属于人民。很多人在这一点上没有弄清楚:革命是反资本主义,不是反资本,资本是生产工具,是好的,是大家需要的,任何社会体系运转都需要的。过去三十年搞了开放,结果,我们允许出现控制大量资本的金融机构。那么在这种体系下,从世界各国经验来看,都是从人民中吸收资本,再让人民对其银行产生依赖,每年存款获得2%的利息,然后银行拿着这些资本,去进行管理,投资,然后获得50%的回报,将其中2%给人民,自己留下48%的回报,复合增长迅速……(这里廖老似乎有错误,50%为资本收益率而不是利率,和2%不是同一个概念)
所以我所思考的解决办法,是主张倡导一项发展模式,我叫他“人民金融公社”(类似于农村合作金融协会等等赋予本地农民更多资金渠道扶持的组织)。过去,我们出现过的人民公社搞的是生产。而目前从生产上来说,我们在很多方面是世界最大的生产者,但在金融管理方面,可以说还处于“封建社会”阶段。举例来说,人们没有通道、技能去管理自己的经济。比如说一个小村庄里的农民,到最近的工商银行网点可能要来回花费4个小时。而即使你到了工商银行,他们也会说你没有自己的资本(主要是你没有很多自己的现金),所以不能贷款给你。而我们的政府虽然嘴上说要实现财富平等,但走得是美国人宣传的“财富慢慢渗透”的“涓滴效应”路线(即富人富裕了会带动穷人生活水平上升)——我告诉你,这套“渗透”永远不会发生!
所以我所推荐的方案,使一个能够让人民获得自己资本的政府机构:比如说任何的农村,都有土地,都有人力,如果能够获得资本的话,就能够从事实业,搞生产搞发展。现在这些人存在银行的钱,通过金融中介都流到大城市里去了(银行倾向于贷款给城市、富裕地区而非农村等需要发展的地区)。你可以说这些农村人不知道怎么经营,不错,但目前他们缺少这方面能力正是因为政府没有给他们权利、机会让他们去操作。而我们有很多经营人才,有技术,有能力,但他们的才能现在被外资或合资公司利用。我们应当组织这些人才回来,和农村结合,但不是回到农村去当农民,而是当组织管理者,人民的组织管理者。人民是主人,这些人为其工作。
问题在于目前的社会情况下这套想法不可能实现。所以我们需要积极推动国家政策来促动,推动。如果能够实现这套体制,我向你保证,社会的财富鸿沟会很快缩小,而我保证你中国经济会非常迅速的发展。目前来说我们有很多闲散资本,因为银行只要支付你2%的利息,所以他们不需要很努力的工作来推动项目让资本增值。但如果资本是人民所拥有的,他们会很快很有激励的去为当地创造财富。举个现有的例子,现在上海陆家嘴的工商银行,可能对他周边50公里外的农村一点概念都没有,自然不可能去解决当地的需要。我希望中国的知识分子,如果他们能够了解我的建议,能够参与讨论和改进,然后敦促政府去采纳。这很关键,如果我们采纳了这个政策,很多问题都迎刃而解。
主持人:好那么在我们谈气候话题之前,我想就廖先生所提到的这个设想多问一点。您刚才提到了您设想的人民金融公社,其功能在于为农民提供生产型的资本(生产工具和资金)。
廖:是的,这是他们自己的资金。
主持人:所以这些资金他们能够发展自己的小型产业,而不是需要跑到珠三角去打工。这是很好的想法,在其他国家也有类似的设想,比如说……您能否就您自己的设想和他们的做法作一个对比?
廖:是的,世界上有一些类似的做法和制度,但没有哪一项和我的完全一致。
主持人:在规模上无法对比?
廖:在美国有农民合作社,合作银行。在那里当地农民聚合在一起,然后以合作组织出面向银行贷款,这样他们创造了本地合作一级的金融机构,并通过其融来的钱来相互帮助、调剂。如果你研究一下美国进步主义运动的历史(美国19世纪末起由小农为主发起的运动,针对当时美国工业化的社会矛盾各方面都提出了主张,带有社会公平色彩),里面有很多此类的政策主张。我个人也被邀请去参与一个叫富兰克林·罗斯福基金会的组织,在里面出任“思想者”,这个组织主要是在美国再推动罗斯福式的新政。所以在罗斯福总统的新政中,有很多类似的想法。当然,在美国这些想法表现的形式有所不同,因为美国在意识上是一个基督教国家,所以要在宗教概念的衣钵下去推动带有社会主义性质的想法来让社会更公平——当时美国到了如果社会不进行公平压缩就要完蛋的地步。但在我们中国,既然中国革命的目标就是要建立一个社会主义社会,所以我们是名正言顺,更容易,更应当去回归我们原本的诉求。历史上人民公社失败的原因很复杂,很多也与当时美国的禁运如化肥禁运有关。当美国进行物资和技术禁运的时候,中国又处于很低级的物质生产阶段,自然就无法启动。所以这种公平发展经济的想法无法实现,因为你在公平化财富的前提是你必须先创造出财富来才能搞分配分享。这也是邓小平的本意,本意很好。但现在的问题是在创造财富的过程中,我们国家又出现了一套阻碍财富分配的社会结构。
主持人:所以也许我们在发展过程中应当参考参考日本的经验,日本搞了各种合作银行,在工业和农业领域都有。
廖:是的,但是仍然陷于一定的范围之内。我看我们应当不要去搞什么“学习他国经验”,而应当重点创造自己特色的制度。就日本作例子,因为它比较小,所以他们就需要搞集中(日本的机构特点:集中巨大)。而我们国家很大,有这么多人,你搞集中控制,权力集中,很可能会损害我们自己,损害超过好处。举个例子,光广东一省,人口就已经超过德国,如果我们光集中统筹广东一省,就超过柏林把自己德国建成一个大组织的规模。而如果我们想把各类统筹都集中到北京,那根本没有可能。如果你研究研究中国的政治历史,你就知道我们的组织从来是一个松散的网络,只是在某些重大问题上的决定权集中在首都,这也是为什么我说党很重要的原因,因为党是要确定经济活动的大概方向。现在美国和欧洲执政者自己明白某些方面的经济增长(比如泡沫)其实对于本国是有害的,但是他们没有能力去阻止它,因为市场是支配性的。而在中国我们尚有党,当然,中国有人希望党从经济路线中完全撤出,我个人持很不同的观点,我认为党应当制定经济的方向,当然,在同时,给予它们激励创造、自由的活力。
主持人:好的,让我们进入最后一个问题,就是即将举行的哥本哈根气候高峰会,近来这个成为热门话题。特别是在匹兹堡G20会议上。最近中国媒体上也在流传一个词语,叫做低碳政治。有些学者主张我们应该积极效应,跟随欧洲乃至美国。比如说,清华大学的学者胡鞍钢教授。另外一些学者,特别是那些不在学术机构里的学者,则认为我们在这方面应该有所谨慎,甚至有些人认为可能是一个阴谋。另外有些中国官员说在2050年以前我们没有能力减排温室气体,您在这方面观点如何?
廖:对于胡教授我因为不知道他具体的观点,但我总体认为应该分开看。首先,在这东西里面有大量的所谓“环保投资”的利益。有许多人说这些投资、产业能够帮助我们从金融危机中摆脱出来。我看这好比用一个大象用鼻子喷水来清理你的卫生间——很不恰当。气候问题是非常长期的问题,光要获得对这个问题的一致意见就需要2-3年的时间。所以对于气候的关注对于摆脱危机没有什么帮助和影响。
其次,如果我们因为哥本哈根协议的关注,就过快、过大规模的投入到气候改善的投资里面,那么可能今后数年内就会迎来大量的企业破产。因为我经历过70年代那场新能源投资热(始于1973年石油危机)。当时石油进口价格暴涨,他们就说既然石油价格从5美元上升到了30美元一桶,那么我们就应当发展替代性能源。问题在于你要保持替代性能源的健康发展的话,你就必须将石油保持在高位——当时高于30美元一桶。如果有人把石油价格降下来,比如说欧佩克的人说:好啊,如果你发展新能源产业我就把价格降低到15美元,那么你的新能源产业就会统统破产。我们很可能也会面临类似的事情。
第三点,对于中国来说,数据显示我们目前是世界最主要的碳排放国,但问题在于60%乃至70%的碳排放是外国资本干的。所以现在美国说:你中国需要承担清理这些碳排放的成本,他们可不会去说这些外资公司需要承担其中的70%。结果就是那些从来没有从这些生产中获得好处的中国农民在未来数年中去承担清理的成本,这简直是荒谬,完全的不公平。
第四点,气候变化,在科学上还具有争议性,也比较复杂。我们对于那种“如果你做了……那么你就能收获……”的观点要非常谨慎。在物理上,污染不可能消失,只可能被转移(注:此处廖老是对物质守恒定律的误读),从一个领域转移到另一个领域,这是物理基本定律。所以就碳政治话题来说,很快就会显现:这不是减少不减少污染的政治游戏,而是一个谁把碳排放转移给谁的游戏。比如说,有一个温室气体排放者是奶牛(奶牛的粪便),但是我们如果需要牛奶,那么就不可能避免这种污染。这只是许多例子中的一个。现在我们不能说,因为现在遭遇金融危机,在这一块以前没有投资所以就往里面大量投资。这可能会让我们从金融的破产又跳进另一场破产危机。我们应当谨慎。比如说,我曾经是纽约州的环境方面的咨询人,纽约州的哈得逊河曾经被严重污染,当时是因为GE等企业都向里面倾倒化学物质,倾倒了一百年。纳尔逊·曼德拉出任州长之后,建立了一个“清理委员会”,而我是其中的一个顾问。当时花了10年时间终止污染,然后逐渐的清理,哈得逊河现在非常非常干净。这只是一条河。对于中国的主要河流,污染清理不可能在1-2年内完成。也不可能靠罚款来解决。这是一个复杂的问题。
但不管怎么样,我们所要做的不是通过纳税人的钱来补救,而是通过发展一个全国性的环境恢复规划局来实现,这个规划局可以发行环境债券。同时各个地方政府也有能力发行这种债券。这样能够筹集资金来清洁水、发展清洁煤技术以及其他环保技术。从而对污染问题进行根治。现在在北京,因为奥运会搞了一些措施,比如限行啊,搬迁企业到河北、山东啊,这种做法的代价很高,同时进展却很有限:只是把污染从北京转移到其他地方而已。这是我们需要避免的结局。奥运会这样做还可以谅解,但到整个国家来说,所需要的是启动一个全国性的经济发展项目。但你不可能用市场的钱来做这个事情,如果你打算以利润动机为动力,靠私人投资来治理污染,结果会是不但没有完成清洁的任务,而且还让私人取走短期的利润,把破产企业给留下来。因为大部分私人对环保产业的投资,都不是清理污染,而是把污染转移给他人。比如说,通过把他们的污染外部化,比如说外部化到我们国家(把有毒垃圾转运到我国)。
对于京都协议上的碳排放额交易制度,我们要非常谨慎。因为说碳交易机制能够减少污染的说法也是一种“无依据论断”,它们绘出一个图景说你可以边赚钱边环保。他们说如果你有污染,不舒服,污染可以用购买碳排放来得到解决。到目前为止,让整个碳排放清理事业能够赚钱的唯一办法,不是去限制碳排放,而是简单的转移污染,把废料运到没有环保法规的国家去。所以,市场没有能力去解决这个问题。只有政府,只有配备了头脑清楚的经济学家和优秀的科学家,才能理解、解决这个问题。
理解这个问题就要2-3年,然后又要花3-5年去设计机制,然后再要花几十年去执行。现在,有两个选择,一个是让污染行为更昂贵,从而停止污染,但这种做法的代价是降低经济发展速度,我可不能肯定现在就放低经济发展速度是值得的。当然我们鼓励产业界去一点一点的改善,但这不是真正的解决办法。我们所要做的是花时间建立一个长期的经济结构去解决环境问题,而不是仅仅搞出一套金融体系(金融游戏,比如碳交易)就完事了。你需要先确定经济结构,然后再在其基础上搞一套金融制度区适应它,推动环保。但我认为其中重要的一点,就是光靠市场不可能解决这个问题,它必然是一套政府政策问题。
主持人:我可以归纳成:不要盲目崇拜市场。
廖:对。目前在国际论坛会议上,他们总是说,中国,你要让市场来完成这个事情,因为你的市场发展的很快。(这是胡说八道)。首先,市场不可能完成这个事情,其次,我们要让外资在这方面做出对应比例的支付来清理他们造成的污染。我很早就说过这一点,在我出版著作之前就提过:我们在改革开放早期所付出的代价,就是低工资和免费的环境污染,我断言,清理这些污染的代价将比得到的好处多上很多倍。但那个时候没有人听我的,因为大家都想要一点钱。我理解他们,因为那个时候我们很穷。但是现在我们应当明白这一点了。不仅我们应该开始明白,我们应当要逆转进程。不要总是听信、自己把自己捆在西方送给你的思想陷阱里面,一心想着市场能够发挥魔力,清理污染。
主持人:所以我们对于那些向中国推销碳交易机制的外国人要保持警惕。
廖:就像可替代能源一样。比如说,关于风能和太阳能有很多说法,太阳能被严重的误解了。在人类历史上,甚至在原始社会,就已经开始利用太阳能,因为农作物都是靠太阳生长起来的嘛。现在,在很多时候如果你要发展太阳能,就要占用土地,那会圈掉不少耕地(注:廖老在这方面较少经验,大部分规模电场选择在沙漠干旱地带建设)。如果你只是使用屋顶安装太阳能,也不是办法。大部分房子的屋顶铺满太阳能板所发的电还不足以支持这个建筑本身的能源消耗,更不能输出给其他用电者。所以说太阳能只是一种用于日常修补性的能源应用,比如说我们手机上可以有一个太阳能电池板,这样你等太阳出来了晒一晒就不用充电了——雨天除外。所以除了这些能源应用上的技术替换之外——单价其实比较昂贵,太阳能并非解决我们能源问题的主要出路。但这并不意味着我们不应该持续投资以保持技术突破。因为是否克服前沿技术困难经常决定了一个国家的未来命运。就像航海技术给英国带来了海军,这样他们能够统治世界。所以对于这些替代性新能源,我们都应当保持研发投入,但不要指望他们能解决全部的问题。
主持人:是补充性的解决办法。
廖:是的。
主持人:事实上太阳能还是一个间歇性的能源,还需要和电网进行适应,需要在能源储存技术上作投资。
廖:我没有提到其他问题,现在很多有长远眼光的经济学家开始担心两点:一是水,水的短缺或者说清洁水的短缺,特别是在中国。我们现在甚至还没有认识这个问题。另外一点,很多人没有充分意识到的是粮食短缺。如果继续纯粹依赖市场,我们将面临严重的粮食问题。市场导致了某些国家在其他国家尚存在饥饿人群的时候,向海里倾倒“过剩”粮食。这是典型的市场失败。如果你深入看待这些问题,你就能发现市场资本主义的局限性。
市场资本主义,对于那些梦想发财的小市民,很有吸引力。过去30年,我们中很多人都较为轻松的实现了小市民的发财梦。但现在应该要明白为此付出的代价了——可能要付出几代人的代价。这就好像对于很多人提高医疗保健水平是个好事,但是你不可能靠提高保健水平以让人们能够活200年。靠牺牲环境来换取经济发展也是一样的道理。我们总是用长期的麻烦去换短期的利润。比如说,你把人类的期望寿命,从70-80岁的正常水平,提高到120岁,但由此带来的问题也将是社会性的、物质性的。在中国,我们将人均寿命从40岁提高到70岁,在目前的社会分配制度下,就出现了严重的养老金问题),而我们又在人口政策上犯了过度推行独生子女政策的错误,为短期利益付出的代价现在是非常明显的。另外一个问题就是我们忽视了社会科学研究。在美国,他们也忽视了社会科学。社会科学在美国长期被市场原教旨主义所俘获,而我国的社会科学则长期被那些误解马克思主义的学者把持着。马克思本人也是一个社会科学家,一个经济学家。……
主持人:非常感谢廖先生与我们分享那么多他关于金融危机和国家发展的观点和见解。在这里,我们希望廖先生能够给四月论坛(ACCN)提一些建议和希望。您可以给ACCN的未来发展提一些建议吗?
廖:好的。我很早就听说了你们团队的工作,虽然不是很详细。今天,你们这群年轻人,在很少外界帮助(政府、企业)的情况下自主推动的事业,给我留下了深刻印象。
在国外,你们很有名,但是因为不正确的原因而出名。你们被认为是一个反外组织。事实上对于那些真正了解你们的人来说,你们所做的工作,是对国外媒体对中国的文化和政治歧视的反击。对CNN在奥运会前夕的那些报道的反击,创造了你们的四月论坛,这是一件好事,一件幸事!这也是毛主席说的,坏事,不总是坏事,可以是一个好事。但从一个机构的发展的角度来看,很多机构,可能是在某种逆境中作为某些主流机构的反方起步的,但他们都需要从一个“反方、被动”的角色,转变成一个主动的、建设性的机构。我认为你们正在这个过程的起步阶段。我们所应该做的,不是简单的反对西方媒体的文化、政治和意识形态偏见,因为如果你仅仅是一味的反对他们的话,你只是让他们更有名而已。我们所应该做的,应该是走毛泽东的战术:你打你的,我打我的。我们应该提高我们的视野,水准,我们对世界大事的看法,我们对国内时局的看法,我们对真相的看法,我们对国家长远利益的看法。我们的读者、观众会欢迎,比如说,我们能够自己覆盖G20会议,我们不需要说华尔街日报的报道是错的,我们只需要说我们是如何看待的。因为我们是中国人,我们是人民的一部分,我们所说的是代表人民的普遍观点。
最后祝福:
从“被动”的反对,转移到主动的自我立场的宣传,是很重要的,因为我们所要完成的任务,不是去纠正、教育外国人,我们要完成的,是为中国人民提供真实声音的渠道,如果我们只是单纯的反对外国记者,那么我们其实反倒是给这些虚假报道以合法性。如果我们不理睬他们,他们自然就会走开。我们所需要的是有自己的声音,不仅仅是让我们自己的人民明白真理,而且是要让世界了解我们的立场,以及我们思考的思路。要做到这一点,我们这个机构必须成为人民的组织,只有这样,才能得到永远的支持。

微信扫一扫|长按识别,进入读者交流群

|
|
|
|
|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