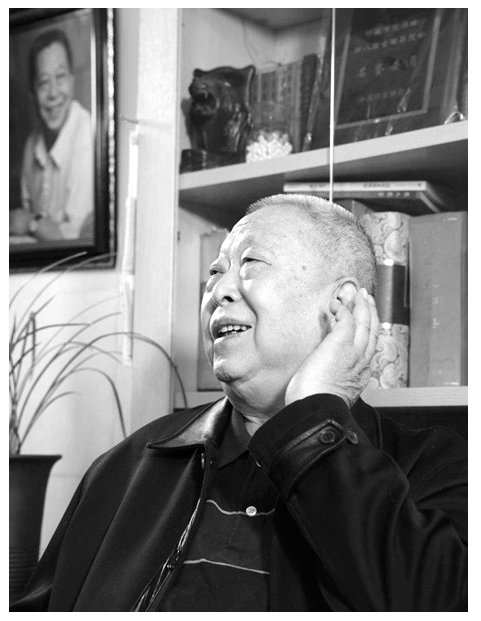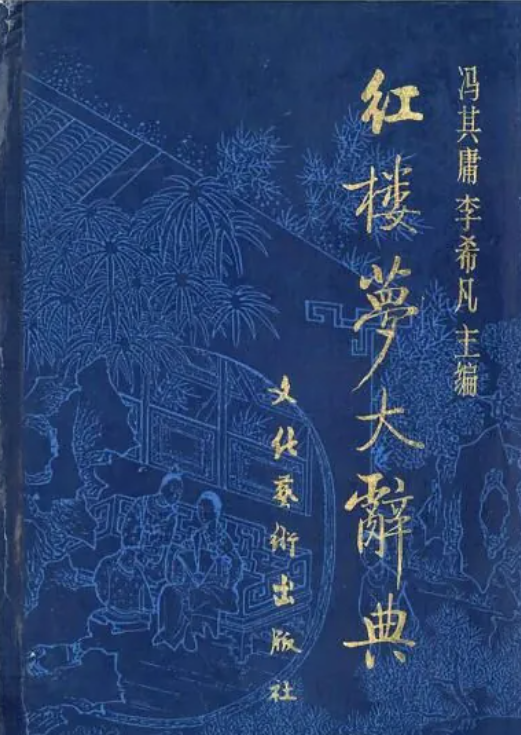李希凡口述:懵懂少年走上革命道路
李希凡(1927—2018),原名李锡范,字畴九,著名红学家,文学评论家。历任人民日报文艺部编辑,文艺评论组组长,文艺部副主任、常务副主任,中国艺术研究院常务副院长、研究员,中国红学会副会长,《红楼梦学刊》主编等职。代表作《红楼梦评论集》(与蓝翎合著)、《论中国古典小说的艺术形象》、《〈呐喊〉〈彷徨〉的思想与艺术》。1954年,与蓝翎共同撰写的文章《关于〈红楼梦简论〉及其他》在《文史哲》上发表,受到毛泽东主席的关注和肯定。
李希凡
红楼梦大辞典旧版封面
“绍兴师爷”先祖定居通州
我原籍是浙江绍兴,我的先祖当时来到北方,他叫李应彪,是所谓的“绍兴师爷”。我小时候很喜欢武侠小说,因为我们绍兴出过黄三太,出过黄天霸,我就想,我这个祖先一定也是很威武的人物。但其实不是,他就是一个刑房师爷。
李应彪到通州的时候正是这里最风光的时期,也就是漕运最兴盛的时候。他是乾隆时期来的,是通州的第一任首府师爷。世袭罔替,从他开始一直到民国,李家人都是通州政府衙门里的师爷。李应彪有两个儿子,一个叫李若民,另一个叫李若海,我大概是李若海的后代。从小,我对自己家族的历史不是很清楚,后来一个侄子告诉我很多事情。李家在通州不算盛族,但总是一个大家族,到我的上一代已经是衰落了,只有我们长房还做通州的事业。后来我的老二哥(长房堂兄)做了吴佩孚的秘书,和北洋军阀搭上一些关系。
我们这一支就很衰落,我的祖父是做小买卖的,我父亲幼年时很贫苦,上不起学,他一辈子最大的遗憾是没有考个清代的秀才。可他自学成才,他自学英文,第一个职业是给北洋大学的校长当外文秘书,做翻译工作,后来又在北京西城的甘家口做邮政局分局的局长。他在那时算是白领,薪金待遇很优厚。我有两个姐姐、两个哥哥,我的母亲大概15岁时就嫁到我们家来了,她是一位非常能干的母亲。在抗日战争以前,我们家有过一段温馨的生活,可这时间持续不长。“西安事变”前,当时于学忠做河北省主席,英国来搞中国邮政,我的父亲就参加了邮电工人罢工,而且是罢工委员会的成员。结果是虽然斗争胜利了,可人家把我父亲抓住了,也不敢把他开除,只是反复调查,但不让他当局长了,他就失业退休了,当时他只有36岁。后来坐吃山空,我们家里生活受到影响,上学的也受到影响。我的姐姐们当时上了高师,我的大哥因为在家里不受管束,我的父亲就把他送到军医学校去做军医了。
失学挨饿做学徒
那段时间对我的影响是最大的。我几岁的时候发生了“通州事变”,当时有一个军阀,也可以说是北洋军阀的一个遗老,叫殷汝耕,他搞了一个冀东二十二县“自治”,实际上就是日本傀儡政权。有个叫张庆余的,他的部队起义,发生了“通州事变”。那时我们住在五定庵,部队在城墙上开炮,打西仓的日本驻军,后来通州人都去逃难,因为日本要回来报复。大家就逃难到潞河中学,那里是美国的租界地。
又失学又挨饿的时代被我赶上了。这时我父亲的养老金已经没有了,更何况“大票子”一来,把银元都搞掉了。他找了一个私塾,教十几个孩子,没过多久就得了半身不遂。我本来上小学,后来上他的私塾,我这一生可以说没有完整的学历,小学上到二年级就失学了。父亲生病以后,我二哥出去当学徒,我也去当了一次学徒,在北京现在的东安市场,一进南小门,有个华宝洋服店,那时我大概13岁。老实说,封建的商店里,徒弟和师父之间绝对是一种封建的关系。比方说我有三个师哥,有一个出师了,一个跟着师父站柜台,另一个师哥和我就是不能上柜台的,只能去打打水,到食堂去帮厨。这位师哥只比我大一岁,我们俩一起挑水,用大木桶把水从门口挑进厨房。木桶本身二三十斤,再加上水五六十斤,我在后边,师哥总说我偷懒,老是给我穿小鞋,有一次实在是惹恼我了,我就打了他一拳,打在鼻子上,满脸的血,我一下子吓跑了,从东安市场一直跑回通州家里,再也没敢去。后来人家也没把我怎么样,只是我二哥把行李领回来了,从那以后二哥就说我不是这块材料,还是上学吧。
我不是一个安安静静的孩子,更像个野孩子。那时候通州虽然不是太繁华,但比起旁边几个县,它还是一个繁荣的县城。现在的通州很引起研究《红楼梦》的人的注意。据考证,有一部分红楼梦专家都承认曹雪芹最后埋葬在通州张家湾,现在在张家湾有一个小型的纪念馆。通州是漕运的终点,林黛玉是坐船来,从这一带登陆的。
曾经有一个皇帝临时停留的地方,叫万寿宫,对面是河沿,那里就是通州的娱乐场所,说书的、杂耍的都在那里,旁边还有个剧院。我从小就爱听评书,当时有几个说得比较好的,我最欣赏的是说《三侠剑》的一个老说书人,可他是吸毒者,最后死在了白面房前面。戏园子是要钱的,我进不去。
我家这条胡同里大多数是中下层人,但都很讲义气。我父亲生病的时候,我大哥曾经从军医队伍回来过一次,大家都知道他是国军,却没有一个人泄露,如果有人泄露,日本人就会把他抓走。邻里乡亲让我很感动,虽然三教九流都有,但大家都对日本人很仇恨,不愿意做亡国奴。所以我大哥安然地回来探亲,也安然地离去。这些都对我有一定的影响,我们小朋友别的事都是懵懵懂懂,但有一点相同,就是恨日本兵。后来我小学毕业,姐姐给我找了个工作,去印刷厂印钞票。我做电机工徒,钞票是四个版,印钞票要一个版一个版来回走,打磨的、往上铺纸的是师父,擦版的是徒弟。我那时候营养不良,非常瘦,没有力气,擦版擦得不干净,干了不到一年,实在干不下去了,就跟我二姐流浪到石家庄。
与“五四”新文学结缘
石家庄那时正在成立石家庄图书馆,这地方叫教育馆,实际是图书馆。我当时16岁,当一个管理图书的小馆员。这是我第一次比较全面地接触“五四”以来的新文学,包括茅盾、巴金、鲁迅的一些作品,最多的是老舍的作品,其实这些作家都在大后方,并不在沦陷区。但我看后得到些启示,朦朦胧胧觉得书里描绘的社会不公,当时我觉得最惨的是老舍的《月牙儿》。在石家庄的日子里,我不只在文学上接受了“五四”的影响,那里还有一个业余剧团,剧团临时的团长是长期做话剧工作的,我觉得他是一个很有才华的导演。那段时间他导演《雷雨》,晚上借我所在图书馆的图书室来彩排、对词,我跟他们熟了,后来加入了剧团,在布景后边做提词,有一段时间《雷雨》剧本我都能背下来。
除去剧团,我还跟一个年轻人的小团体经常在一块聊天,聊天的中心就是日本人什么时候滚蛋。他们是在天津、北京有很多消息来源的人,在小团体里有时谈到延安,有时谈到重庆,有倾向于共产党的,有倾向于国民党的。我就是从这里了解了共产党。后来抗战胜利了,我就希望赶紧找到我的哥哥姐姐,我的愿望就是上学。我又找了一份看场子的职业,看了两三个月,在这时接触了当时美国的所谓文艺电影,对我的影响比较大。
通过书信来往,我找到了我的大姐和大哥。大哥已经是国民党的军医,大概是中校了。我向他提出要上学的愿望,当时是1946年,我19岁,想上中学已经过时了,想上大学又不够格,我就盲目地补习,学习小代数、大代数、几何。就这样一直到1947年上半年。我希望哥哥姐姐能给我找一条考学的路子,但他们当时都在上海,觉得我没有学历,没办法考学。商量的结果就是让我到姐夫身边去。
投奔共产党员家庭
我的姐夫叫赵纪彬,在东北大学、东吴大学、复旦大学都当过教授,他学哲学,是研究先秦诸子百家的,特别是《论语》。当然,我那时还不知道大学教授是什么,只知道要去帮助他写作,可以在他的学校旁听。实际上,他是地下党,搞学生运动,之前在东北大学被辞退了,他就到了上海的东吴大学,1947年上半年就上了黑名单,国民党特务在追捕他,他又到苏州去避难。后来应老朋友杨向奎的邀请,到山东大学去任教。我姐夫给我的意见就是到青岛来,我也没有别的出路,既没有学历也没有专长,已经20岁了,只好先到这里来,至少闻闻大学的气息。
当时我在家里也已经待不下去,因为冬天的时候我从北京回来就被国民党的人盯上了,他们愣说我不是这家的人,幸亏我们的保长出来作证,说我是李家的三儿子,这样才没有被抓走。坐了三天三夜的海船,我到了青岛,背着行李找到了我姐姐的家。这是我第一次接触共产党员的家庭,我姐姐当时在青岛是受到两位共产党员援助的,一位是青岛地下党的市委委员,在纺织公司做职员。还有一位受党的委派,从青岛到华北工作,临走时把炭和四百多斤大米留给了我姐夫。这是一个教授家庭,不会为柴米油盐吵架,但他们也有不同意见,有时是生活上有不同的看法,有时是对某种事情有不同的意见。我感觉说到底是有文化和没文化的区别,而且,共产党员的家庭跟一般的家庭还是不一样。
我的姐夫给了我很大的帮助,而且算是我的启蒙老师。我是混混沌沌地到青岛去的,对国际国内大事根本没有过接触。我看到有山东大学的同学来,跟我姐夫讨论问题,逐渐了解了他们的看法,他们要进行什么样的活动,宣传什么思想,我的脑袋稍微开窍了一点。我的姐夫又建议我到山大听听课。山大中文系系主任杨向奎是对我一生有很大影响的老师,他给我开了听课证,所有中文系老师的课我都可以去听。那时候有几位名师,有《中国诗史》的作者,中国文学史专家,陆侃如和冯沅君,这都是很有名的一级教授;有杜诗专家萧涤非,我很同意萧老师对杜甫的评价。还有杨向奎的中国通史、冯沅君的宋元戏曲、萧涤非的魏晋南北朝和唐朝两个朝代的诗歌讲座,我都听得很入迷。我姐夫还建议学一门外语,不然很多书看不懂,他提议我学日语。
建立马克思主义世界观
我要着重介绍一下我的姐夫赵纪彬,他在启蒙老师中对我影响太大了,老实说,我的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就是在他的帮助下建立起来的。他1926年就加入了共产党,领导过河北一带的农民起义,也在吉鸿昌的部队里做过政委。后来因为在河北省和陕西省做地下党的宣传部部长,一段时间内被捕了两次。他就在监狱里学日语,自学成才。在山大我听了很多中文的课,主要帮助姐夫写作,那时真是苦,他说的话我都听不懂,因为都是文言文,我只好整天抱着《辞源》。姐夫是个马克思主义者,给了我一本《简明哲学辞典》,让我先熟悉熟悉。那本书对于马克思主义是什么,列宁主义是什么,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这些人是什么状况,全有介绍,而且对每一个马克思主义的相关名词都有简明的解释,我就逐渐地熟悉了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我姐夫研究的又是中国的诸子百家,特别是《论语》,孟子、墨子。我只好读《诸子集成》,不懂就到《辞源》找解释。最初我是很痛苦的,因为如果不能给我姐夫口述做笔录,我待在这里就没有意义了。我笔录了他的一本哲学著作《中国哲学思想》,就慢慢地进入他的哲学世界。后来我又大量地读马克思主义著作,一直到我想读《资本论》,我姐夫就生气了,觉得我的文化水平和社会知识达不到看这部书的水平。可是我把《列宁选集》和《斯大林选集》都看了。
我姐夫后来转移到胶东解放区去了,因为国民党要抓他。1948年年底到1949年年初,我看了《资本论》第一卷。我重点看了“商品”这一章,就是剩余价值学说,我觉得不难懂,但马克思主义运用到实际当中就难了,因为光读懂文字是不够的。另外,我因为听了些文学课,对文学很偏爱,很想将来做文学的工作。我也读了很多的书,除去马克思主义原著,还有《鲁迅全集》。我姐夫虽然不让我看《资本论》,但我读鲁迅他很高兴。我读第一遍《鲁迅全集》的时候,真是佩服得不得了。我又读了李何林的《近二十年中国文艺思潮论》,他对于现代文学史的精细论述,对我影响很大。我后来在经历文坛斗争的时候,内心深处很倾向鲁迅。还有一些苏联小说,当时我几乎两三天就能看完一本,年轻人精力旺盛,晚上我给我姐夫做完笔录已经是一两点了,可一下子睡不着,我就看小说。所以,我的文化水平就是看书看的,我的整个中学是一片空白。从1947年到1949年解放,我在青岛度过的两年时间给我的一生带来了很大的变化。
树立革命理想信念
我在姐姐姐夫家经历了国民党最后的时代。生活上,这两位教授是很困难的,到了金圆券时期,都是我去给他们领钱。因为解放前夕,青岛的形势很复杂,国民党特务很活跃,要抓捕进步的人。山东大学的教务长就是特务机关的一个负责人,特别是训导处处长,这个人抓捕了很多学生,有的学生还牺牲了,赵纪彬他们的名单也是他提供给特务机关的。到了1948年下半年,金圆券在人民心中完全没有威信了,工薪阶层领了钱,得马上到黑市去买银元或者美金,否则很快就变成废纸。我当时替杨向奎先生和我姐夫去领工资,然后去黑市买银元,大学教授的工资太少,美金是买不起的。我给我姐夫大概能买八块银元,杨先生可以买十块。这些也不够过一个月的生活,我记得我姐夫到解放区去的时候,陆侃如和冯沅君先生送了四十元钱给我姐姐。那是青岛最黑暗的时期,教授之间只能互相救助。
在这中间,我还到过一次解放青岛的前沿阵地。党和山东大学的联系是通过毕中杰同志,就是我之前提到的,青岛地下党的市委委员,通过他给山东大学的教授传送文件。他跟我姐夫有点私交,时常由我去取送文件,所以这时候我也看到了很多解放区的书,比如毛主席在七届二中全会上的讲话、大连出版的《毛选》。这版《毛选》现在很难找到,它包含很多方言土语。后来,他们市委领导了山东大学的反迁校斗争,这场斗争是学校委员会胜了,他们把国民党教育部弄来的费用全都转给中法公司,买了布。校长叫赵太侔,他虽然是国民党任命的,也是国民党党员,但对国民党已经完全失去信心了,他就放任不管这事,故意让教授委员会把钱扣下。积极做这件事的就是我姐夫和杨向奎,后来国民党抓他们,地下党就赶紧把这两位转移了。杨向奎是个民主人士,就转到青岛的寺庙里,我经常去看他。毕中杰要迎接解放,他就到青岛解放的前沿阵地去了,他也叫我去。那时候形势很紧张,我也不想读书了,一心想参加革命。这些就是我的少年生活。
(于溟跃 整理)

微信扫一扫|长按识别,进入读者交流群
|
|
|
|
|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