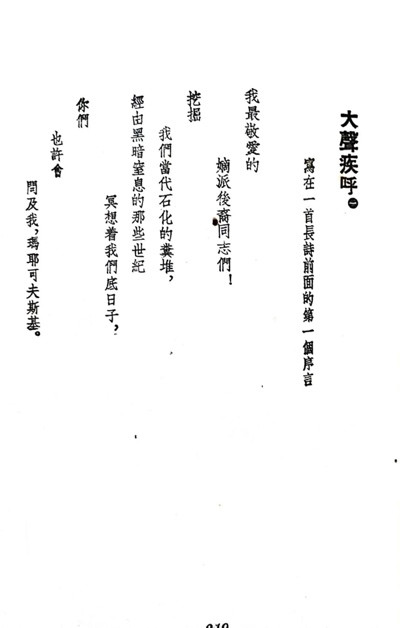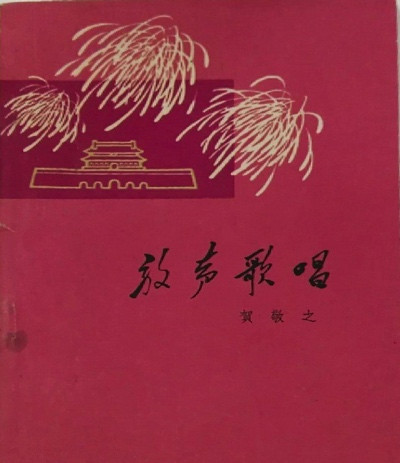贺敬之与社会主义文艺探索中的“民族化”问题——重读《放声歌唱》
摘要:贺敬之在20世纪五六十年代创作的诗歌被评价为文艺“民族化”的初步成就,这些诗作的形式探索与思想建构,体现了当代中国在社会主义文艺建设上的基本构想。诗作的探索性体现在形式、思想以及读者询唤三个方面:在形式方面,这些诗作改造并吸收了外来文艺形式和中国传统文艺形式,形成当代中国的“民族”表达,参与建设了“民族形式”,也基于当代中国的需求重新定义了“古典”和“外来文化”;在思想内容方面,诗作将中国的历史和未来加以具象化,打造了当代中国足以超越时空的乌托邦形象,构建了当代中国的历史文化认同;在读者询唤方面,诗歌将历史文化认同化作个体的感知方式,塑造了当代中国的文化主体。
1956年7月,贺敬之的《放声歌唱》刚在《北京日报》发表,就收获广泛好评,备受鼓舞的诗人在之后两个月内完成了后三节,向“八大”和国庆七周年献礼。第二年,中国青年出版社出版了《放声歌唱》的单行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将诗作录音播放,产生全国反响。之后,贺敬之的《十年颂歌》《桂林山水歌》《雷锋之歌》等诗作也接连引起关注。评论家高度评价贺敬之,认为他的创作融合了“楼梯式”等外来艺术形式和对偶等中国传统艺术形式,茅盾更指出贺敬之的创作“达成了民族化的初步成就”1。直到今天,研究者也都肯定贺敬之在推进当代中国民族形式建设上的贡献。
贺敬之:《放声歌唱》,中国青年出版社,1957 年
贺敬之无疑是中国社会主义文艺探索道路上的代表性作家:20世纪40年代,他作为主要执笔人创作的歌剧《白毛女》影响了数代中国人对革命的情感;五六十年代间,他创作的《回延安》《放声歌唱》《桂林山水歌》《雷锋之歌》等诗作,以生动的意象和昂扬的激情,形塑了新中国的形象,召唤了人民对新中国的认同。这些创作不仅推进了当代中国文艺对中国历史的叙述,抒发了对中国革命的感情,还因为充分作用于读者的感觉结构,参与塑造了新中国的主人翁意识,进而切实地作用于中国各项建设。贺敬之早已不只是一位文艺工作者,他的创作参与构造了当代中国人的精神,因而,他的书写是当代中国进行思想建设和民众动员的一种代表性方式。近年来,学界围绕20世纪40至70年代文学与政治、文学与社会的关系问题展开研究,产生了一系列重要成果,这些研究拓展了文学研究的边界,揭示了文学超越文字艺术的价值。不过,文学能够起到这样重要的作用,在于它具有强大的形式功能和表现力,而贺敬之等人的创作能够在政治、社会和思想文化上产生巨大作用,在于其文学的表现力起到了感染和动员的作用,因此,考察贺敬之的文学创作所产生的现实作用,应关注他的政治、经济、社会观照如何以文学的方式表达出来。重读其《放声歌唱》等代表作,可以管窥当代中国思想是如何获得文学性表达的。
《放声歌唱》等诗歌所收获的评价中,“民族化”这一点格外醒目,几乎每位评论者都会赞誉贺敬之为“民族化”作出的贡献。2五六十年代的中国正强调“民族形式”建设,3贺桂梅将“民族形式”探索视为中国当代文学的源头之一,指出民族形式探索辅助了当代文化逻辑的构建。4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贺敬之“民族化”的形式探索及其相关评价,都应视为当代中国构建自身表达方式和文化逻辑的一部分。考察贺敬之的“民族化”到底是怎样一种形式,这种形式具有怎样的意义,将透视出这一时期中国文艺对形式与主题的追求。
阐释“民族化”的意义,首先需要厘清“民族化”在当时的具体意涵,本文第一节通过贺敬之对中外资源的使用及其获得的评价,分析“民族化”的所指,确定“民族化”与外来文艺资源、中国传统文艺资源之间的关系,明确贺敬之具体进行了怎样的形式探索。其次,“民族形式”若没有完善的民族叙事作为依托将流于空洞,贺敬之在民族形式探索上的成绩离不开形式和内容的充分结合,所以第二节从贺敬之诗歌中的中国叙述入手,分析形式与内容如何结合,构建了“民族”历史认同。再次,“民族化”探索需要充分作用于读者才能得到落实,而贺敬之诗作中体现出对“大我”与“小我”关系的思考,这一思考反映出他对于当代中国主体的理解,因此第三节着力分析贺敬之的诗歌构造了怎样的主体,以及诗歌何以询唤读者,使之成为当代中国的“民族”主体。三部分内容分别聚焦于贺敬之的创作在形式探索、思想建设以及读者建构上产生的“民族化”效果,它们将反映出从作家创作到读者反应的整个文学过程如何塑造“民族”的文化认同。
01
“民族化”的所指:在外来文化与本土传统之间
评论家们在肯定贺敬之诗歌的价值时,突出了他在“吸收外来艺术形式”并使之“民族化”上的成绩,但这两点都让人困惑。评论者认为贺敬之学到了马雅可夫斯基的精髓,但只讨论了楼梯式的使用,两位诗人的风格实则有很大不同:马雅可夫斯基大部分的诗歌富于个人色彩,歌颂苏联革命、展现苏联人民精神的长诗也多带有悲愤的情绪,而贺敬之的诗歌多以集体为发言主体,情感基调也以昂扬为主。仅就楼梯式来说,贺敬之也只保留了其面貌。作为俄国象征派和未来派的继承与发展者,马雅可夫斯基高度注重诗歌形式问题,他也以自己对长韵脚的使用以及对重音的考究为傲。他使用楼梯式时,分行的主要目的是凸显重音,但这建立在俄语自身形式特征上,不符合汉语表达的习惯,因此不宜在中文表达中使用。所以当贺敬之使用楼梯式时,他的目的是通过楼梯式拉开的距离来突出意象。极端地说,就算没有马雅可夫斯基的先例,中国作家也可能灵机一动地将自己的诗歌分行拉开。固然,为了尊重创意和尊重文学影响的轨迹,对前辈作家的任何借鉴都需要表述为受到前人影响,但若真正探究文化间的交流影响,这种程度的借鉴能否看作“影响的焦虑”是值得讨论的。考虑到当时中国着力体现中苏友好,评论者甚至作家本人都可能过度强调苏联作家对中国的影响。不过,评论者选择贺敬之的这些诗作为代表来解读苏联文学对中国文学的影响,表明其创作在当时确实有代表性意义。深剖贺敬之的作品何以是代表性的,有助于进入当时中国的文化政治逻辑,也能更好地理解苏联的影响到底是如何发挥作用的。
《玛耶可夫斯基诗选》(新文艺出版社 1954年版)内文
将贺敬之的加工视为“民族化”的判断也需要深究:当评论者认为贺敬之的创作具有“民族”特征时,这种“民族”特征是什么?以谢冕的解读为例,他指出贺敬之诗中“大量使用着对偶的形式。字与字、句与句、甚至是上下段落间,都有严格的对称和排比。古典诗歌和民歌中那种一字一句加以推敲的优良传统,也被继承了下来”,他运用的楼梯式“是经过了改造的,如诗行内部结构的改造、诗行内部及诗行间的排偶的广泛运用、民族习惯的押韵等;使它们初具民族化,而且是贺敬之所特有的东西了”。5但创作者只要使用中国语言创作,必然会使用中国的句法、韵律、节奏等形式,这些特征都可以被称为“民族”的吗?如果这些是“民族”的,翻译者就已然将其“民族化”了,何以认为贺敬之进行了“民族化”呢?可见“民族化”不仅是用已有的中国形式对外国形式加以改造,它还意味着在中国固有的形式和外国形式之间进行筛选和加工,形成一种能够代表“民族”的形式。这也意味着,中外文化的交流碰撞出一个空间,在这空间中生长出既非外国也非中国固有的一种新形式。
要理解这一空间的存在,首先需要理解外来文化进入中国文化领域的过程。中外文化所发生的最初碰撞是翻译,而翻译必将开启一个既非原始语言也非译入语言的空间。由于不同语言各自的特征和局限,文化接受方即便力图完全保留所接触文化的原始状态,也是无法实现的。雅各布逊从语言学的角度指出诗歌无法翻译,因为诗歌的意义体现在其形式上,而一种语言无法百分之百地复制另一种语言的形式美,6所以等值翻译不可实现。因为等值翻译不可实现,翻译必然做出退让来保证表达成立,所以翻译总是基于译入语的语言习惯去转换原始语。不过,这不等于说译入语一方仅按照自身语言习惯去译介外来文化,因为外来作品的语言表达过于接近译入语也会让读者感觉不真实,所以翻译也需要以带有异质色彩的形式去呈现异质文化。韦努蒂将翻译区分为接近译入语的“归化”式翻译,和与译入语形成差异的“异化”式翻译,7这种区分方式提示我们,翻译是以译入语为基准的行为。晚清以来,中国学者就力图通过“硬译”等方式来拓展中文表达能力,这看似要使语言完全合乎原作表达,但这种探索的实际目的也是拓展中文,关注点还是译入语。这种权衡带来的结果,便是在原作语言和译入语之间,促生一种既不同于原作语言也不同于译入语的新型表达。译制片配音时采用的“翻译腔”是一个直观的例子,翻译腔既非原始语言的语调,也非中文本身的语调,而是中国想象他者时构建出的腔调。可见,译介本身制造了一种新的艺术形式,它既受到两种语言和文化的影响,又异于这两种语言文化。因此,中外文化交流首先是因为翻译而打开一个文艺可以生长的空间,在这个空间内部,外来文艺的内容和形式经过中国文艺的接受习惯和现实需求的加工,而成为新的形态。即便是中国“一边倒”地学习苏联的时代,对中国产生影响的苏联也是经由中国接受习惯和需求加工后的“苏联”;本文探讨的马雅可夫斯基对贺敬之的影响,也应理解为经过了中国需要而处理后的马雅可夫斯基所产生的影响。
外来文化也构成了中国文化的参照物,中国因此更自觉于自身的艺术特征,关注自身的文化传统,并力图在吸收古典和民间文化的基础上形成自己的表达。评论者正面评价贺敬之将楼梯式加以“民族化”,体现出对贺敬之具有民族自觉的肯定,也体现出当代中国强调民族文化的自觉。不过,如果“民族化”只是要求书写者以中国固有形式进行书写,那么楼梯式在译介过程中已然经过中国化,解释不了贺敬之的创作何以被看作“民族化”的初步成就。茅盾的评价中提到《十年颂歌》等抒情长诗对中国传统抒情长诗的继承、对骈散体的利用,“巧妙地采用了一些传诵已久的古典诗词的词汇,溶入语体的诗句中”8,这里“传诵已久”和“古典”都值得注意,它们表明贺敬之是转化了代表中国文化的要素,才被视为“民族化”的表达。所以,一种形式能够获得“民族化”的评价,需要它合乎对“民族”的想象。贺敬之获得的认可,意味着他的书写表现出一种新的形式,且这种新形式合乎时代需求。由此反观贺敬之的书写,其诗作主体是现代书面语,是一种规范的、正式的且能够在全国流通的语言,他的语言是在达到了这一标准的基础上,又融入了“古典诗词”和符合“民族习惯”的形式,才被视为民族化的创作。
何为“民族”的形式也由此得到指认,即贺敬之的创作吸收了“古典”文化要素后,评论者通过指认其创作中的古典形式和民族习惯,确定了何谓“民族”的形式。安德森等学者的研究早已指出“民族”是一种现代建构,9它不是不言自明的,所以,什么能够代表“民族”,应在评价过程中做出解释。而评论者强调贺敬之对“古典”的使用和对“民族习惯”的把握时,并未解释“古典”何以经典化为“典”,也没有解释什么叫作“民族习惯”、何以这就是“民族习惯”,而直接以此定义贺敬之的书写,这就等于以贺敬之的书写来界定了“古典”和“民族习惯”。所以贺敬之被命名为“民族化”的这一过程,就是在定义“民族”的文化。回顾茅盾指出贺敬之“民族化”的语境,他力图指出的是中国文学自“五四”以来过度强调外来文艺形式影响,而中国有自己的文艺传统,应当注重吸收来自民间和传统文人的文艺形式,通过“批判地继承旧传统和创造新传统”,实现“毛主席在二十多年前所指出的‘新鲜活泼的、为中国老百姓所喜闻乐见的中国作风和中国气派’”。10当评论者以“民族化”指出写作者的创作价值时,不仅是肯定了其作品的地位,也在中外文化碰撞出的空间中,确定了当代中国应有的表达方式。进而,当贺敬之对古典和民间文艺的使用被视为“民族化”的手法时,这些文化遗产便得到了重新赋值。
贺敬之被认为成功地在吸收外来文化的基础上将其诗作“民族化”,也同样指认了外来文化资源对中国文艺发展的作用。通过指出贺敬之创作中带有马雅可夫斯基的形式特征,等于承认苏联文学对于中国文学的启发作用,呼应了当代中国对中苏关系的叙述。这种指认是基于中国已形成的民族形式而后设的命名,是因为贺敬之已具有代表性,故选择以他的作品作为中国文学吸收马雅可斯夫基影响的依据,哪怕这种形式并不接近马雅可夫斯基。这也反映出中外交流的成果是从当代中国的形式构建出发而对外来文化要素加以筛选后的成果。
所以,当代中国是在中外文化碰撞出的空间中,基于自己的需求而吸收、转化外来文艺形式、中国传统文艺形式,从而构建出当代中国的“民族”表达。它既不全然是中国的,也不全然是外国的,而是在中外交融中生长出来的。近年来翻译研究格外强调“主体间性”,11以此取代“主体–客体”的关系,强调要尊重交互双方或多方各自的主体性。“间性”的提出对于理解中外文化的交流问题确实有意义,它启发人们关注多种文艺各自的脉络,理解文艺是在交互关系中发生动态变化。但这一概念也存在一些盲区,即“主体间性”预设“主体”是一个个独立的原子,但“中”与“外”、“我”与“他”都是相对而生,当“间”这个位置生成“民族”后,它对原有的“中”形成了溶解和替换,如果以“间性”来指认当代中国的“民族”性,就将它与传统中国切割开来。所以,以“主体间性”的理论为参照,当代中国的“民族性”更体现出它是一种融合的结果。应当将“中”“外”视为一种流动状态,置身流动中的当代中国基于一个特定时间和空间位置的限定,选择展现为一种形态。这接近于东浩纪所提出的“数据库”,12即各类文化都变成了数据库的碎片,它们相互拼合而成为一个新的叙事。但当代中国的实践又与“数据库”不同,因为“数据库”带有机械化和随机性的特点,而当代中国是基于现实需求而自觉地选择各类资源,并融合各类资源使之和谐并自洽。若是生硬地拼合各种形式,诗作也将支离破碎,而贺敬之以合乎时代需求的叙事,有效吸收和消化了包含马雅可夫斯基和中国传统形式在内的多种艺术形式,其诗歌表达才连贯而有感染力。这种有效的融合才是当代中国探索民族形式的要义。而这也提醒人们注意,构建民族形式是建立在民族认同基础上的,它离不开民族叙述作为依托,所以民族形式的探索不能局限于形式层面,它必须与叙事及内在的认同构建相结合。
02
民族历史认同:历史的空间化与去空间化
20世纪50年代中期至60年代初正是革命历史叙述逐渐成熟的时期,文学、美术、电影等多个艺术门类从革命历史、工农业发展、多民族团结等多个角度描绘了中国革命与建设的历程,为当代中国建立了稳定的历史想象。贺敬之对中国民族文化的呈现,离不开这样的历史观作为依托。同时,他的创作也参与塑造了中国的历史面貌,这与他的民族形式相结合,共同形成他的“民族”表达。
在主题与内容方面,贺敬之创作备受认可之处,在于它以生动的意象再现了当代中国的空间景象和历史变迁,“用鲜明的有特征意义的词,概括一个事物、一种现象,形象与形象之间留有空间,特意给读者以回旋、联想的天地”13。《放声歌唱》开篇就写到“无边的大海波涛汹涌”“生活的浪花在滚滚沸腾”14,打开极为阔大的视野,并以楼梯式的排布重复该句,以文字营造出近乎图像式的呈现,让读者感到“生活”真如海浪般扑面而来。诗中也以大量意象再现出中国的景致:“长安街的/夜景呵/怎么竟这样迷人?/大兴安岭的/林场呵/怎么竟如此美丽?/一片汪洋的/淮河两岸/怎么会/万顷麦浪?/百里无人的/不毛之地/怎么会/烟囱林立?/为什么/沙漠/大敞胸怀/喷出/黑色的琼浆?/为什么/荒山/高举手臂/捧献出/万颗宝石?”15以一系列景观化的意象展示中国广博的地域上既富于现代化又富于自然活力的场面;为众多评论者称道的“我走进农村。/我走进工厂。/我走向黄河。/我走向长江。……/五月——/麦浪。/八月——/海浪。/桃花——/南方。/雪花——/北方”16,拉出了纵深的空间风貌和悠长的时间感,展现出中国不同地域、不同季节的生命力。不仅是《放声歌唱》,《桂林山水诗》中“画中画——漓江照我身千影,/歌中歌——山山应我响回声……//招手相问老人山,/云罩江山几万年?//——伏波山下还珠洞,/宝珠久等叩门声……//鸡笼山一唱屏风开,/绿水白帆红旗来!//大地的愁容春雨洗,/请看穿山明镜里——”17,先展现桂林山水如画的景致,而后“云罩江山”“穿山明镜”的诗句,烘托出山水的神圣和灵韵;《十年颂歌》中“看不完的/麦山稻海,/望不尽的/铁水钢花……/四时春风/吹万里江河/冰消雪化,/中秋明月/照进多少/幸福人家”18,所有这些都带给读者以鲜活的视觉化景观。这些书写体现出贺敬之高度自觉地描画新中国的景观,使新中国以形象具体的面貌呈现出来,因此,贺敬之的“民族化”探索便不只是形式探索,而是结合了形式与思想内容的探索。
以这样生动的意象呈现中国历史和当下面貌,贺敬之的创作产生了三方面效果。第一,它以极强的画面感烘托了中国形象,形塑了读者对新中国的认识。而塑造读者对中国的这种认识,意味着通过视觉化的呈现去构建读者认识中国的方式。柄谷行人以“风景”为例来分析日本现代文学的起源,指出“风景”是内面的人将自己的意识外化于世界的呈现,它是现代认知装置下的结果,被改变了认知方式的现代人将自己的感受当作了外部世界的“风景”。19贺敬之笔下富于画面感的表达,也构成一种历史观和中国观。当读者通过《放声歌唱》中钢铁的火焰、少先队的领巾、穿山越岭的列车、飞上高空的飞机、迷人的长安街夜景、美丽的大兴安岭林场等看到“新中国”之“新”,也重新以这样的方式理解了中国;当《桂林山水歌》中,作为新中国歌唱者的诗人将心中的“中国风景”投射于外在,将中国的认知转化为空间抒写时,他便引领读者以这样的视角认知中国,重构读者对中国和对自我的认知。
第二,诗歌以风景呈现新中国形象,也意味着以空间形象去承载中国历史。《放声歌唱》中,“在联合收割机/滚动着的/大雁塔旁,/在长江大桥头的/黄鹤楼上,/在宝成铁路边的/古栈道旁……/我看见/你们——/我们古代的诗人们”20,将现代与古代的景观放置在一起,勾画了中国底蕴悠长而又充满活力的精神面貌;“一片汪洋的/淮河两岸/怎么会/万顷麦浪?/百里无人的/不毛之地/怎么会/烟囱林立?”“我的曾是贫困而孤独的/乡村,/今夜/为什么/笑语喧哗?/我的曾是满含忧愁的/城镇,/为什么/灯火辉煌/彻夜不息?”21等诗句,以新旧对照展现了历史变迁。《桂林山水歌》中“鸡笼山一唱屏风开,/绿水白帆红旗来!”22一句,利用山与山之间突然打开新天地的宏阔感受,使“红旗”以排山倒海般的气势推向读者,让读者通过桂林山水的面貌感受到红旗,以及新中国强大的力量。诗人也借此表明,山川壮丽是中国人民通过翻身革命才得以实现的,所以山水之美与革命中国之神圣性融合在一起,萦绕在桂林山水上的灵韵,正是新中国的神圣性和吸引力降落在具体空间上的成像。这样的表达压缩了历史的纵深维度,使“历史”脱离了线性发展的轨道,化身一系列空间意象。中国的历史、当代中国的革命精神,因此得以意象化和视觉化,成为人们可感知的对象。
第三,空间化的呈现也引导人们以对历史的想象来替代空间。因为空间已然是以人们认识中国的方式而构建起来的,可视化的诗句以去空间的方式赋予了新中国以新的空间形象。在这些叙述里,场所是丧失了实存的,人在场所中的生产生活活动,都以理念化的叙述加以处理,一如桂林山水闪烁着历史的光芒,它被历史重新命名;身体是没有身体性的,每一个个体都可以扬弃自身,成为千千万万的“我”。以《放声歌唱》中从“我”到“我们”的推进为例,当“我”感叹“假如我有/一百个大脑呵,/我就献给你/一百个;/假如我有/一千双手呵,/我就献给你/一千双;/假如我有/一万张口呵,/我就用/一万张口/齐声歌唱”23,“我”胀破了自身的躯壳而成为众人。这样的“我”进入了各类空间:“呵!我走进/我的支部。/我走进/我的厂房。/我打开/星光灿烂的/《毛泽东选集》,/我登上/‘旄头漫卷西风’的/山岗。/我踏着/工农红军的/二万五千里足迹,/我翻过/党的伟大史诗——/千山万岭的篇章……”24此时,“我”和“我们”都越出了作为人的身体性,融入整体的空间之中。物与人都是历史性的存在,又以空间性的方式在世间显影,于是空间便是历史的构成,其立体维度也压缩了。所以历史固然空间化了,但也同时去空间化了。
这种构成空间的历史因为丧失了时间性、身体性、场所性,显现出来的“新中国”形象便是一个无时无地的超时空:“新中国”的缘起不在别处,正在此地,因为历史上的一切都在这片土地上留有印记;“新中国”的未来也不在某时,正在此刻,因为一切的幸福都已经在这片土地上歌唱出来。当诗歌通过“我”的行进历程来讲出斗争的历史,并在最后一节展望未来,歌唱出“让我们的歌声/飞向/今天和明天的/世界上的/一切地方”25,就让古今中外一切时空凝缩于新中国的大地,“新中国”就是一个在此刻已然实现的乌托邦。
贺敬之由此既继承也发展了新中国成立初期的颂歌。胡风《时间开始了》、何其芳《我们最伟大的节日》等作已然出现对中国形象的描绘,但胡风、何其芳等人笔下的中国是置身在时间线索中的中国。李杨指出胡风之所以认为“时间”开始了,是因为新中国的成立让中国得以进入现代化的时间,中国至此真正可以与西方的历史观念对话,真正具有了西方意义上的“历史”。同时,这种时间观和历史观是启蒙主义的,它上承五四新文化运动以来的发展意识,并对于新中国成立后的历史观产生了重要影响。26贺敬之诗歌中的中国已然进入新的历史,这继承了胡风诗中的发展意识,但另一方面,贺敬之通过将这种时间和历史加以空间化/去空间化,使当代中国成为当下实现的乌托邦本身。贺敬之的诗作带给读者的是一幅光明的画卷,中国发展至光明未来的过程被光芒所掩盖,仿佛它自始至终都是如此。在此,贺敬之可谓构造出了关于新中国的神话。让-吕克·南希指出“神话”的特性在于“它并不交流(/沟通:communique)某种可以旁证的知识:它是自身(se)沟通着(communique)的沟通本身(从这个意义上说,它也是同语反复)”,神话的真相就是它自己证明了自己是神话,“神话指称自身,因此,它将自己的虚构变成了自身意义的创建和开端”,它“不仅是由一个专有的真理,自生(sui generis)构成的,也许,它还有变成真理本身的倾向”。27当新中国被打造成超越时空的乌托邦,它就已经具有了神话性。
追溯贺敬之此前的创作,会发现他早已在构建中国神话。贺敬之在介绍《白毛女》创作缘起时,说这个故事源于“一九四〇年,在晋察冀边区河北西北部某地传出一个故事,叫做‘白毛仙姑’”,28但这段历史追溯是可疑的,因为这样的“白毛仙姑”传说产生不了仙姑信仰,不可能影响党的思想传播,也就不会像他所说的那样引起区干部去调查仙姑信仰之事。贺敬之自己也称之为“民间新传奇”,所以势必有一个可以影响到革命宣传的旧传说。依据孟远对周巍峙做的访谈,当时在晋察冀所流传的传说是“白毛仙姑爬山越岭,如走平路,像仙家一样,腾云驾雾”29。已有研究者指出这类“旧传说”中的白毛仙姑属于传说谱系中的毛女原型,30它们源于人们对山林野人的发现,31后人对其加以附会,称避乱山野的人因不食人间烟火,可以长生不死、羽化飞升等等,并与道教信仰和神仙方术建立起联系。这类书写往往感慨女子若不为人所寻见就已经成为仙人,说明其价值观认为成为毛女是幸事。自唐以后,毛女叙述日益完整和富于冲突性,在两种传说变体的基础上加以演绎,讲述躲进山林的女子因被亲人所“救”返还人间而凡人化乃至衰亡,或女子无论他人如何劝阻仍拒绝回到人间,因而可以继续腾云驾雾长生不死,这些叙述仍是以留在山中为幸。原本的“白毛仙姑”传说只体现仙姑光鲜的一面,所以是真正的“仙”传说。既然最初存在一个白毛女是“仙”的传说,《白毛女》就并非天然是由“鬼”变“人”的故事,而是首先从“仙”变成了“鬼”。所以“白毛仙姑”传说被认为是遭遇压迫的女子得到解放的故事,是《白毛女》后设的印象。以新的话语重构历史是现代历史叙述的常态,其中的关键在于让人们相信重构的历史就是历史本身,而在《白毛女》这里,让一代代人不假思索地确信《白毛女》源自“白毛仙姑”传说的,正是作为歌剧作者的贺敬之所写下的《〈白毛女〉的创作与演出》。贺敬之的创作内在地包含一种构造起源而又同时抹去起源的功效,他为当代中国的历史叙述提供了一个依托,让中国“民族”的历史得以自足。当读者将这个“新传奇”当作历史本有的叙述,就接受了当代中国的历史叙述方式,认同于“新中国”描绘的历史、现在与未来。
03
作为文化主体的“民族”
“歌唱”可以唱出“新中国”的历史认同,歌唱者的塑造便非常重要。研究者也注意到了贺敬之笔下的抒情主体,指出贺敬之的诗作充斥着大量的“我”,看似有很强的个人主义色彩,但这些“我”又表现出集体性。32恰如洪子诚在比较“政治抒情诗”的两个代表诗人时所言,郭小川表现的是“大我”构建的过程,而贺敬之则直接表现已然成熟的“大我”:“在贺敬之的诗中,‘我’、抒情主体已是充分本质化的,有限生命的个体已由于对整体的融合、对历史本质的获得而转化为有充分自信的无限”,相对于郭小川书写的是个人“本质化”的过程,“贺敬之抒写的是个人‘本质化’的完成、实现的状态”。33所以贺敬之笔下固然出现数量繁多的“我”,但每一个“我”都代表着群体。特别是第四节,贺敬之点出“在我的/献给祖国、/献给党的/诗篇里,/我要来歌唱,/关于:/我——/我自己。/呵,/‘我’,/是谁?/我呵,/在哪里?/……一望无际的海洋,/海洋里的/一个小小的水滴,/一望无际的田野,/田野里的/一颗小小的谷粒……”34指明每一个个体都是时代的组成部分。随着“我”的成长,“我”逐步成为“同志”、步入人群,从“我”成为“我们”:“呵,我!——/我们的/我!/我的/我们!/——是这样地和谐、统一!/这是党/给我们创造的/不朽的/生命,/是祖国的/无敌的/威力!/呵!/未来的世界,/就在/我的/手里!/在/我——们——的/手里!”35诗人看似只发出一己的声音,但他是以自己代表了集体在发声。贺敬之笔下的“我”,开口吟唱出的就是时代声音本身,其个体与时代无裂隙,也仿佛没有作家创作的痕迹在其中。
但常常为评论者所忽视的是,贺敬之诗歌中的“小我”并没有消失。诗中经典的“春风/秋雨”“晨雾/夕阳”“轰轰的车轮声/踏踏的脚步声”“五月——麦浪”“八月——海浪”“桃花——南方”“雪花——北方”,顿挫的对偶、递进的台阶形式,让人感到无数力量推动着整体打开宏阔的局面,每一个顿挫的节奏,都显露出“大我”中“小我”的存在。不同声音的唱和,意味着每个声音并不是同一的,它们在各自唱出不同声部时,和谐地汇合成华美乐章。所以,“大我”中的每个人仍是具有自主思考意志的,他们发现、思考中国发展中存在的问题,提供自己的声音,而最终这些意志共同推进集体的成型。个体并非背向人群而体现出自我意识,而是在与他人声音的唱和中,听见了自己的声音。所有个体的共同努力,推进“大我”的发展;所有声音的和鸣,促成新中国诗篇的完善:所以,“大我”通过“小我”才得以显影,诗歌以富于弹跳性的节奏形成“大我”对“小我”的询唤,让读者充分感到自身作为“小我”都代表“大我”,并随时聚合成“大我”。贺敬之以“我”的歌声,示范了理想的歌唱者应是什么样子:每一个抒情主体是自主的,同时也是与他人相联系的,每个人都自觉于自己是属于集体的,自愿表达对集体的认同。诗歌由此构筑了当代中国的集体性抒情主体“人民”,作为“人民”的每个个人处于交融状态,他们既是个人又是集体。
塑造这样的集体性主体显然具有文化政治意义。当读者按照贺敬之给出的方式去识别中国的形象之美、识别中国历史之变迁,进而参与歌咏中国,便回应了大主体发出的询唤,成为“人民”的一员。由于正是作为“人民”的“我”讲出了当代中国的历史变迁与空间形象,支撑了当代中国的“民族”性叙述,所以作为民族国家一员的“我”与作为政治性主体的“我”是同一的,作为“人民”的主体便是当代中国的“民族”主体,被呼唤组成“大我”的“小我”们,构成了当代中国的民族。民族的表达方式、民族的共同体认同因此得以落实到具体的人。
集体性抒情主体的构建,也因为与中国固有的文艺形式构成呼应,而参与构建了中华民族历史文化的传承想象。如上文所言,“传统”不是自然而然的存在,它是文化领导权的所有者基于自身需求而对各类文化要素加以筛选后,构建起来的关于自身发展脉络的叙述。中国文学本有抒情,这种抒情不仅可以是“心之忧矣,我歌且谣”“闻君有两意,故来相决绝”式地抒发私人情感,也可以是“靡不有初,鲜克有终”等颂歌式地抒发集体情感,抒情者也不限于个人。但自近代以来,受到西方浪漫主义影响,中国对“抒情”的理解也逐渐窄化为抒发个人情感。若以这样的抒情观来梳理中国文学的传统,不仅中国文学的自身特性会被忽视,中国思想文化乃至政治历史的连贯性也将受到冲击。
近年来对“抒情传统”的研究便显现出这一问题。王德威在总结陈世骧、高友工所梳理的中国“抒情传统”基础上,提出“抒情传统”在中国现当代文学中的传承,并使这一传统与“史诗”传统相对,力图从一个新的维度和脉络上梳理中国文学发展史。36“抒情”与“史诗”的区分源自李欧梵整理普实克选集时作出的区分,他将普实克笔下的“史诗”与“抒情”两个概念,分别定义为代表强调社会性的和强调个人性的两种文学倾向。37王德威提出“抒情传统”时,自言目的在于扭转学界对“抒情”惯有的极端个人主义式的解读,并使之与史传传统相结合。这本应发掘抒情超越个人的可能性,从而关注到20世纪40—70年代文艺中集体性主体的存在,但王德威在整理抒情传统时,仍仅关注传达个体意志的“抒情”,并称能够抒发个人主观意志的作品为“这,才是左翼文学最耐人寻味的抒情理念”38,限定了抒情是个人的表达。他对革命年代的“抒情传统”的挖掘,也是有意识从中选取带有个人性的作品,因此他所勾勒的中国“抒情传统”,便是自传统中国发展到现代中国的个体抒情,遗漏了集体抒情的部分。
姑且不论王德威这种处理是在政治因素影响下的有意为之,39还是西方浪漫主义影响下的抒情观导致他忽视了抒情的多样方式,这个不完整的“抒情传统”都表明若不破除抒情是个人抒情的定见,中国文学的很大一部分将遭到隐匿,自古至今的发展线索就出现了断裂。而五六十年代集体性抒情主体的探索,力图改变现代文学所限定的个体性抒情,通过与中国文艺固有的形式相呼应,构建更为连贯的中国文学传统。《放声歌唱》《十年颂歌》创作的时期,也正是毛泽东提出从“民歌”和“古典”的结合中产生出另一种“新诗”的时刻,40这种另类的“新诗”通过发掘与修改民间歌谣,营造了属于民众的歌声,这也在构造一批群体性的抒情主体。李杨将20世纪50年代末到60年代初的文艺阶段称为“抒情”阶段,并指出这一时期每个抒情主体并不是自然意义上的个人,他们每个人都代表着“人民性”,41这指出了这一时期的文艺探索是构造一种既是个人又是集体的抒情主体,贺敬之笔下既是个人也是集体的抒情主体,也是时代需求下的产物。
还需注意的是,毛泽东提出这种另类“新诗”的探索方向时,也着重强调了它与中国历史文化的联系,所以集体性主体的构建是有意识地对应中国文学传统的,它表明当代中国的文化主体是足以代表中国民族文化的。当《放声歌唱》中“我”吟诵着古人的诗篇,驰骋于中国的大地,“我”就凝聚了中国自古至今的文化,承载起了中华民族数千年的文明。当代中国以此重新梳理了文化的传承,当代中国的“民族”也有了历史性的起源。
结语
安德森指出“民族”是一种“想象的共同体”时,分析了现代印刷技术和阅读行为在构建“想象的共同体”中的重要作用,42揭示了文学艺术对于构建共同体想象的价值;柄谷行人将自己对认知装置的分析与“想象的共同体”结合起来,指出“民族”也是一种认知装置,人因为接收了这种认知装置而认同于“民族”。43贺敬之创作的价值不仅体现在他吸收中外艺术形式来构建出一种当代中国的表达,更体现在他将构建当代中国叙事和形象的题旨与民族形式的探索相结合,形成了一种感知中国的方式,并以之构筑当代中国文化主体。他的创作首先体现出了当代中国构建民族表达的自觉意识,这种表达以当代中国的需求为基础,复合性地吸收并转化了传统与现代、世界与中国等多种要素;他的创作也将当代中国塑造成了超越时空的乌托邦形象,将社会主义建设的理想图景加以形象化和直观化,筑成了新中国神话;这样的形式和主旨,最终通过作用于每个中国人的感知方式得以实现,所以,贺敬之的书写也参与建构了新的文化主体。他的创作折射出当代中国文艺“民族化”探索的实质是引导各种资源去化成“民族”。
1茅盾:《反映社会主义跃进的时代,推动社会主义时代的跃进!——一九六〇年七月二十四日在中国作家协会第三次理事会会议(扩大)上的报告》,《中国文学艺术工作者第三次代表大会资料》,中国文学艺术界联合会1960年编印,第95页。
2 上文提到的茅盾的报告在确定贺敬之“民族化”的成就上具有定性的意义。此外,还有谢冕《论贺敬之的政治抒情诗》(《诗刊》1960年11、12月号合刊)、马畏安、于皿《“走向亿万人的心里……”——评贺敬之的诗》(《社会科学战线》1979年第3期)等评论文章探讨贺敬之的“民族化”问题。更有一些当代文学史教材以“民族化”评价贺敬之的创作,如华中师范学院编写的《中国当代文学》第2册(上海文艺出版社1984年版,第283页),等等。可见,贺敬之创作具有“民族化”的特征得到了普遍承认。
3如茅盾在《人民日报》发表《漫谈文学的民族形式》(《人民日报》1959年2月24日),围绕语言和体裁两个方面分析文学的民族形式;焦菊隐《略谈话剧的民族形式和民族风格》(原刊《戏剧研究》1959年第3期,参见《焦菊隐戏剧论文集》,上海文艺出版社1979年版,收入文集时名为《略论话剧的民族形式和民族风格》)从具体的表演、布景、灯光等实际操作的层面指出了话剧应当学习戏曲经验,建立中国特色的戏剧样式。
4参见贺桂梅:《书写“中国气派”:当代文学与民族形式建构》,北京大学出版社2020年版,第4—35页。
5谢冕:《论贺敬之的政治抒情诗》,《诗刊》1960年11、12月号合刊。
6罗曼·雅各布逊:《论翻译的语言学问题》,谢天振主编:《当代国外翻译理论导读》,南开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13页。
7参见韦努蒂著、香港理工大学翻译研究中心编:《译者的隐形:翻译史论》,张景华等译,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2009年版,第19—20页。
8 茅盾:《反映社会主义跃进的时代,推动社会主义时代的跃进!——一九六〇年七月二十四日在中国作家协会第三次理事会会议(扩大)上的报告》,第95页。
9参见本尼迪克特·安德森:《想象的共同体:民族主义的起源与散布》,吴叡人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
10 茅盾:《反映社会主义跃进的时代,推动社会主义时代的跃进!——一九六〇年七月二十四日在中国作家协会第三次理事会会议(扩大)上的报告》,第88页。
11 参见查明建、田雨:《论译者主体性——从译者文化地位的边缘化谈起》,《中国翻译》2003年第1期;许钧:《翻译的主体间性与视界融合》,《外语教学与研究》2003年第4期;陈大亮:《翻译研究:从主体性向主体间性转向》,《中国翻译》2005年第2期;等等。
12 参见东浩纪:《动物化的后现代:御宅族如何影响日本社会》,褚炫初译,(台湾)大鸿艺术股份有限公司2012年版,第54—57页。
13 谢冕:《论贺敬之的政治抒情诗》。
14 贺敬之:《放歌集》,人民文学出版社1961年版,第20页。
15 同上,第27—28页。
16 同上,第35—36页。
17 同上,第17页。
18 同上,第101页。
19 参见柄谷行人:《日本现代文学的起源:岩波定本》,赵京华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9年版。
20 贺敬之:《放歌集》,第36页。
21 同上,第27—28页。
22 同上,第17页。
23 贺敬之:《放歌集》,第50—51页。
24 同上,第39—40页。
25 同上,第84—85页。
26 李杨:《“时间开始”与“英雄出世”——〈时间开始了〉与二十世纪中国文学》,《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22年第7期。
27 让-吕克·南希:《解构的共通体》,夏可君编校,郭建玲、张建华、张尧均、陈永国、夏可君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第83、88页。
28 贺敬之:《〈白毛女〉的创作与演出》,参看延安鲁艺工作团集体创作,贺敬之、丁毅编剧,马可、张鲁、瞿维、焕之作曲:《白毛女》,新华书店1949年版,第117页。
29 孟远:《歌剧〈白毛女〉研究》,中国人民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05年。
30 姚圣良:《汉代毛女传说及其渊源流变论略》,《河北师范大学学报》2011年第1期;王立、孟丽娟:《染及俗气难为仙——毛女传说的历史演变及其性别文化内蕴》,《聊城大学学报》2004年第1期;孙霄:《从民间传奇到宏大叙事——〈白毛女〉故事的母题、原型及深层结构》,《文艺理论与批评》2010年第6期。
31 参见姚圣良:《汉代毛女传说及其渊源流变论略》。
32 谢冕在《论贺敬之的政治抒情诗》中提出贺敬之笔下的“我”过多而有些不恰当的问题,随后石榕《对抒情诗中“我”的几点理解》(《文艺红旗》1961年第10期)提出不同意见,认为贺敬之的“我”不是用来自我表现,而是能够体现党的光辉形象和革命事业常青的。
33 洪子诚:《个人“本质化”的过程》,《诗探索》1996年第3期。
34 贺敬之:《放歌集》,第51—52页。
35 同上,第76—77页。
36 参见王德威:《抒情传统与中国现代性:在北大的八堂课》,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0年版;王德威:《史诗时代的抒情声音:二十世纪中期的中国知识分子与艺术家》,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9年版。
37 普实克:《抒情与史诗——中国现代文学论集》,李欧梵编,郭建玲译,上海三联书店2010年版,“序言”第2—4页。
38 王德威:《抒情传统与中国现代性——在北大的八堂课》,第59页。
39 关于王德威提出“抒情传统”的政治背景,李杨《“抒情”如何“现代”,“现代”怎样“中国”——“中国抒情现代性”命题谈片》(《天津社会科学》2013年第1期)、贺桂梅《“抒情传统”论述的文化政治及其启示》(《汉语言文学研究》2017年第3期)等论文已进行过充分分析。
40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7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版,第124页。
41 李杨:《抗争宿命之路——“社会主义现实主义”(1942—1976)研究》,时代文艺出版社1993年版,第168页。
42 本尼迪克特·安德森:《想象的共同体:民族主义的起源与散布》,第32页。
43 柄谷行人:《日本现代文学的起源:岩波定本》,第205页。

微信扫一扫|长按识别,进入读者交流群
|
|
|
|
|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