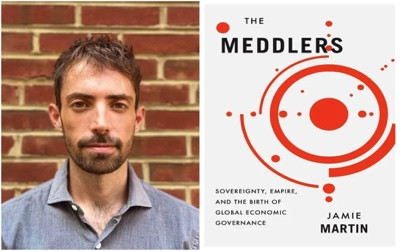美国教授:美国主导的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体系烂到根了!
图为网站文章截图
图片来源:https://www.thenation.com/article/culture/the-rotten-roots-of-global-economic-governance/
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腐朽根源
作者:丹尼尔·斯坦梅茨-詹金斯(Daniel Steinmetz-Jenkins)
译者:何伊楠
图为本文作者丹尼尔·斯坦梅茨-詹金斯(Daniel Steinmetz-Jenkins)
图片来源:http://danieljenkins.me/
杰米·马丁与他的新书《干涉者:主权、帝国和全球治理的诞生》(The Meddlers: Sovereign, Empire, and The Birth of Global Governance)
图片来源:https://www.thenation.com/wp-content/uploads/2022/06/Jamie_Martin-Meddlers-qa_img.jpg
长期以来,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因对许多国家的国内政策施加繁重的影响而受到批评。特别是自上世纪90年代以来,它们一直因向附属国施加政策(如结构调整改革和紧缩措施)而受到严厉批评,这些政策加剧了南半球国家的不平等,反过来又使强大的北半球国家受益。我们如何理解这种全球失衡的结构性根源?一种相当标准的观点是,将责任完全归咎于新自由主义。这种观点认为,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这些可以追溯到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机构——一度允许在布雷顿森林体系的全球货币管理下建立一个更公平的经济治理体系,而这在20世纪70年代初崩溃。这种观点认为,自由市场经济政策开始占据主导地位。在罗纳德·里根和玛格丽特·撒切尔当选领导人巩固了这些制度,并在整个20世纪80年代朝着明显的新自由主义方向发展。到了20世纪90年代,民主党已经与这场意识形态革命和解了。在比尔·克林顿的领导下,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进一步采取了经济休克疗法。就这样,转向新自由主义被认为是第三次世界债务危机、1997-1998年亚洲金融危机、以及苏联解体后对俄罗斯和前东欧集团国家的掠夺的罪魁祸首。
然而,杰米·马丁(Jamie Martin)在他的新书《干涉者:主权、帝国和全球治理的诞生》(The Meddlers: Sovereign, Empire, and The Birth of Global Governance)中对这种标准叙事提出了挑战。即将成为哈佛大学历史与社会研究助理教授的马丁认为,如果我们真正想要理解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干涉主权国家国内政策的灾难性后果,就有必要了解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出现的国际联盟和国际清算银行等最早的国际经济治理机构。这些机构赋予了公务员、银行家和来自欧美的殖民当局执行紧缩政策、监督发展项目和调节商品价格的非凡权力,他们中许多人都有用来为干预其他国家的经济辩护的文明的、家长式和白人至上主义的假设。马丁认为,考虑到欧洲帝国的衰落和越来越多的人要求自决,这些机构实际上是将19世纪的金融帝国主义实践重新包装成一种新的、更干净的形式。在做出这一分析时,马丁为当今全球经济治理危机提供了另一种视角,显示了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的干涉主义权力如何一直植根于帝国主义和殖民主义。
我和马丁聊了聊他对帝国与当代全球经济治理关系的思考、为什么布雷顿森林体系会被误解、他对新自由主义的定义、以及他眼中对“干涉者”有吸引力的替代性经济方案。为了篇幅和清晰度,本文对这段对话进行了编辑。
——丹尼尔·斯坦梅茨-詹金斯
DANIEL STEINMETZ-JENKINS(丹尼尔·斯坦梅茨-詹金斯,以下简称DSJ):批评人士通常会从全球化的角度来考虑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和世界贸易组织的经济政策。最典型的是在20世纪90年代,这些机构通过强制紧缩、结构调整改革和其他经济休克疗法,给南半球国家和前东欧集团国家造成了严重破坏。这些政策经常被批评侵犯这些国家的主权。而你的书反对这种叙述,因为你不认为这些政策是20世纪70年代所谓的新自由主义革命的结果。为什么会这样呢?
JAMIE MARTIN(杰米·马丁,以下简称JM):我们将其与华盛顿共识联系在一起的那种影响深远的国际经济机构的干预力量——强制借款国实行紧缩并要求它们实施广泛的自由化改革——并不是在20世纪后期突然出现的。相反,它们起源于几十年前的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时,当时强大的国家和私人行为体在全球经济和政治巨大动荡之际建立了新的伙伴关系,以保护自己的利益。
的确,在上世纪80年代和90年代,国际货币基金组织通过向借款者提供援助以承诺进行广泛的市场改革为条件,大幅扩大了其影响力。这发生在布雷顿森林体系结束后连续三个全球动荡时期:第三次世界债务危机、苏联解体和1997-1998年的亚洲金融危机。在每一个时期,国际货币基金组织都对接受贷款的国家——从阿根廷、哈萨克斯坦到泰国——施加了巨大的压力,要求它们承诺紧缩财政,并对国内经济进行重大改革。不同意这些条件不仅危及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援助;它还危及获得其他外国资本来源的机会,因为其他贷款机构利用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事先安排来确定一个国家的信誉。正是因为干涉主权国家的国内事务,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变得臭名昭著,其目的是让美国主导下的超自由化资本主义形式全球化。
我们有充分的理由将强大的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出现与同时期的新自由主义革命联系起来。毕竟,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当时坚持在南半球和后共产主义国家推行的市场改革,与当时在美国和欧洲实施的改革相同。考虑到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由美国财政部主导,在俄罗斯或印尼等地,经常是同一群人在监督美国经济的转型,同时也在呼吁他们这样做。
但这种情况已经不是第一次发生了。第一次有国际机构以紧缩和央行独立性为条件,提供救助贷款是在20世纪20年代,国际联盟在前哈布斯堡(Habsburg)和奥斯曼帝国(Ottoman)的土地上所做的。这需要采用19世纪由欧美投资者和政府建立的半殖民债务委员会所使用的方法,以约束北非、巴尔干半岛、拉丁美洲、加勒比地区以及中国和奥斯曼帝国的借款人,并从他们那里获取收入。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前的这些非正式金融帝国主义工具和战后全球经济治理的出现之间,存在着深刻的连续性。
在20世纪40年代初设计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时,一些设计师坚持认为,这个新机构必须放弃这些明显的帝国主义做法。他们不希望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威逼各国削减预算,放弃战后福利计划,他们还同意政府应该被允许保护其公民免受资本主义繁荣与萧条周期的影响。这就是为什么今天人们如此怀念布雷顿森林体系,以及为什么它经常被描述为新自由主义的解药的原因之一:因为,回顾过去,它的创始人似乎相信,有必要将温和形式的全球化与国家福利主义和凯恩斯主义的经济管理进行人道和解。
但事实上,在二战结束、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开始向第三世界成员国提供第一批贷款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中最强大的美国行为体几乎没有真正致力于这一愿景。早在冷战初期,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就开始像早期的帝国债权人安排一样,以紧缩和反通货膨胀政策作为贷款的条件,开始于墨西哥、巴拉圭和智利等拉丁美洲国家,然后更广泛地遍及整个加勒比地区和非洲的后殖民国家。因此,这些实践并没有随着新自由主义的兴起而重新出现。
DSJ:从你对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历史的另类描述中,你得出的主要结论是什么?
JM:这段历史的一个关键结果是,给今天的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可能会放弃其对附加条件的坚持的想法泼了一瓢冷水。我们有充分的理由认真对待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近期经济理念的变化——从强调解决不平等问题,到对使用资本管制的谨慎支持。但是,即使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正式放松了对一些新自由主义思想的采纳,该机构仍将其对脆弱成员国的援助与同样的紧缩要求联系在一起,包括最近在新冠肺炎疫情期间提供的一系列紧急贷款。将这些实践视为20世纪末的创新表明,随着新自由主义思想的转变,它们可能很容易被抛弃。但如果你把它们视为拥有一个多世纪历史的金融治国方略的延伸,那么就会明白,为什么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继续对理论经济学和政策制定中的范式转变无动于衷。
DSJ:您能解释一下您的“干涉”概念吗?具体来说,它与您书中出现的一个主要紧张关系——以国际联盟为代表的一战后民族自决的兴起与威胁国家主权的全球资本主义经济体系之间的冲突,有什么关系?您能详细解释一下这种紧张关系吗?在何种意义上,解决这场冲突的新的国际主义解决方案包含了对帝国的重塑?
JM:书中探讨的干涉的概念是指外部行为体对主权国家的国内政策、制度和法律所行使的一种权力。一个例子就是当像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这样的机构坚持要求成员国削减预算或取消对议会的控制,以换取贷款时所施加的权力。我的书讲述了这种权力从19世纪到20世纪如何演变的历史,以及它如何在这个过程中改变了国家地位的意义。
现在,重要的是要记住,这种干涉所涉及的主权丧失,与一个国家签署条约、采用金本位制的束缚、或邀请外国专家帮助进行国内改革不同。我感兴趣的干预是指一个国家被外部强大力量所强迫,让强大的外国行为体来塑造国内的制度和政策——无论是在19世纪以军事干预的威胁,还是在20世纪被切断与国际资本市场的联系。
从长远看,这有助于理解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等机构所行使权力的激进本质,以及它为何会产生这样的阻力。免受外部势力干涉国内政策和制度的保护,与现代主权概念本身是一致的——即使在实践中,历史上只有最强大的国家才享有这种保护。直到19世纪,宗教、王朝继承和宪法问题被认为是最重要的需要保护的问题。但到了20世纪初——经济快速全球化的时期——经济政策也被视为需要这种保护。
以贸易为例:虽然许多贸易协定是在19世纪签署的,但关税被视为严格的国内政策,尽管它们会影响其他国家的经济福祉。很少有人记得,国会拒绝让美国加入国际联盟不仅仅是出于某种普遍的孤立主义情绪,而是出于一种非常具体的担忧:担心国际联盟会干预美国国内政策中最受争议的两个领域,关税和移民。公共财政也是如此:一个国家如何选择向公民征税和如何使用财政收入,是其主权最基本的表现之一。在20世纪初,任何一个允许他人决定其财政体系的国家,都不再被认为是一个完整的国家,而是一个准主权或半殖民政体,就像当时的中国或埃及。
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当全球经济治理机构开始出现时,它们面临的政治问题是能否干预这些国内政策和机构。很明显,治理全球资本主义不仅可以包括管理国家之间的关系,比如防止一个国家与另一个国家发生战争;它还可能涉及权衡敏感的国内经济问题。但这些机构必须努力行使这些干涉主义权力,而不是让其看起来更像是帝国长期以来对全球经济边缘国家的欺凌。
现在,毫无疑问,像国际联盟这样的新的国际机构正在继承旧的帝国主义实践。毕竟,国际联盟中最强大的成员是两个庞大的殖民帝国英国和法国。但是在一个要求自决的时代,自治政体(self-governing polities)——尤其是那些刚刚赢得独立的国家,比如波兰和阿尔巴尼亚——不希望像19世纪那些贫穷的、半主权的债务人那样被颐指气使,不断受到债权人的监视,而不能完全控制国内政策。
国际机构的目的是通过向行使这些权力的国家提供正式代表,使这种情况不那么尴尬。通过这种方式,这些机构将成为合法化的机器——在一个要求自决的时代,使主权国家更容易容忍古老的帝国主义实践。但即使是在这种经过净化的新形式下,这些权力在任何需要它们发挥的地方都产生了巨大的阻力。
DSJ:我们今天如何看到类似的动态仍在发生?
JM:从上世纪90年代末开始,在接受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纾困的后果变得清晰之后,越来越多的国家远离了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对于俄罗斯、中国、韩国和土耳其等“新兴市场”经济体来说尤其如此,这些国家已经发展出应对金融不稳定的方法,不再需要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援助。这并不是因为所有这些国家都在对新自由主义发动战争;远非如此。以普京领导下的俄罗斯为例,该国长期致力于一种极其保守的财政约束形式,并以拥有一个由最现代的技术官僚经济学家组成的央行而自豪。这个时代的俄罗斯绝不会允许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告诉它要致力于这些政策,尤其是考虑到俄罗斯在苏联解体后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打交道的经历。允许一个由美国财政部主导的机构对其国内事务进行这种干预,无异于承认由于输掉一场战争而丧失了某种主权。在某种程度上,我们可能会将普京的崛起视为俄罗斯自治和文明威望的保护人,这是对上世纪90年代允许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这样的机构如此深入地介入俄罗斯国内经济和政治所带来的羞辱的直接反应。
我写这本书的目的之一,就是要说明这种动态的历史有多悠久。即使是那些已经接受了自由改革或财政紧缩必要性的国家,在外部强大力量要求它们这样做的时候,也总是不愿做出承诺,除非是在严重困难的时候。接受国际联盟或后来的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这样的组织的纪律,对某些政治行为体来说当然是有战略意义的——例如,放弃实施财政紧缩的决定,往往是政府为了阻止国内的反对而做的。但这样做总是有政治风险的,因为它可能被视为将一个特定的国家转移到全球等级体系的较低级别,并被视为一种放弃自主权的行为,这可能会导致国家地位本身的丧失。在这一基础上建立可行的国际合作构想是极不可靠的。
DSJ:你能精确地指出这些最早的国际经济治理机构的文明、种族和文化等级吗?反过来,它们又是如何进入1944年7月的布雷顿森林会议,从而导致了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的成立的?
JM:在20世纪初,许多拥有正式主权的国家的国内事务受到了广泛的不必要的干涉,这些干涉有很多种形式。在埃及和尼加拉瓜等借款国,外国经营的委员会控制着资产并制定政策;其他国家,如中国和暹罗,则失去了自己设定关税的权力。在许多国家,自然资源和土地为外国行为体所有,央行由外国董事控制。像海地、利比里亚、伊朗、墨西哥、希腊和许多其他国家,并没有看到他们的法律主权转化为不受外部强制的真正自治。
许多人清楚地意识到这一矛盾,试图以各种方式证明它。对这种主权不平等有明显的种族主义辩护——一些人认为真正的自治权和经济自决实际上只属于西方以白人和基督徒为主的国家。从发展的角度来看,也有这样的理由:新独立的国家需要外国的指导,使他们走上通向“负责任的”政府和经济发展的道路。这也是一个根据国家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选择的立场来评判国家的时代。并非巧合的是,正是在这场战争的输家——奥地利、德国和匈牙利——发展出了一些最早的、最具干涉主义的国际经济治理工具。但这些工具的反对者也同样诉诸于想象中的文明等级制度。20世纪20年代,从德国或奥地利这样的国家的有利地位来看,反对外部干预被所有信奉意识形态的政治行为体描述为防止该国沦为像中国或希腊那样的主权国家的关键,但他们的国内事务总是受到屈辱性的干涉。
DSJ:考虑到美国崛起为一个经济和军事超级大国,这种等级制度在什么意义上被修改了?美国从两次世界大战之间英国和法国的干涉中学到了什么?二战后,美国干预英国和法国的经济,英国和法国又以何种方式尝到了“自食其果”呢?
JM:关于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布雷顿森林体系的起源,有一个众所周知的故事。1944年,来自44个国家的代表在新罕布什尔州的华盛顿山度假村开会,重新制定国际经济规则,并创建了两个新的机构——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来管理战后世界经济。在大多数解释下,这一进程涉及一个衰落的大国——以约翰·梅纳德·凯恩斯(John Maynard Keynes)为代表的大英帝国和一个崛起的大国——以财政部经济学家哈里·德克斯特·怀特(Harry Dexter White)为代表的美国——之间令人担忧的谈判,最终达成了有史以来最伟大的国际协议之一。
但布雷顿森林体系充其量是一项喜忧参半的成就。诚然,美国在提供全球公共产品和对抗危机方面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承担了更多的承诺。但作为两个布雷顿森林体系中更重要的机构,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设计初衷就是要由美国主导——甚至比在此之前英国对国际联盟的主导作用还要大。当英国人开始正视这一事实时,他们开始担心,被战争削弱的英国现在面临着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干涉其内政的风险,就像英国长期以来在巴尔干半岛、中东和其他地方所做的那样。英国官员担心,在美国眼中,英国正堕落到那种长期受到美国官员和银行家对其事务干预的“没有责任感”的债务国的水平。这是旧时代动态的重演:在20世纪20年代的德国和奥地利,同时代的人不断提到英国和法国对待这些国家的方式,就像这些帝国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对待奥斯曼帝国和中国一样。
凯恩斯孜孜不倦地努力阻止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发展这些干涉主义力量——不是出于对普遍主权平等的承诺(他在布雷顿森林会议上对拉丁美洲和非西方国家的代表团大多不屑一顾),而是因为他担心削弱了的英国现在很容易受到美国的干涉。就在布雷顿森林会议召开的几天前,他向罗斯福政府的同僚们阐述了这一点。他问道,如果一个国际机构告诉美国,它负担不起新政,他们会作何感想。
在布雷顿森林会议上,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是否能够做到这一点还没有定论。凯恩斯自信地认为,他赢得了华盛顿的承诺,即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不会告诉议会它负担不起贝弗里奇计划(Beveridge Plan)。但在会议结束后不久,凯恩斯意识到他输掉了这场斗争:美国主导的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显然能够将其援助与借款者对国内政策的广泛需求联系起来。果然, 1946年凯恩斯去世后不久,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一开门,其英国和法国成员国就发现,这不是他们当初签署的机构。命运发生了巨大的逆转,那些干涉者现在冒着成为被干涉者的风险。但最终,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发展出最具干涉主义色彩的力量并不是在西欧,而是在南半球。
DSJ:上世纪六七十年代,南半球的代表是如何应对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的干预的?例如,最近有很多关于这个时期出现的国际经济新秩序的文章。它希望达到什么目的?
JM:在南半球国家的代表看来,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在冷战期间附加条件的演变,与这些国家长期面临的许多其他类型的外国干涉类似。因此,这些国家(通常得到苏联的支持)最一致地主张所有国家都有权享受不受其他国家干涉的保护。这成为联合国的核心要求,并包括在20世纪70年代初推动建立国际经济新秩序的进程中。这方面的主要例外是南非的种族隔离制度和美国的吉姆·克劳法(Jim Crow),它们被视为不应隐藏在主权墙之后的国内法律和制度安排。但在经济问题上,南半球国家对反干涉主义的强调是一致的。
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内部,围绕这个问题的冲突早在“华盛顿共识”兴起之前就开始了。早在上世纪60年代,第三世界国家的代表就对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干预主义的双重标准和不对称性产生了越来越强烈的反对。1967年,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援助了英国,但对英国的政策提出的要求却几乎没有对其他成员国(比如南美)的政策提出的要求那么多,之后这种反对达到了狂热的程度。正如阿多姆·格塔丘(Adom Getachew)和克里斯蒂·桑顿(Christy Thornton)等学者所证明的那样,早在冷战之前,南半球的官员和活动人士就有一段试图在高度等级化的国际体系中使主权平等成为现实,但没有呼吁完全退回民族主义的漫长历史。同样,对有条件贷款的反对也比上世纪90年代全球抗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浪潮出现得早得多。
DSJ:请您详细解释一下您之前提到的问题。在《干涉者》一书的结论中,您指出,“这本书中讲述的历史表明,21世纪初全球治理的挑战比嵌入自由主义(embedded liberalism)及其崩溃为新自由主义的程式化历史所暗示的更重要。”这是对自由主义的一般控诉吗?自由主义和帝国是紧密联系的吗?
JM:如果我们过于关注新自由主义的相对较近的历史,我们可能会忽略全球资本主义和帝国关系中的更长期演变。我们没有意识到,我们继续生活在一个由非正式的金融帝国主义的旧实践塑造的世界中,这些实践至少可以追溯到19世纪中期,并且存在于许多种类的自由主义之下,这些自由主义往往被历史学家和社会科学家整齐地分为古典自由主义、“内嵌自由主义”、新自由主义等等。结构性调整并不仅仅是帝国的“远亲”,而是它的“直系后代”。
DSJ:我最近采访了加里·格斯尔(Gary Gerstle),他关于新自由主义兴衰的新书中特别指出,像“嵌入自由主义”这样的东西确实崩溃成了新自由主义,并最终导致了新政秩序的崩溃。格斯尔也主张以全球视角看待问题,但他认为新自由主义秩序的兴起与苏联的垮台是不可分割的。不过,你如何从你在书中提出的全球视角来解释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新政”(在北大西洋彼岸也有类似情况)逐渐被削弱的现象?
JM:一般来说,对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干预主义的描述集中在从冷战早期的凯恩斯主义共识到20世纪末的新自由主义的转变上。按照这种说法,布雷顿森林体系用一种新的国际体系取代了两次世界大战之间的金本位制,这种体系允许各国有更多的自主权来推行扩张性政策,建立福利制度,并使其公民免受经济危机的影响——所有这一切都无需诉诸于20世纪30年代摧毁世界经济的那种竞争性民族主义。爱沙尼亚经济学家拉格纳尔·努尔克塞(Ragnar Nurkse)的洞见经常被用来概括这一创新:世界经济现在是为了国内的社会和经济优先事项治理的,而不是反过来。政治学家约翰·鲁吉(John Ruggie)在1982年将这种安排描述为一种“嵌入自由主义”的妥协。
但这种叙述是建立在对20世纪中期的一种虚构的描绘之上的。这种自治是一种奢侈,很少有国家能负担得起。这并不是说新自由主义是不存在的,也不是说战后存在的社会民主安排的破坏不是一种具有世界性后果的重大政治发展。远非如此。但我认为,我们应该谨慎地避免怀念战后的那个时刻,那时社会民主是安全的,国家可以控制自己的经济命运,福利主义是充满活力和普遍的。我们非常清楚,在国家层面上,这是一个多大的神话。
在美国历史学家看来,“新政”国家核心的种族主义妥协和结构性矛盾是显而易见的;同样显而易见的是,凯恩斯主义在战后的美国并没有像许多人想象的那样成为一种共识。我想让我们看到的是,我们也应该警惕使用嵌入自由主义的概念来描述1945年之后的全球秩序,除非我们指的是北大西洋的少数相对富裕的国家在一段短暂的时间内经历的。显然,世界上大部分地区仍然生活在殖民帝国的疆界内,很少有国家实现了“旗帜独立”,并在实践中转化为强大的自治。嵌入自由主义可能是美国和英国官员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经常谈论的东西。但在1945年之后,它并没有成为全球秩序的一种组织逻辑,尽管我们希望它已经成为,也希望今天它能以某种方式被重新利用。
DSJ:我们可以考虑哪些历史上的替代方案(没有走过的道路),让我们重新思考国家和国际之间的关系,从而战胜今天的干涉者?
JM:我们应该鼓励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进行改革,很明显,新的想法正在该机构生根发芽。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一些官员对此表示欢迎,他们认为该机构在上世纪90年代做得过头了,而且没有附加条件的贷款形式,比如特别提款权,在该机构的“工具箱”中占有一席之地。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正在努力改革其对待债务国的方式,特别是通过减少惩罚性附加费。如果G20不被大国竞争完全束缚的话,它就有领导主权债务减免方面的集体努力的潜力。尽管目前正处于全球危机的时刻(或者正因为这场危机),但现在正是就如何改革国际经济机构展开充满活力和富有成效的讨论的时候。
但我也认为,我们需要避开达成“新布雷顿森林体系”的想法,因为这经常是这些改革呼吁的口号,或将我们的雄心限制在对现有机构进行调整上。这些机构是在帝国仍被视为全球秩序理所当然的组织原则的时代设计的,其建立是为了确保一个大国的主导地位。我们需要从下至上,创造性地思考,在我们多极而不稳定的世界秩序中,什么样的机构可能真正发挥作用:那些能够实现无论是减少全球不平等还是减缓气候变化的集体目标的机构,而且是各国满怀热情地期待,而不仅仅是迫于压力的机构。
我不知道这到底会是什么样子。但我认为这是一项长期的努力,需要涉及学术、政治和社会运动的多个领域。我发现,如果我们不能对我们面临的生存挑战做出集体反应,就很难想象地球上的生命会像我们所知道的那样继续下去。但是,如果不考虑我们是如何走到今天这一步的,以及在追求新的、更公正的国际合作形式的过程中需要如何不断克服帝国的遗留问题,我们就无法开始想象什么在政治上是可行的。

微信扫一扫|长按识别,进入读者交流群
|
|
|
|
|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