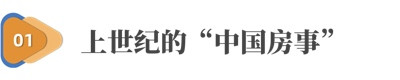何以为家:中国租房人的昨天、今天和明天
公元803年,一个后生考中了进士,待业三年终于得到一份“校书郎”的工作,相当于在唐朝中央文献研究室当研究员。
每月一万六千钱的薪水,让他只敢在长安五环外的长乐里,租四间茅草屋。
存钱二十年,仍买不起长安房子的他,无奈写下“长羡蜗牛犹有舍......且求容立锥头地”的感慨。
这位后生,正是唐代大诗人白居易。
但白居易好歹还有份不错的差事,有马代步、有两个仆人。他的前辈杜甫,就只能在秋风瑟瑟中,孤零零地大呼“安得广厦千万间”。
千百年来,“安居”都是一个奢侈的梦想。
民国年间社会动荡,大多数人不敢买房。这造就了租房市场的兴盛。
当时的上海有三百万居民,租房住的有二百万。作家郭沫若就曾携妻带子租住亭子间,跟石库门里其他租户共用一个厨房、一个水龙头。
郭老推开西窗,邻居家的客厅立马暴露在眼前:锅碗瓢盆、孩子吵嚷,各种杂音像环绕立体音响,以至于“刚一动笔,脑子里乱打架”。
散文家梁实秋也有类似经历,他在《亭子间生涯》里吐槽:“厨房里杀鸡,无论躲在哪一个角落,都听得见鸡叫。厨房里烹鱼,可以嗅到鱼腥。”
名人尚且如此,贩夫走卒的居住状况,可想而知。
他们住不起正经房子,只能住月租一块多钱的小棚子。这些小棚子一个个连在一起,组成棚户区。1950年的调查显示,上海棚户区居民占上海人口的1/4强。
▲上海窝棚
来源:上海历史展览馆
进入新中国,万象更新。
房屋被纳入公有范畴,城市实行“统一管理、统一分配、以租养房”的福利分房制度。即城镇居民的住房,主要由所在单位解决,并以极为低廉的价格分配给职工居住。
30平方米的房子,月租金也不过三四角,只相当于一斤猪肉的价格。
1961年,住在上海里仁坊居民楼的阿三在一篇题为《我的住房》中激动地写道:
“我今年六十五岁了,在旧社会吃尽了苦头。因为缴不出房租,被赶出流落街头。只好去住放死人棺材的‘会馆’,里面阴森森的黑得怕人……我现在住的是一所很好的朝南楼房,有玻璃窗,空气流通,阳光充足,冬天暖洋洋,夏天凉风徐徐吹来,真叫人舒畅。”
这样的文章屡见报端,当时的《杭州日报》甚至开出专栏,呼吁大家“不忘旧社会住房子的苦,珍惜新社会住房子的甜”。
分到一套房子,是当时城镇职工最具幸福感的人生大事。以至于到九十年代末,人们进城找工作时,仍然不忘问上一句:“你们这个单位分房吗,什么时候分?”
但免费的午餐,喂不饱疯狂增长的人口需求。
1950年到1977年,国家投资建设住宅面积为4.93亿平方米,年平均建房约1826万平方米。对应的中国人口,却从5.41亿增长到9.37亿,净增73%,城镇人口更是翻了一番。
尽管新增建设面积,相当于给每个城镇新增人口建设住房9.42平方米。但相比于1949年人均8.3平米的城镇住房面积,1980年反而滑落到7.18平米。
人口密集的上海,尤其突出。
9平米住一家三代8口人、全家住在一个直不起身的阁楼……这些故事,几乎人人熟知。在80年代末,人均2平方米以下的家庭,全上海有几万户。
如何解决住房需求?这个难题,并没有在领导人的考虑范围之外。
1978年10月,在视察了几十栋北京新建的公寓住宅楼后,邓小平忽然问身边的同志:“居民住房可不可以成为商品?”
这个问题,当时没人敢回答。
但随着时代前进,房改的路子,却慢慢走了起来。在国家突破了福利分房制度后,又融入公房补贴出售政策,回收资金用于新的房屋建设。
1986年,提租补贴方案开始试行。月租金由原来的0.07-0.08元/平方米,提高到1元以上,相当于成本租金的80%左右。
沈阳市北制药厂按此方案,每年回收125万元用于再建房,然后以优惠的商品房价格出售给工人。第一年150套的名额,就有超过500人申请。
1998年,被称为中国住房制度改革里程碑的国发〔1998〕23号文件出台,宣告了福利分房制度的终结和商品住房制度的开始。
这一年,户籍制度进一步松动。
“凡在城市有合法固定的住房、合法稳定的职业或者生活来源,已居住一定年限并符合当地政府有关规定的,可准予落户。”
房地产逐渐成为支柱性产业,但浪潮卷起的,还有浩浩荡荡的“进城大军”。
农民工,是中国现代化进程中绕不开的群体。
农民工这个词的第一次出现是在1965年,作者于嘉珍在《黄河建设》上发表了一篇文章,提到“农民工”是黄河修堤岸中的擎天柱。
改革开放之后,城市经济引擎启动,市场对于增量劳动力的需求持续扩张。根据农业部统计数据显示,从1984到1988年,非农转移的农村劳动力数量由2161.4万上升到8611万。
农民工来到城市,首先面对的问题并不是工作,而是住所。
工厂为了招揽劳动力,往往会提供集体宿舍来吸引工人。但集体宿舍的生活,常常不是美好的回忆。
1976年出生的工人老赵,在工厂集体宿舍住了十年。他至今记忆犹新的,仍然是住宿舍的人,每天为了抢水吵架乃至大打出手的样子。
水龙头的开关大权由厂方掌握,为了节约用水,只在晚上8点到10点开放大水流。无论是早上洗脸刷牙,还是晚上冲凉洗衣服,工人在为数不多的水龙头前排队是日常。
生活的不便,远不止这些。
虽然居住成本低,但用电、用网等都有限制。七八个甚至更多人挤在同一间房,没有成人的私人空间可言。而一些建筑工地搭建的简易铁皮房,更是“冬冷夏热”。
不舒服还是其次,不自由更令人感到压抑。
以拥有45个工厂和近67万员工的富士康为例,有学者研究过里面工人的宿舍生活后,直言“宿舍就是生产管理的延续”。
虽然园区里银行、医院、邮局、超市、网吧、健身房等公共设施一应俱全,俨然一个小城镇。但这个“城镇”,既封闭,规矩又多。
2011年的一份问卷调查显示,富士康85%以上的工人每个月休息4天或少于4天。
为了减少洗衣晾衣时间投入,员工不能自己洗衣服,由富士康进行统一洗衣服务;宿舍里不能抽烟、喝酒、打牌,进出宿舍楼都要刷卡。
一位廊坊的工人表示:“如果连续3天不刷卡,就默认没回宿舍睡觉。”惩罚方式,是取消床位,得自己去外面租房住。
大概为防止工人之间过于熟识,抱团闹事。工厂还会通过将老乡分散安排住宿的方式,将其社会关系切割开,并限制随意串门。
缺乏娱乐、进出自由和人际交往的生活环境,很容易带来紧张的压抑感。久而久之,大家都感受不到集体生活的热闹,唯一想法就是“里面人际关系太冷淡,找不到倾诉对象”。
大量远离家乡的“时代淘金者”,则形成现代安居史上,另一特色鲜明的群居景观——城中村。
1995年,从北京天安门广场南行5公里,刚跨过南三环,就会被甩入一个“拥挤而又奇幻”的漩涡。
这里人来人往、南腔北调。打扮光鲜、拿着大哥大,开着奔驰丰田的生意人,竟和拎着大包小包的打工仔,都住在临时搭建、简陋拥挤的小平房里。
这就是“浙江村”。
80年代以后,浙江温州地区进京经商的人,在这里自发形成了聚集区,以服装生产和销售为主。
生意人多了,生活需求自然增多。于是,卖水晶糕的、美容美发的、做海鲜生意的,都蜂拥而至。
生意门店多了,用工需求也增长起来。
从经商人的亲戚朋友老乡,到打工人的亲戚朋友老乡,逐渐枝分叶散。不过几年,外来人口已经有10万之巨,是本地人的五六倍。
整个社区变成了以温州人为中心,当地村民纷纷搭建房屋出租。以至于北京丰台区政府曾在一份正式文件里,开篇指出:京城人不知南苑乡者有之,不知“浙江村”者无几。
1988年,嫁过来十几年的马村居民李桂芝,把丈夫家的小四合院出租。原本3个人的屋子,硬是挤进了8户温州人,变成了40多人共同居住。
在英国牛津大学社会人类学教授项飙的记述中,李桂芝讲起出租致富之道:“还是我们那口子有眼光,花了两千多块钱,又搭起了三间小房。”
八间房子的租金,一个月可达2000多元,而李桂芝夫妇的工资加起来还不到1000元。
但这并不意味着,本地人就很欢迎外来人。
住在大红门后街的居民董帅前抱怨道:“浙江人来了,是活跃了经济。但这社区也变乱了,有的仗着人多,房租说不给就不给。更不用说这卫生,大红门都快成尿盆街了,你看这厕所脏的,都踩不下脚!”
这其实与个体的素质关系有限。自发聚集的社区,往往缺乏公共规划、公共管理和公共服务的投入,脏、乱、差,似乎是难以避免的结局。
远在两千多公里外的广州羊城村,同样如此。
“村里对外来人还是很有成见的,因为治安差基本都是外来人在闹事”,1997年搬来的湖南销售员孙某如是说。
更令他感到麻木的是:“我在这里住了5年,基本上很少和村民来往,就是一种房东与房客的关系。”
这几乎是城中村的常态,外来人员多是为了致富或生存,打工赚钱是第一动力。对于背井离乡的他们来说,身在异乡为异客,无论外面的世界多么繁华,他们终究要落叶归根,也就无意在临时驻扎的城中村里,结交工作、生意之外的朋友。
房东眼里,外来人只是“流动的人口”。保持简单的经济来往关系,反而收租更省心。
在浙江村,很多房东把所有房子都租出去,自己则远离这片被外地人“侵占”的领域,仅每月来收一次租金。
这样的场景,至今仍然在现实中上演。
到2019年,深圳只有16%-17%的房子是商品房,超过60%是城中村的租赁房,还有超20%是工厂提供的集体宿舍。
工厂集体宿舍里,找不到家庭的温暖,一切都是为了生产做准备;城中村里,房东与房客的关系往往形同陌路,外来群体聚集地像是城市中的孤岛。
他们无法融入这里,他们只是漂泊的外乡人。
2009年,一部电视剧大火。
剧情讲述了1998年大学毕业的郭海萍和苏淳,拖着行李来到江州市。并在只有10平方的老式建筑里租房而居,为买房上演了一出出悲欢离合。
这部叫做《蜗居》的电视剧,正如它的名字,像一根针刺到了当代青年的生存隐痛。
1999年,国家通过高等教育扩招政策。到2003年,中国普通高校本专科生在校人数超过1000万。
蓝领不再是进城谋生的唯一主角,受过高等教育的年轻人,怀揣着梦想蜂拥而至“北上广深”。
1997年5月,丁磊在广州8平米的出租屋里,拉着三个人创建了网易公司;非典时期,刘强东亏掉了几乎所有的钱。他只能将自己关在北京的出租屋里,边吃泡面边思考未来。
他们是时代的幸运儿,寒微时的租房经历,反而成为人们津津乐道的大佬往事。
但更多的普通人,无论是专科本科还是985、211院校毕业生,大多面临着相似的情况:饱和的就业市场和低廉的薪资。
根据2006年中国社科院发布的“蓝皮书”预测:2007年,中国城镇需要就业的人口将超过2500万人,而新增加的就业岗位加上自然减员一共只有1000万个。
这种窘迫,使他们在选择住址时,不得不优先选择租金便宜的城乡结合部或近郊农村,作为初入社会、人生落脚的第一站。
2007年,位于北京西北五环外的唐家岭,曾经居住着四五万“北漂”的年轻人。
他们平均工资在2000元左右,人均月租金则达377元。加上水电费,意味着约工资的20%都要用于住房。
他们的居住面积,大多不足10平米。简单的房间里,通常只有一个床位和一个桌子,再无其他。
他们每天吃两顿饭,坐两个小时公交车通勤,从家到公司两点一线。只为了一个简单的梦想:月薪能够涨到七八千元,存点钱回家买个房子。
在接受北京大学政治学博士廉思访谈时,一个在小公司做财务的湖北女孩何易,慷慨激昂地宣告“以我现在的资本,当然很难。但是只要我破釜沉舟考过注册会计师,这个目标就很容易实现了。”
广告设计专业的梁亦娴,则自信地说:“我的能力比较强,另外我很细心,就算是去做扫地这样的工作,我也一定比别人扫得干净。”
廉思在其调查中,将这群年轻人称之为“蚁族”。
他提到,蚂蚁有25万个脑细胞,是所有的昆虫中最聪明的物种之一。它们又很弱小,一阵风就能将其从任何高处吹落到尘土中。但它们却以勤勤恳恳、全力以赴的工作态度,群居而生。
“这些特点,都是低收入聚居的大学毕业生群体的真实写照。”
即便是住在条件简陋的小窝里,这些年轻人也没有停止过憧憬未来。
但市场乱象如同水藻,也在需求旺盛时泛起,黑中介成为令年轻打工人痛恨的顽疾。
链家创始人左晖曾在一个采访中说:“1992年我大学毕业,2004年买了第一套房子。中间这12年,我一直在租房,换了10个房子,也曾经被骗得一塌糊涂。”
58同城创始人姚劲波1999年毕业开始北漂时,也被房产中介骗过钱,“信息不对称”甚至让他交出所有积蓄。
或许正是这种经历,让他们看到了一个新的市场缺口,58同城和链家,都很快开始涉足租房市场。
盯上这块蛋糕的不止他们。2010年后,随着移动互联网兴起,长租市场开始酝酿,并在2014年后火热。
这一阶段,几乎所有80后流动人口都进入了社会,至少1/3的90后开始进城工作,两者加起来的总数有2.8亿左右。
这相当于中国每6个人中,就有1个要寻找工作和安居的地方。
大规模需求刺激下,从2012到2019年的短短7年间,长租公寓行业公开融资超过100次,融资总额约2160亿元。
资本在狂欢,蜗居的年轻人却高兴不起来。无序扩张的长租市场,让他们陷入了新的麻烦。
2018年9月,关于长租公寓甲醛超标导致白血病的传闻和案例,以及长租公寓可能是“致命住所”的说法,一时间在互联网上疯传。
此后,虽有医学专家出面解读释疑,但事件的发酵,让更多的人站出来爆料在长租公寓租住时,都出现过皮肤过敏等不适,长租公寓装修间隔和甲醛问题,引发打工人的集体声讨。
“致命住所”的问题,刚刚有所缓解。整个长租行业,却又面临“致命崩盘”。
2018年,“鼎家公寓”爆雷,成为第一张倒下的“多米诺骨牌”。
两年间,陆续超过170家长租公寓爆雷。2020年登陆纽交所的第一支中概股“蛋壳公寓”,从上市高光到泡沫破灭,只用了10个月时间。
在微博“蛋壳套牢的年轻人如何自救”话题下,有人悲叹“晚上10点,顶着零下17度寒风走路半小时,不舍得打车回家省下的血汗钱,就这样没了!”
有人心有余悸地讲述:“房主喜欢半夜带人上门威胁赶人,已经三次了,不接受任何协商。现在加班结束没感到轻松,竟然是因为害怕回家……”。还有人崩溃地讲起自己的心酸:“一直没敢跟父母说这件事,如果他们知道自己的孩子租的房子被清退,还要继续还贷,会很难过吧。”
彼时,蛋壳管理的房间超过40万,意味着有如此经历的年轻人也会超过这一数字。
在电视剧《蜗居》里,郭海萍的妹妹质问道:“为什么我们的人生和梦想,都要拴在一个房子上呢?我们所有的努力,所有的期盼都仅仅是一处房子,这样的人生是不是太悲哀了?”
这一问,包含了多少“蚁族”的辛酸苦楚。13年后,仍然久久回荡。
曾入选2016年十大流行语的“葛优躺”,6年后依然以表情包的形式疯传。
在一所三室两厅的房子的沙发上,无所事事地斜躺着,竟是年轻人最可望而不可及的梦想。
但二十多年以来,国家其实一直致力于在非市场化租赁方面,解决国民安居问题。
1998年,国务院首次提出廉租房的概念,保障对象为城镇最低收入家庭,后拓宽至城市低收入住房困难家庭。
2010年国内开始公租房建设,2020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要高度重视保障性租赁住房建设”,保障性租赁住房正式登上历史舞台。
这些相关政策,取得了不少实效。
截至2018年底,3700多万困难群众住进了公租房,累计近2200万困难群众领取了公租房租赁补贴;棚户区改造,让上亿棚户区居民“出棚进楼”。
相较于1978年,2021年城乡居民人均住房建筑面积增长5.6倍,达到37.8平米。
但另一面,依然是沉甸甸的事实。
人社部数据显示,2021年全国农民工总量为2.92亿人。2022年,高校毕业生规模突破千万大关。
相应的,2021年全国40个城市新筹集的保障性租房只有94.2万套,2020年长租市场房间保有量也仅1100万间。
面对高企的房价,连王石、潘石屹等房地产大佬,都站出来劝年轻人租房。但年年上涨的房租,却让房客们叫苦不迭。
1955年,一篇中央书记处的调查报告指出:“各个城市的房租一般占职工家庭收入的8%至10%左右,与目前工资水平比较,有些城市应予调低。”
也就是说,当时对于交房租的一般理解,应在家庭收入的5%左右。
但到2020年左右,根据北京市职工平均工资标准和房租价格,其租金比例实际上达到了40%。
这背后,与长租市场供需失衡、渗透率不够有关。
总人口3.3亿人的美国,拥有4700万套长租公寓,租房人口比例为37%;欧洲国家租房比例,更是达到50%以上。它们的租赁房源机构渗透率,是中国的5-10倍。
针对乱涨价、黑中介、暴力催租及日常服务乱象,较为完善的租赁法规和市场机制约束,同样不可或缺。
关于北漂,有一个浪漫的解释:水下的鱼类,通过鱼鳔调节身体比重上升或者下降。唯一没有鱼鳔的鲨鱼,为了不让自己沉入海底,每时每刻都在游动。
北漂一族,就像在深不可测的都市里游荡的鲨鱼。为了生存,他们必须用尽全身力气“漂流”。
但现实是,打工人所依赖的工作和住所,都不具有稳定性。自己就像无根浮萍,跟着社会浪潮飘来荡去。
为此,住建部于2015年首次提出“租购并举”,推动租购同权。
十九大报告指出:“加快建立多主体供给、多渠道保障、租购并举的住房制度,让全体人民住有所居。”
2022年《政府工作报告》,再次明确了“探索新的发展模式,坚持租购并举”的指导要求。
地方也积极跟进。20多个省份出台相关细则,北京、深圳、成都、武汉等50多个城市出台住房租赁的扶持政策,相关房企相继推出商品租赁房规划。
2017年7月24日,位于上海浦东新区的全国首块R4全自持租赁住房用地,由张江集团底价摘得,并由专业机构“旭辉瓴寓”负责运营。在北京,类似项目有西红门高立庄地块,由当地国企与“万科泊寓”合作开发运营。
以自如为代表的长租行业,也进一步在运营模式上迭代升级,通过对产品和服务的精细化运营,让租房更安居。
社会各界正为租房安居作出更多努力,越来越多人正以租房实现着安居之梦。合力之下,“以租为家”,已经并且还将成为更多人安居乐业的新选择。

微信扫一扫|长按识别,进入读者交流群
|
|
|
|
|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