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龙:没有公平的“最优效率”是根本不存在的

“效率”与“公平”的“悖论”?根本不存在!
二战后,世界进入了一个新时代,显著特征之一就是在“自由、民主”的大旗下,西方对世界其余民族的无形殖民。为配合新一代无形战(“冷战”)的战略需求,“西方经济学”也随之开始了悄无声息的化身,不仅化身成一盏航标灯,指引着诸国政府为了取得政治上的既定社会目标应该制订什么样的经济政策,甚至开始扮演一个至高无上的角色:规范一个社会的价值观及发展目标。
在“中立客观”的“经济科学”规范下,“效率”被捧上神坛,成为高高在上、骑在公平与道德的头上被顶礼膜拜的图腾。而经济学家们则要为之配置一套相应的合理合法的“科学依据”,其中一个就是有关“公平与效率”的“悖论”。然而,被经济学家们纷纷扬扬长期渲染的这个所谓“悖论”根本不存在。
效率与公平其实并不相互排斥或有什么根本冲突。二十一世纪的今天,分⼦生物学与⼈类对基因密码的破译在逐渐向人类揭示大自然的根本运行机制与自然规律,向我们证实华夏文明之源《易》传输的宇宙运行法则才是生命和人类社会得以存续和升华的奥秘所在:最优机制在于协同合作,而不是你死我活的“生存竞争”。基因、细胞及其构建的各种组织器官都高度复杂精细,只有协同合作、各尽所能,一个生命体才能达到最优状态。否则整个宇宙早已被摧毁而不复存在。
换句话说,放眼整体观,最大的效率只能来自最大的公平与相互协作。作为宇宙与自然的一部分,人类社会不可能违背这个自然与生命的根本运行机制。亡命徒夺宝式的生死搏斗竞争论,是只看点不看面,是对这一自然规律的根本性曲解,最终只能因其背离自然规律而损人不利己,甚至造成自灭也毁人的后果。我们会看到,诞生于十九世纪的达尔文“进化论”携带着浓厚的殖民主义与种族主义背景,根本不是“科学观察和实验”的结果,与生命的根本运行法则完全背道而驰。
以有悖自然运行的根本法则、反人类社会的“科学理论”为借口,把“效率”高高凌驾于“公平”之上,这本身就是阻碍人类社会健康发展的一个癌变。依靠话语权的垄断,经济模式的这些特质也由媒体、教育、社会舆论导向操纵者们引入社会公众的思维意识中,在人们毫无觉察中,禁锢着人类面临困境寻求更开阔视野的努力。

生活在一维世界的“功利主义”
十九纪欧洲对外殖民扩张、对世界诸民族的强取豪夺进入高潮期的同时,在欧洲内部产生了一个奇异的共生体,传播一种让许多人毫无质疑并无条件接受的理念,即自由市场体制本身具有真正的道德要素。如此,“自由市场”逐渐地被视为一个有效而正确的社会意识形态,一种有效的经济方法,并被“科学”地证明。
在此期间,方法论越来越被多地嵌入经济学,其中一个就是“功利主义”(Utilitarianism)。当“功利主义”崛起时,它被推销成“科学的”经济学与伦理道德的完美结合。这不过是西方经济学的又一个梦幻泡影。
“功利主义”提倡追求“最大幸福”。其代表性哲学家包括约翰·斯图亚特·密尔、杰瑞米·边沁等人。在亚当·斯密的《国富论》诞生十三年之后,杰里米·边沁也发表了其影响巨大的《道德与立法原理导论》(An Introduction to the Principles of Morals and Legislations)。在该书中,边沁阐明了“功利主义”最被熟知的原则,并把它应用于法学、政治学、经济学、伦理学,以此作为判断一切行为和立法措施的准则。
边沁认为,社会是由个人构成的整体,其中每个人是组成社会的一分子。社会整体的幸福是组成社会的个人幸福总和,最佳行为则是可以带来最大人数的最大幸福的行为。不同于一般的伦理学说,“功利主义”并不考虑一个人行为的动机与手段,而仅考虑这个行为的结果对最大幸福值的影响。一种行为若有助于增进幸福,就是正确的,反之就是错误的。
“功利主义”的吸引力在于,至少从表面看,它似乎提供了一种道德判断的普适标准。
尽管边沁本人不久即修正了自己的理论,加入了一个条件:如果可以增加更多人的更大幸福,那么无论社会的少数人经受多么大的困苦,也必须容忍。按照“功利主义”的设想,人类社会道德上的冲突与选择可以简单地得以解决:只需计算不同的选择对幸福总量的影响大小多少。
“功利主义”的这个理论实在是个奇想,它基于一个既不现实、也明显误导人的虚幻根基上。要让这个假想成立,就需要一系列概念与要素,并以数学公式在人与人之间、并以超越时空的神奇方式加以对比,而要进行这种对比,幸福的数量、福利的数量等数值也要相当、并被指定一个独特的单位值。若果真如此,那么所有种类的快乐、所有人感知的幸福、愿望的满足、所有购买的产品及服务、大千世界万物的状态等等,都可被简化、降低到一种一维直线的标准,除了数量上的考虑,不允许任何其它变化。显而易见,这是个根本不可能成立的荒谬命题。
在本质上,“功利主义”与西方经济学的其它理论没有什么区别,嘴上声称自己尊重并捍卫个人的选择自由,实际做的却是把人降格到动物不如的一维物化物,完全忽略不计人类社会错综复杂的真实世界:一人一样的目标、愿望、感受、理想、幸福感,等等。这一切多基于每个人内在的主观考量及个人生命的独特历程,根本不可计量。“功利主义”是把一个虚构的伪命题作为现实去构建一个一维化的空中阁楼,设想人的各式价值观与七情六欲统统可以降维到一种简单的货币价值指数。
不仅如此,“功利主义”在经济增长与福利的进步这二者之间简单地划上等号,这更是一个明显的谬误。虽然在确保所有不同种类的需求都被供应满足这方面,自由市场常常的确是有效率的,但它本身并不会有什么效率去赋予所有市场参与者市场平等准入的机会以表达他们的偏好与愿望,它通常也不可能对初始收入与财富的不平等加以修正。它只能满足部分有限的偏好,并顶多只能满足那些有足够财富与势力在市场上显示出的偏好。
许多人类的愿望是向往那些不可交易的商品或服务,那些在市场上不被表述的愿望也会在一个自由市场体制中被忽视。即使那些可在市场上得以表述、并通过买卖得以满足的愿望,也可能是对社会福利或健康发展完全没有益处的,如赌博、嫖娼、吸毒贩毒等等。不仅如此,市场上某种欲望的价值比重更与购买者的财富及其愿望强烈的程度有关——从这个角度上看,“经济增长”主要是对某些特殊群体的愿望满足的计量——这部分人富足到足够程度、以至于可以随心所欲地购买自己所愿的任何产品与服务。
在一个被“科学计量”和金钱驱使的时代与社会,那些不能以金钱价值衡量的愿望被日益忽视并被抛弃在“科学计量”的方程式之外。唯一被认可的最终价值是市场价。人的生命与一切神圣的存在都被降格成可买卖的商品,自由市场经济学如此成为成功瓦解社会伦理道德、摧毁人的尊严与生命价值的工具。
尽管如此,“功利主义”依然被嵌入“自由市场经济”的一整套理论中,并让这些理论变得更受人尊重,使得经济学家们可对自由市场经济的道德困境冠冕堂皇地忽略不计,并强化了一个幻觉:自由市场体制会自动带来道德与福利上的进步。
“功利主义”的谬误显而易见,但“市场最懂怎么做最好”、“经济增长=国民福利进步”之类的伪命题仍主导着许多人的思维意识,导致他们对“人类社会进步”这一概念发生悲剧性迷失,产生了一个幻觉:如果愿望的满足可以作为福利的衡量尺度,那么经济增长自然会代表福利进步的计量。
“功利主义”这些基于幻觉基础上的逻辑也致使以数值表达的“经济增长”在许多国家被捧上神坛,作为至高无上的政治与道德目标,不计一切代价地片面追求。
在一个精英权贵高高凌驾于普通民众之上、贫富分化越来越严重的时代,即使“功利主义”表面上那些对社会公平与道德的考量及追求也被大大注水。自二十世纪三十年代,针对其计量的不可行性,生活在一维世界的“功利主义”遭到严厉抨击,其社会再分配伦理也被大大冲淡。经济学家们必须找到一个更光鲜的替代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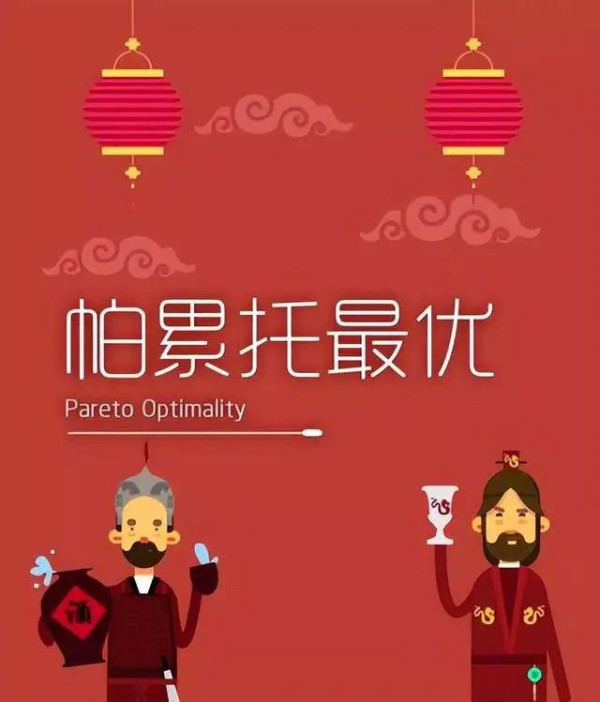
亿万富翁坐视乞丐饿死:“帕累托最优”提供“科学证明”!
根据“功利主义”,既然商品对每个人的边际效用递减,既然所有人都有同样的能力从收入或商品中获利,一个自然逻辑就是,若要最大程度地扩大总效益,就需要向收入与财富的均衡分配点移动。但这是权贵们不可接受的。于是为了将这个收入与财富再分配的伦理从其“中立而客观的科学”中剔除,一个更具有“数学”及“客观科学”味道的衡量标准被使用,这就是“帕累托效率”(又译:“帕累托最优”,Pareto efficiency)。
“帕累托效率”以意大利经济学家维弗雷多·帕累托的名字命名,他在关于经济效率和收入分配的研究中最早使用了这个概念。概括地说,“帕累托效率”是指资源分配的一种理想状态,假定固有的一群人与可分配的资源在进行再分配时,在没有任何人境况变坏的前提下,至少其中一个人的境况变得更好。这种状态被视为公平与效率的“理想王国”。
但“帕累托效率”的前提条件同样是不切实际的,与诸多其它种种经济学理论一样,“帕雷托效率”也基于一系列完全不现实的虚无假设条件基础上,如假设消费者偏好恒定不变、不存在未来的不确定性、不存在外部效应、不存在垄断......等等,这些都属于幻觉,永远也不可能存在于人类的现实社会中。
即使不考虑这个理论是否实际,“帕雷托效率”不容许任何人的利益受到任何损害,也不要求对不同个人之间的利益及偏好满意度进行对比。假设有一个亿万富翁和一个饥寒交迫、濒临饿死的乞丐,若让该亿万富翁拿出自己財富的百万分之一,就可使乞丐免于死亡。但从“帕雷托效率”的角度讲,如果乞丐没有什么可回报富翁的,那么这种财富再分配就不是最优状态,因为这样损害了该亿万富翁的福利。依照此逻辑,让亿万富翁熟视无睹地继续其亿万财富的奢华生活、坐视乞丐饿死,才算是“帕累托效率”效率下的最优状态。
“帕累托效率”的这个“最优状态”对那些走上“科学”神坛的经济学家们产生了无限的吸引力——这些经济学家们难以忍受自己的“科学”背上道德及社会公平收入再分配这个沉重负担。然而自古及今,社会公平收入再分配本来就是经济学及任何一个社会的政府必须履行的天职,这是它们合理合法存在的基石。
为了把重要性牢牢附在“帕雷托效率”的“科学”理念上、把视线从更广义的“功利主义”幸福最大化这个目标引开,西方经济学也有了一个新任务:在“效率”(被捧上圣坛)以及“公平分配”和利益最大化(不被考量)之间,划一道鲜明的界限。不仅如此,“帕雷托效率”被设立在一个既定的局限框架内:不允许更改任何人最初的才能禀赋与收入。
“帕雷托效率”如此轻松绕过那个让“科学”的经济学家们尴尬而宁愿闭眼躲开的问题,即究竟能否通过对这些初始禀赋的再分配而进一步促进公共利益;不仅如此,“帕雷托效率”也无需去证明一个不可能被证明的伪命题,即市场“看不见的手”会通过“绢滴效应”等神工鬼斧而达到利益的重大均衡分配。
把自己的脑袋置于云霄之外的自由市场推销者们根本不屑去考虑地球上的琐事与现实:在贫富严重分化的当今世界,横跨全球的初始收入、禀赋都极度不平等,在这个条件下,试图通过最小干预的方式去实现效率的最大化,即使是边际效用递减律生效,也难以避免剥夺最大效益的机会。
面对人类社会现实,“功利主义”哲学及经济理论并没有提供一个有效可行的方法去比较不同人的利益,以显示任何再分配能否实际上增加总效用或福利;也没有解答如果如此,究竟是多少的问题;更无法找到任何手段有效地量化公平与效率的取舍交换。而这一切,至少部分地导致一种社会病毒在全球扩散:在“客观中立的科学”这层光环掩护下,“效率”成了高高凌驾于最大福利与公平之上的太上皇。
经济学这种不可饶恕的失败是经济学家难以面对的,当“自由市场”推销者们侃侃宣讲“市场是人们偏好的真正裁决者”、“市场最懂”之类的信仰时,这个巨大的失败也是他们便利忘记、缄默不提的,取而代之的是将市场“效率的最大化”赋予了近乎道德目标的神坛地位,并以此为理由,甚至不允许最富的人为了更多人的更大福利有哪怕一丝一毫的利益减少。这是地地道道的服务于权贵群体的经济学,是经济学的严重渎职。

“市场最懂怎么做最好”?谁在忽悠你?!
“市场最懂怎么做最好”吗?推销这个经济学迷信的传教士们既忽略了市场适用范围的严重局限,也对市场失败的现实视而不见。在市场上,每个人要权衡市场交易为自己带来的边际效益与边际成本,并寻求自己净收益的最大化。然而当存在环境等外部成本时,社会总成本并不会在相关市场参与者的私人成本/收益中反映出来,因而个人对私利的“理性追求”并不可能最大化地带来社会公共利益。这与西方经济学推销或想象的完全相反。
就拿“环境资源”这个今天已成时髦的话题来说:清洁的空气或河流、湖泊、海洋等公共财产。这些公共财产本来属于全体国民,由政府代替其管理。对之进行任何形式的私有化,把本属于全体人民的所有财产非法分配给有钱有势去购买这些资源的少数人,是变相的偷盗与洗劫。
不仅如此,从经济管理角度讲,要设立一个市场机制去协调所有人的行为以防止资源枯竭或确定捕鱼的最佳总捕鱼量,是不可能的。因为无人拥有海洋中的鱼或清洁的空气,市场价格只能反映对鱼的需求以及捕鱼的成本,而这两大重要因素也并不一定要与供给的持续性相连。如果一个人很大公无私,并有足够的良知把所有因素纳入自己的成本计算中,他很可能被挤出市场。因而若要避免过度捕捞而导致鱼类资源枯竭之类的危险,只能诉诸一个比市场更有效的途径:政府或某种干预。如由政府出面设立一个最大限度捕捞的配额或可强制性的集体行动、垄断性拥有者等外部干预。
再比如清洁空气。如何对清洁的空气进行市场化、私有化?你能把清洁空气打包并一包一包出租吗?显而易见,同样不可能让“自由市场”去决定以什么价格购买污染空气的权利,或以什么价格出卖给那些“使用者”(那些天天呼吸空气的人)以维持其清洁。
如今,美西方向世界推销的时髦新兴概念“碳排放交易”等概念,与其说是经济学的一个解决方案,不如说是从美西方刮来的又一股镜花水月歪风,不仅无视现实,而且涉嫌旨在一箭双雕误导中国等目标国家。
有人被欧美抛出的“碳排放交易市场”机制忽悠,相信这个机制是让污染公司为污染付出代价,最终将会终结污染。这个信条完全缺乏事实支撑。相反,环境组织CE Delft 等机构的研究显示,污染公司购买碳信用额等成本完全可以简单地转嫁给客户,甚至可借机从那些“亲大企业”的政府手里获得特别惠顾,转而成为发污染业横财的专业户。如根据欧盟碳排放交易计划,具有货币价值的碳排放许可证被免费提供给钢铁和炼油行业。这些行业尽管没有支付许可证费用,却将假定的成本转嫁给了消费者。研究表明这在2005年至2008年间为那些污染企业带来了140亿欧元的横财,也意味着“大量资金从消费者口袋里转移到了能源密集型行业”,造成的一个荒唐结果就是:污染有功,污染发财。
实际上,所谓的“碳排放交易市场”并非一个新机制,它不过是在复制九十年代美国一项早已被证明失败的政策。作为1990年美国清洁法案修正案的一部分,美国政府设立了一个旨在降低二氧化硫 (SO2) 污染排放量的交易市场。这就是后来崛起的“碳排放市场”模式的先驱。事实证明,采取这个机制的美国公司继续造成污染,减排效果远比中国、欧盟和日本治理模式低效。其他这些国家采取的减排措施更成功,大体上都是政府通过法规等途径,直接监管工厂减少二氧化硫排放。
1997年在京都谈判达成的第一份联合国气候协议中,大多数国家对纳入碳排放交易持怀疑态度,然而美国代表团坚持要建立碳排放交易市场,甚至威胁称,如果不接受这个计划就退出谈判。其他国家在美国的压力下屈服了。
尽管有失败的历史先例并缺乏任何可信的证据证明“碳排放交易市场”有助于应对气候变化,更无任何证据表明市场是解决环境污染的有效途径,但为什么失败的美国模式反倒成了全球气候政策的一个重要范本?!这种荒唐的国际运行规则在1997年的气候大会时如此,近三十年后2024年的今天并没有实质上的改变。
这就是我们生活的现实世界!这就是为什么中国必须从精神上、心理上、可供选择的应对手段上都强大到足以有勇气和力量直视黑暗森林的魔王之眼,彻底砸碎这个荒唐世界的荒唐规则!如此才能把自己乃至整个人类解救出来,共同奔向自由和解放。
更意味深长的是,2001年,在美国主导起草的碳排放交易市场框架已稳稳当当地嵌入《京都议定书》后,美国却宣布自己不再受其制约——退出《京都议定书》。这个时间点很有意味。
在《地球物理战:信息黑幕下呼风唤雨术如此一路走来》、《“环保运动”崛起与“气候变化”:教科书不会讲述我们如何被忽悠》等主题上,我们已详细审视了数十年以来围绕着“气候变化”的舆论宣传战与“环保运动”崛起的新一代军事大革命的背景,这里不再多驻足,只借眼下话题略重温几个时间点上的“巧合”:
1.七十年代,冷战两大“天敌”美国和苏联罕见携手,开始推动“全球环保减排合作”,环保运动从此开始大张旗鼓地向世界尤其是发展中国家推动。背后推动这场如今已声嘶力竭的“气候暖化”、“环境保护”运动崛起的主要力量并非环境组织,而是军方,更非两大国真心关注人类未来与世界环境,这一切的发生有一个被三缄其口的背景:
二战后,为确保在军事理念及新型武器研发领域对其他国家维持绝对的代差优势,“冷战”两大对手一方面锣鼓喧地渲染“核武”,另一方面在心照不宣间对新一代军事大革命杀手锏进行各种秘密研发与投放试验,除了生物基因武器外,另一个杀手锏被紧锣密鼓秘密研发的,就是苏联抢先、美国急追的地球物理武器。恰值七十年代,苏联在该领域的成功实战试验震惊美国军方,苏联的暂时领先优势迫使美国急切以各种借口寻求“合作”。如此才出现了国际舞台上二者携手上演的“双簧戏”。
2.自九十年代,尤其是2003年后,横跨全球、尤其是发展中国家遭遇的各种自然灾害剧增,在时间段上恰好与美国的地球物理武器研究设施“竖琴”安装及完备吻合。与此同时,由英美担当主角幕后组织协调的的“全球气候变化”运动也铺天盖地肆虐整个世界。人类如此进入了一个前所未有的“人工制造自然灾难”+声东击西信息垄断黑幕的一体化博弈时代。
3.如今其军事使命已完成多年、早已转入民间机构之手的“竖琴”第一阶段是在克林顿总统的大力推动下于1994年安装完毕。这一阶段虽然仅有18个发射器被实际连通,但其功能已可达到实战制造地震、极端气候的有效程度了。《京都协定》恰是克林顿政府在那之后开始大张旗鼓渲染“全球气候变化”并推动各国签订的;
4.“竖琴”的发展大多是在小布什总统执政期间完成,美国政府宣布退出《京都协定》恰是在小布什入主白宫后不久;
5.小布什政府为其后的奥巴马政府大力推进以“全球气候变化”等屏蔽话术为核心的外交政策“转向”、全球军事打击战略铺设了道路。自奥巴马时代至今,包括中国在内的一系列目标国家开始经历不成比例频繁的各种异常气候等自然灾难。这个“自然”现象与欧美及其主导的国际组织声嘶力竭开展的“气候变化”喧闹战的同步协调绝非时间上的偶然巧合。
美国这数十年间持续不断步步推进的进程是两大政党的共同“使命”,虽然在国内选举等舞台上各方政客与娱乐明星们一同频频为美国及世界公众大打出手上演政党对峙游戏,在这些戏剧幕后,是美国全球征服战略不变的恒定蓝图。明白了这一点,就不会被两党政治游戏迷惑,更大可不必浪费时间和精力为此彻夜不眠、关注这场游戏双方的输赢。我们要做的就是对手害怕的:放弃任何幻想,抛弃任何诱导,一心一意准备应对绝杀各方来犯豺狼的有效手段!
回归普通常识原点
长期以来,西方强权、它们主导的“国际机构”、它们主宰的教育与信息流通话语权,依赖与现实相悖的虚幻理论甚至虚假信息,黑白颠倒地诱导着世界公众,这种现象令人触目惊心,说它如同黑暗的中世纪时教会对欧洲的窒息性思想垄断,一点不为过。在其《危险的潮流(经济学现状)《Dangerous Currents (State of Economics)》 (1983)中,经济学家莱斯特·瑟罗曾评论主导世界经济学研究的西方经济学理论及其经济模式“就如同相信地球是平的、或太阳绕着地球转——在这两个例子中,你尽可去严格地论证,但真凭实据却几乎不可能有。”
对政府在一系列必要领域的投资带来的多重效益决意视而不见,致使一些人如同被洗脑而相信地球是平的、太阳绕着地球转一样,偏执地反对任何必要的政府干预经济、一味强调“自由市场的美德”。他们拒绝面对一个普通常识般的事实:政府对基础设施的投资通常会提高一系列经济领域的效率,对人力资本的投资也同样如此,如通过政府对教育、医疗的投资也会帮助企业更快、更有效地采用新技术、扶植创新、提高产品质量等等。由于其相对的边际市场收益,这一切基础设施、人力资本的投资并不宜被私有资本提供。
在“市场化”、“自由化”、“私有化”沿着一条不归路疯狂裸奔中,许多人也忘记了一个基本常识:对公共财产的健康维护不仅是一个政府不可推卸的天职,也是在这些领域达到最优效率的最佳途径——只有政府才处于最佳位置,防止“搭便车”、环境污染等问题。这也正是为什么亚当·斯密本人相信公共工程等项目必须要由政府承担,政府则可使用各种手段与途径,将外部成本内在化,也只有通过政府必要的干预,才可使市场发挥效率,有效地将之分配给最有用的生产者。
至于教育、医疗、养老、面向全社会的失业培训与成年人再教育等公共服务领域,在这些领域承担开支,不仅是任何一个政府都理应承担的不可推卸的神圣天职,也是在整个国家层面长期并全面提升社会健康运行效率的最优途径,是一条通向经济健康发展、社会公正与和谐的进步之路。对这个天职的放弃,与西方列强设计、诱导的“自由市场”、“私有化”之路“接轨”,最终只能导致国民被迫为教育、医疗及养老承担沉重的支出,许多孩子被迫停学,许多家庭因无钱就医而家破人亡,适龄人口不想生也养不起的现象会日趋严重。这种“新自由主义”的经济政策是对国家发展、民族存续的无形阻断,不仅是政策导向失误的技术性问题,它更是政府的渎职性犯罪。
它牺牲的不仅是社会的公平正义,最终摧毁的必然也是国家健康运行的最优效率。

微信扫一扫|长按识别,进入读者交流群
|
|
|
|
|
|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