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宗教市场理论”在中国来龙去脉的背后
“宗教市场理论”在中国来龙去脉的背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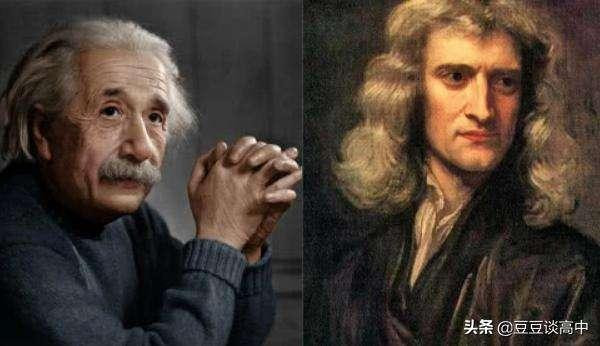
内容提要:本文依据杨凤岗于2020年10月7日在“普世社会科学研究网”发表的《宗教市场理论在中国的来龙去脉》和他的相关言行,回顾和评论了“宗教市场论”及“中国宗教三色市场论”在中国学术界的一些反响,再度揭示杨凤岗及其后台的现实政治诉求,批驳了他对中国无神论者群体的攻击。
2020年10月7日,美国普度大学教授杨凤岗在北京一家“普世社会科学研究所”的“普世社会科学研究”网站上发表了一篇《宗教市场理论在中国的来龙去脉》(以下称《来龙去脉》)的长文,对于他将美国宗教社会学家斯达克、芬克提出“宗教市场理论”的《信仰的法则》一书译介到中国,并据以发展出所谓“中国宗教三色市场理论”15年来在中国的遭际进行了一番回顾和议论。文中对“宗教市场理论”和“中国宗教三色市场理论”得到的反响做了一些区分。他说:“宗教市场理论在中国的学者和官员中很快引发兴趣。学界对于这种理论的认可和赞赏显现在会议、出版物和研究生论文当中。”“官员和官方学者对于三色市场理论所表现出的……反应”是“爱恨交加”,“有一类学者对于宗教市场理论作出了另类批判——厌恶和拒斥,其原因在于他们的学科背景,或者意识形态背景,或者二者兼而有之。” 他点名批评了对“宗教市场论”和“三色市场论”表示异议的一批学者,接着把攻击的重点转到对该理论“发起了政治性挞伐”的“战斗的无神论者”和《科学与无神论》杂志身上,指责“在……新时代,战斗的无神论趁机搏取上位,主导了宗教政策日程的设定,通过了更加严厉的宗教事务条例,并且对于宗教学术研究和出版加强了审查和封杀。”因此造成了“宗教市场理论的低潮和骤降”。
杨凤岗教授如此“厚非”“战斗的无神论者”和《科学与无神论》杂志,而且矛头直指“新时代”的宗教政策和宗教治理,笔者作为同样撰文批评过“宗教市场论”或“中国宗教三色市场论”的无神论者之一,很想也沿着这个话题做一点回顾和议论。
杨凤岗(1964- ),河北省沧州市沧县人。其学术经历为:河北师范大学政治教育系法学士(1982),南开大学哲学硕士(1987,硕士论文探讨西方哲学中上帝观念的演变),中国人民大学哲学系讲师(1988-1989,1989年1月公派去美国做访问学者,滞留不归,1992年前后接受基督教洗礼);美国天主教大学社会学博士(1997,博士论文研究北美华人基督徒群体),美国休斯顿大学移民宗教研究博士后(1997-1999),美国南缅因州大学社会学系助教(1999-2002),美国印第安纳州普度大学社会学系副教授(2002-2007,主要讲授“宗教在美国”课程);2000年前后入籍美国,并开始在中国大陆从事系统的宗教社会学调查研究;中国人民大学宗教学讲座教授(2004- ,还多次应邀在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北京师范大学、山东大学、上海大学、四川大学、陕西师范大学等高校举行讲座),美国普度大学社会学系教授兼中国宗教与社会研究中心主任(2008- )。2003年10月在美国科学研究宗教学会年会上,口头发表题为“Religions in Communist China:Open,Black,and Gray Marketsina Shortage Economy(共产中国的宗教:公开的、黑色的和灰色的短缺经济市场)”的论文,后来改题为“The Red, Black, and Gray Markets of Religion in China(《中国宗教的红色、黑色和灰色市场》)”在美《社会学季刊》发表,获得美国宗教科学研究学会2006年度杰出论文奖。2004年在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出版译著《信仰的法则:解释宗教之人的方面》;随后在《中国人民大学学报》2006年第6期发表其获奖论文的改编本《中国宗教的三色市场》,在《中国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8年第4期发表该文原作的全文汉译本,仍以《中国宗教的三色市场》为名。同期,他从2004年起由美国邓普顿基金会(The John Templeton Foundation)资助在中国人民大学等高校组织安排各种宗教学研讨活动,大力推广《信仰的法则》一书的“宗教市场论”和自己的“中国宗教的三色市场”论,还在《中国民族报·宗教周刊》设立“此岸彼岸”专栏,在多个公共电视频道和门户网站发表以中国当代宗教特别是基督教发展态势为主题的演讲。除中国大陆外,他还应邀在香港、台湾、美国和欧洲的很多著名大学和智库发表演讲,接受过美欧澳很多主流媒体的采访。2012年当选美国科学研究宗教学会1949年成立以来第一位非白人会长。
用“宗教市场论”观察中国宗教现状而写成的《中国宗教的三色市场》,被杨凤岗教授视为“用经济学术语对中国的宗教进行理论建构”的成功之作。然而,它实际是从一个特定角度汇总了海外某种势力对当代中国政府宗教工作的评判。作者由此取得了在美国学术界的地位和来自“上层社会”的财力支持。
在《中国宗教的三色市场》一文中,杨凤岗将中国宗教分为“红市”“黑市”和“灰市”。“红市”指“官方批准的宗教”,但“受到诸多约束和限制”。“黑市”指在地下活动的非法宗教组织,如天主教“地下教会”、基督教“家庭教会”,以及“许许多多的所谓私人佛庙或私人家庭佛堂”;作者认为,“宗教黑市最早是由20世纪50年代(当时政府极力创建国家的‘爱国’宗教团体)的国家反宗教政策所催生的。”同时,作者把“在民族分裂者中,有藏传佛教徒( Tibetan Buddhists)和维吾尔穆斯林(Uyghur Muslims),权力部门已多次对其进行了严厉取缔”,也纳入了“宗教黑市”之列。“灰市”则分为两大类:“合法宗教组织和个体的非法宗教活动,政府机关或官员所支持的合法性/非法性边界模棱两可的宗教组织和活动;内隐的宗教性现象包括以文化和健康科学为表现形式的宗教。”作者称:“当外显的宗教性组织和活动遭到限制和约束时,许多人会寻求更加内隐的宗教形式。”“大多数的气功组织和活动是内隐宗教的一种表现形式。”“法轮功是较晚出现的规模最大的气功组织之一。”他断言:“当宗教需求不能在开放市场中满足且黑市中的潜在代价过高时,许多人就会在灰市中寻求选择。”
对于“宗教市场论”在本世纪初的中国学术界引起一部分人的兴趣这一现象,旅法社会学学者汲喆曾提出过自己的认识:“宗教经济模式所蕴含的美国新古典经济学的自由主义意识形态呼应了中国政治+学术界的主流话语,这使得有关‘宗教市场’的研究具备了‘政治正确’的正当性。与此同时,这一模式所暗示的减少国家调控、促进宗教多元竞争的诉求也使中国学者可以委婉地表达出他们对宗教自由的认同和对宗教管制的批评。”(汲喆:《如何超越经典世俗化理论——评宗教社会学的三种后世俗化论述》,《社会学研究》2008年第4期)这个看法应该说是很尖锐的,反映了接受“宗教市场论”背后实际存在的政治-意识形态方面的问题。事实上,即使“宗教市场理论”是作为学术研究成果出现的,但杨凤岗煞费苦心地将其引进中国,并且专门就中国宗教事务管理领域“开发”出“三色市场”理论,与其说同样引起国内不少人的兴趣,不如说也显示了杨教授自己从特定政治-意识形态立场关注中国宗教的兴趣。
中国学术界并不是所有人都听不出杨凤岗借兜售其“三色市场”理论所奏出的弦外之音。有很多学者以学术讨论的方式表示过对于将“宗教市场论”引入中国的疑虑以至反感,包括有人指出要警惕其在中国演变成一个“社会批判话语”的理论。关于这样的反应,只需要引用一下《来龙去脉》中他自己的述说就能证明。在该文中,杨凤岗指名道姓对“复旦大学宗教学学者范丽珠”“北京大学宗教社会学学者卢云峰”“人类学学者梁永佳”等批判性地评论过“宗教市场论”及其“三色市场论”的中国学者进行了语带讥讽的反诘,说范丽珠“宣称‘宗教经济学范式’是错误的,更进而断言,把这种理论应用在对中国宗教的研究则是‘危险的’,但是对于危险何在却语焉不详”;卢云峰“可能是在中文世界第一个批评宗教市场理论以基督教为核心特征的人”,“不幸的是,这一说法被其他人不加思考地借用,并且进而演化出阴谋论,在某些学者和官方理论家那里流行”;梁永佳“借助新左派对于全球资本主义的批判,宣称自由市场竞争只会有利于基督教宗派这种大型集团,因此他主张政府干预,却不顾这样一个事实,即这个政府在无神论意识形态主导下对中国传统文化已经进行了几十年的清洗”,云云。应该指出,令杨凤岗表示恼火的这样一些学界观点,其实很敏锐地触及了他在中国推销“宗教市场论”特别是其“三色市场论”的目的,只是还没有直接说穿而已。杨凤岗的反诘,不过是欲盖弥彰。
不止以上学者,有的从事实际工作的人士也针对杨凤岗的理论发表过批评意见。一位“基层宗教工作者”2010年2月25日17:41:06发给《中国民族报》一个帖子,其中说到:“近段时间,我从网上认识了杨凤岗,并查看了他的许多在贵报上发表的文章,如《杨凤岗:中国总体来说是个信仰缺失的社会》(言下之意是大力鼓噪宗教信仰)、《中国青年宗教态度百年大回转》(为中国宗教复兴呐喊)、《美国青少年的宗教态度》(说明美国青年并未像别人说的那样对基督教正在失去兴趣)等等,从字里行间,似乎有借贵报传播基督教,引发中国基督教界思想混乱等疑虑。”“杨凤岗的观点并不可靠,也不可信。如果我判断没有错的话,杨是个基督徒,从他的文章来看,杨对中国传统文化吃得并不透彻,对中国普通百姓的精神生活也相当陌生,他所作的研究,由于他本人的基督教信仰和西方文化的浸淫,他的文章中有强烈批判中国现行政策,盲目崇拜推广西方基督教文化的色彩,他所得出的结论并不可靠,相反要相当警惕。”(《中国民族报》还收到了其他人包括著名专家学者的同类意见,随后叫停了杨凤岗的专栏。)
这位基层宗教工作者判断得不错,杨凤岗确实是个“基督徒”,而且对基督教在中国的存在势态表现出异常的关注。他曾经预言中国将“超过美国,成为世界上信仰基督教人数最多的国家”;他还兴奋不已地宣称:“新的条例取缔了基督教家庭教会,即把他们从灰市打入黑市,但是,绝大部分家庭教会变换形式依然存在,有些还是非常活跃,甚至在新冠病毒大流行期间,在线聚会充满活力,推动在中国内外的福音传播事工。”(杨凤岗:《宗教市场理论在中国的来龙去脉》)在此之前,2015年5月4日,他在《FT金融时报》中文网刊文《中国基督徒增长辨析》,宣称:“无论如何,基督教在中国的迅速成长,不仅会影响中国,而且会影响世界。”同时意味深长地提示:“很多基督徒对此缺乏准备,只专注于教会生活和传播福音,而缺少对于社会公共事务的关心,缺少应有的社会责任感。”如果说,杨凤岗希望看到基督教在中国“迅速成长”,还可以视之为一个基督徒宗教感情的流露,但他指责他的中国教友“缺少对于社会公共事务的关心,缺少应有的社会责任感”,又是什么意思呢?换言之,他要求中国基督徒在教会生活和传播福音之外,还要以宗教身份关心什么样的“社会公共事务”?该如何关心?要具备什么样的“社会责任感”?该如何体现?这些问题,似乎是杨凤岗以基督徒的名义向中国的另一些基督徒提出来的,但他设计的答案却超出了基督教自身的范畴,仍然要从“中国宗教三色市场论”的底色中去追寻。联系以下这个案例,就可以得到证明:
2009年—2013年,美国邓普顿基金会拿出200万美元,资助杨凤岗的“普度大学中国宗教与社会研究中心”推出一个“中国人的灵性与社会项目”,包括 “培训”和“研究”两项任务。“培训”分为两部分:一是对“研究人员”的系统培训,二是对“大学教师”提供暑期培训班。暑期培训班每年大约有12-30位研究者参加,参与者无需自己掏钱。培训内容包括研究方法、资料收集、数据分析以及期刊论文的写作。还有一个宗教社会学教师的“暑期进修班”,要求学员连续三年参加,分别研讨宗教社会学初级、中级、高级课程的教学内容和教学方法,同样是免费的。“研究”也分为两类:一类是“研究中心课题”,面向中国大陆大学的研究中心或研究所,每项资助5万到10万美元。另一类是“个人课题”,每项资助1万到3万美元。
愿意对这个研究中国宗教与社会的项目慷慨出资的邓普顿基金会是一个什么样的机构呢?我们可以不细说创立基金会的约翰·邓普顿(1912—2008)是一位被称为“全球投资之父”的虔诚基督徒,也可以不细说该基金会被认为在成立之初就是一个亲宗教的组织,只需知道2012年它把其设立的全世界年度最高金额的“邓普顿奖”颁给了达赖,就可以基本上了解它对中国的政治态度了。这样的投资方,对杨凤岗教授的中国宗教研究项目青睐有加,是不是能用“一拍即合”来形容呢?
杨凤岗坦白地告诉大家,所列项目的资助是有条件的:第一,必须符合他所规定或认可的“宗教社会科学原则、理论和方法的中国宗教与灵性研究”。这原则、理论和方法是什么?“中国宗教”的范围是什么?“中国灵性”又是什么?里边都有文章,也都是他可以用来决定给钱不给钱的理由。第二,研究经费由普度大学每年分两期付款,付款的前提包括令人满意的课题研究进展和培训工作坊的认真参与等。什么是“令人满意”、如何才算“认真”?如果杨教授说“不满意”或判定参与者“不认真”,那就一切泡汤。第三点最为要害:“本项目不支持以哲学、神学或文本研究为主要内容的课题”——因为他所要做的只是“对中国大陆宗教或灵性的实证研究,或者包括大陆在内的比较性实证研究”。这个被一再强调的“实证”指的是现实情况:中国宗教的现状及其内部结构和外在的社会联系,亦即他规定的“研究主题:我们优先考虑以宗教为自变量的课题,即探讨宗教或灵性对于个人、团体、社群、组织及制度的影响”。譬如获得“中心课题”资助的“华东师范大学宗教与社会研究中心”的题目是“长江三角洲地区公民信仰状况的实证研究”。许多个人项目也要做实地调研,像湖南的5个村庄、黑龙江农村、东南地区、中原地区、上海+苏南地区,以及冀中、浙南、宁夏、福州等地区,还有“两岸四地”;调研内容很具体很“实证”,如在校大学生对待基督教的态度之类在许多课题中都是必要选项。(参见沈璋:《也谈“宗教市场论”及其在中国大陆“宗教文化”中的卖点》,《科学与无神论》2011年第3期)
就是说,这些课题全用在对中国宗教状况的实地调研上——以学术调研的名义,用课题的形式,搜罗和组织人力,分头收集与宗教相关的国情。收集的结果有什么用呢?肯定是要做综合分析的。分析的结果给谁呢?或者说,谁会需要分析的结果呢?从这几十年的中美关系看,当然有人是很愿意笑纳的。杨凤岗还借机在中国大陆组织访谈了几百位有信仰的商人,包括五大宗教的信徒,也包括“儒商”和共产党员。对于这种特定社会阶层宗教信仰状况的“摸底”调查,说没有包含某些长远意图,恐怕不会有人相信。至于“暑期进修班”和“教师进修班”的举办,其程序和内容往往逸出《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法》乃至宪法的约束之外,变成了意识形态领域宗教渗透的渠道。结果,杨凤岗的所言所行、目的诉求以及邓普顿基金会冲撞中国底线的动作,最终导致这个项目在中国受到了严肃的查处。而杨凤岗在项目到期的第二年(2014年),通过5月5日—7日在普度大学主持“宗教自由与中国社会:典型案例学术研讨会”,“研讨了……近年来几乎所有涉及宗教的法律案件”之后,于5月14日与傅希秋、刘同苏、范学德、张伯笠、夏业良、王怡等51名“中国律师”“牧师”和“学者”一起签署一份《宗教自由普度共识》,完全推翻他自己标榜的“社会科学学者不应该膜拜任何理论,或者予以意识形态化”的主张,彻底暴露了他鼓吹建立“自由竞争”的“宗教市场”,原来“醉翁之意不在酒”,而是以否定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指导地位,推翻中国社会主义制度,破坏中国现行宪法和法律实施,危害中国政治、文化和意识形态安全为目标的政治行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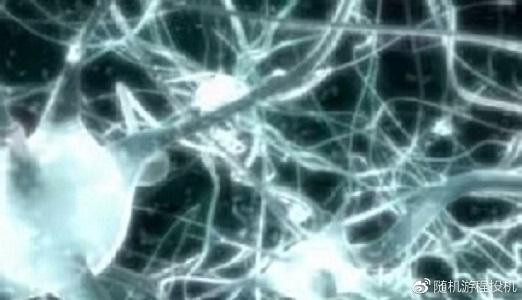
谓予不信,请看这份《普度共识》的下列内容:
“我们深切关注以下现实:
1、在中国的宪法和法律中,缺乏对宗教自由的清晰界定和足够的保护。
2、在中国的法律和社会实践中,充满对公民的宗教自由的各种误解、侵犯、歧视和迫害。
3、在中国知识分子和一般民众中,也因此对宗教自由的价值和涵义缺乏理解和基本共识。
根据一系列国际人权公约对宗教自由的界定和保护,我们相信:
……
4、宗教自由意味着对国家权力范围的一种限制,即国家不能判断任何宗教或非宗教思想体系在教义和道德上的对错和正邪,更不能以此作为处罚公民的依据,亦不能将任何一种宗教或非宗教的思想体系确立为国家的合法性依据或赋予其法律上的优先地位。
5、宗教自由意味着国家无权或没有道德上的正当性,在“合法宗教”与“封建迷信”、“正教”与“邪教”或“正统”与“极端”之间进行区分和判断。任何传统宗教或新兴宗教的成员,都不应仅仅因其相信、表达、传播和实践其宗教信仰,而受到政府的审查和法律的判断。
为此,我们热切呼吁:
无论相信任何宗教、教派或非宗教思想体系的中国公民,都有责任在法律上和公共生活中尊重、保护和争取上述宗教自由的原则和价值。”
《普度共识》的签署者,很多具有“基督徒”的身份。他们终于告诉了人们,杨凤岗心目中基督徒的“关心社会公共事务”和所谓“社会责任感”是什么货色。《普度共识》完全代表“三色市场”理论的现实政治诉求,为杨凤岗教授的项目向他的资助者、也向他自我坎陷其间的那个“基督教社会”交出了一份只有一种色彩的结题报告。
早在2011年,《科学与无神论》杂志就刊登过署名沈璋的《也谈“宗教市场论”及其在中国大陆“宗教文化”中的卖点》一文(见《科学与无神论》2011年第3期。作者采用笔名,是因为作为一位中国宗教学术界的老前辈,不想造成对后生晚辈实行“降维打击”的印象)。杨凤岗在《来龙去脉》中不吝言词和敌意对批评他的“无神论者”大张挞伐,很大程度上是因为这篇文章对“宗教市场论”及“中国宗教三色市场论”的政治面目给予了最犀利的揭露。我想再次引用沈璋先生的观点,作为本篇文字的收尾。
对于“宗教市场论”的实质,沈璋先生指出:
“‘宗教市场论’是为宗教高速扩大势力支招的。它把神灵当作商品,把宗教组织和神职人员当作公司和商人,将信徒和俗众当作需求者,而社会和文化领域则是宗教市场或潜在市场。它发现的‘信仰法则’是:一神教最具竞争力,多神教软弱无能;‘张力’和‘排他性’是宗教得以强大的内驱力,宗教冲突,特别是担当社会冲突的载体,是吸引教徒“委身”最有力的渠道。它把宗教的经济收益定为最高利益,鼓动社会一切领域都应该对宗教开放,自由竞争,蔑视民主宪政,抨击国家主导,属于宗教至上、宗教无政府思潮。其在中国是向依法治国的方针挑战,直接冲击‘教育与宗教相分离’的国家立法。”
“此书(指《信仰的法则》一书——引者)的观点确有特色:反对一般研究者认为宗教有‘非理性’的一面,而是着力抬举‘理性’,采用‘实证’的方法,并因此自名‘科学’;同时否认‘世俗化’在淡化宗教热情和促使宗教衰退中的事实,为的是把宗教也纳进‘市场’这个最世俗的领域。据此,它反对国家宪法对宗教的主导地位和政府依法监管的权力,而让宗教无政府取得像市场无政府一样的效用;最后是鼓吹宗教‘张力’,强化宗教‘排他性’,从社会冲突中挣得市场份额。”
“从基督教看,‘宗教市场论’既可以算作它的传播学——充分运用‘神’的唯一性所产生的张力与排他性布道宣教;也可以视为基督教的神学,因为‘上帝’的等级及其价值被评为至高无上,并论证了为什么‘上帝’最值钱,最值得信仰。”
沈璋先生用中国宗教的历史和现实反驳“宗教市场论”:
“它的理论与中国宗教的历史和现实南辕北辙。它只讲中了一点:中国传统宗教不具‘排他’性,但并非没有‘张力’;它诚然是软弱的,但也不缺‘竞争’。以佛教为例,它在2000年前就进入中国内地,强大的传统儒家和根深蒂固的道教,都没有抑制它的到来和发展,不久就形成三教‘不同而和’的文化格局。基督教传入中国的时间也不短,从七世纪上半叶算起,迄今也有1300多年了,中经元明清三朝,再而三、三而再地内传,直到鸦片战争骑着大炮进来,一直没有成功。相对于佛教而言,它在‘竞争’中是失败了。这一史实本身就把《信仰的法则》打得粉碎——佛教落户中国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但它把适应社会和依靠国主作为生存之道,最为重要。”
同时,沈璋先生没有忘记对中国爱国基督教界的基督教中国化努力方向给予高度评价:
“基督教最终能够落户在我们国家,决不在它的‘高张力’,而是中国爱国教徒长期从事本色化运动的结果。他们的爱国主义扎在祖国大地的最深处,与中国人民革命和建设的进步同行,为了彻底摆脱‘洋教’的丑名,至今还在奋斗着。他们面对国外各色势力的压力,遭受种种恶毒的攻击,坚定地走在自主自办的路上,这不但是中国基督教的骄傲,也是中华文化的骄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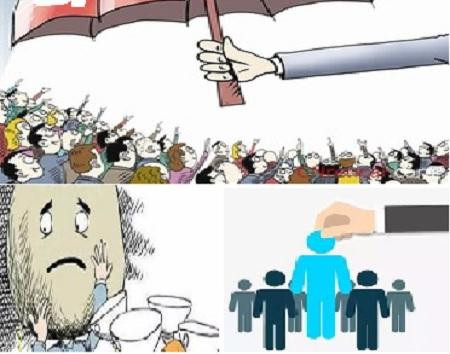
至于对杨凤岗,沈璋先生并没有在文中占用主要的篇幅,只是用几句话便点中了他的政治要害:
“就《信仰的法则》的陈述看,它是在倡导宗教至上和宗教无政府,以利益原则为动力,鼓动宗教组织不择手段地无限膨胀。客观上则是推动宗教排他、制造文明冲突和社会动乱。因此,它的信徒也在向世俗国家或国家的现代化叫板,尤其不能容忍国家依法治国、国家主权和国家管理。杨凤岗先生把中国的邪教、地下教会与合法教会分别以‘三色’分类,就是从《信仰的法则》中活剥下来的。其效果是为邪教撑腰,给地下教会开路,对合法教会进行打击。也就是说,作为二道贩子,他不仅在赚大钱。”
难怪杨教授直到多年后的今天,还要用“万箭齐发”“诛心之论”等等语汇表达对沈璋先生和《科学与无神论》杂志的愤恨,顺便攻讦他所认定的“战斗的无神论者”“反邪教、反渗透”的“横冲直撞”,直至把新时代党中央将宗教治理纳入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建设而制定的方针政策归之为“战斗无神论上位”的结果!
虽然历史真实不可能如同杨教授认知的那般肤浅,虽然我们知道杨教授刻意指责无神论在当前中国的地位,依然是“醉翁之意不在酒”,但笔者身为中国无神论者行列中的一员,承蒙杨教授这等“错爱”,还是感到与有荣焉!
2020年10月31日
(作者是河北省社会科学院研究员)

微信扫一扫|长按识别,进入读者交流群
|
|
|
|
|
|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