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大座谈会:敢问中国,路在何方
编者按:4月3日,北京大学国家战略传播研究院举办第一期战略传播沙龙。会议由北京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副教授王维佳主持,邀请新书《大道之行:中国共产党与中国社会主义》》(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5年2月出版)作者、75后青年学者鄢一龙、章永乐、欧树军、何建宇,及来自其他高校的嘉宾学者等,分享对中国政治的观察与思考。环球网评论频道特将发言内容整理成文,以飨读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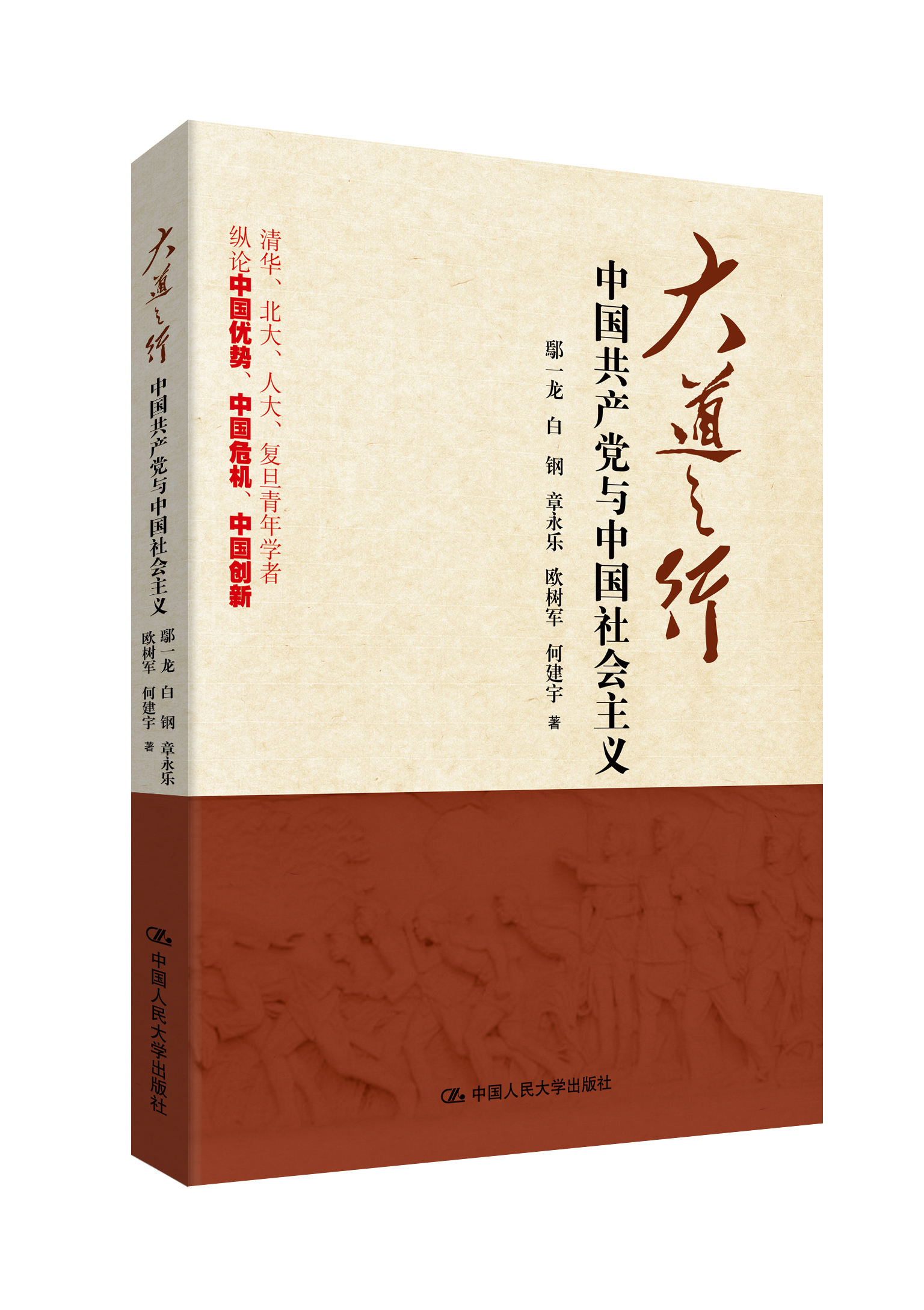
《大道之行》封面图(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5年2月出版)
欧树军:中国不该再步西方“衰退停滞”的后尘
2007年美国的次贷危机,到2008年演变成了影响至今金融危机,这就刺激我们重新理解中国所处的世界体系。这个高度资本主义化的生产体系,的确存在一些周期性的问题,尤其是在金融、财政和经济上。
1960年代末1970年代初,西方国家在二战之后,完成了一个“休养生息”阶段。经济繁荣不再持续,出现通胀、停滞甚至衰退。福利体系和人口老龄化叠加在一起,再加上经济衰退带来的经济停滞,西方国家从1970年代开始出现石油危机。这些问题在社会层面,表现为西方发达国家内部的贫富分化进程在加快。这也是《21世纪资本论》中谈到的问题。由于资本收益持续增加,而劳动收益长期止步不前,两者之间的差距持续扩大,最终导致贫富两极分化的全球化现象。
这样一个世界进程再次提醒我们,必须把中国的问题放到世界的层面,放在世界范围内,通盘思考;同时也需要更为全面的观察,不仅仅注意到全球化的积极层面,也要关注其消极的方面。(作者是新书作者、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政治学系副教授 )
章永乐:对于中国制度,我们没有妄自菲薄的理由
有一种观点认为,世上存在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政体,因为这种政体以所谓“普世价值”为追求。然而,追求一种价值,并不等于就能实现这种价值,在不同的环境中实现同一种价值,往往需要不同的制度工具。还有种观点建立在历史阶段论基础之上,认为欧美的政体在现阶段可能并不一定适合中国,但随着中国达到与欧美相当的发展阶段,就应当采取那样的政体。但这种历史阶段论的要害在于,它并没有考虑到当代世界正在发生着新的变化。
事实上,即便是欧美自身的政治体系也在经历着严峻考验。从表面上看,冷战是西方赢了,但随后经济全球化波涛汹涌,信息技术的发展塑造了新的社会互动模式,这就给西方各国带来了新的挑战。一方面,全球化使得许多发达国家的资本流向发展中国家的“资本洼地”,导致发达国家出现明显的“去工业化”趋势,国家税基被削弱,财政上“开源”变得比较困难。另一方面,人口寿命的增长,“去工业化”带来的失业问题,都使得福利支出持续增加。在全球化条件下,执政者如果向富人加税,往往会导致资本外逃,经济恶化间接导致丧失选票;执政者如果削减穷人的福利,往往会直接丧失选票。政府两头都得罪不起,既不能开源也不能节流,其结果就是高负债运作,但这就使得政府很难做有利于社会长远利益的投资。另外,社会的信息化,尤其是互联网技术的发展,使得少数人群可以在短时间内放大自己的声音,对原有的代议制民主格局形成很大冲击。各种否决力量此起彼伏,政府行为就出现了“短期化”倾向,很难有定力去做长线决策。
而对处于工业化关键时期的发展中国家来说,迫切需要的是一个能够克服短期行为,做明智的长远决策的政府。但只在形式上建立某种政体,保证不了领导力。亚投行受到发展中国家很大的欢迎,其实就很能说明问题,这些政府在基础设施建设上碰到的不仅仅是资金不足,同时也是政府领导能力不足,他们在中国看到的不仅是雄厚的资金和强大的制造能力,同时也是中国政府对基础设施建设事业的强有力的领导。而发达国家只有付出很大的努力,才能保持自己的领先地位。所以中国不必妄自菲薄,我们是与发达国家一起在探索适合人类未来的、更好的政治制度。(作者是新书作者、北京大学法学院副教授)
王洪喆:别低估了中国“认识群众”的能力
1971年,一个加拿大的传播政治学者访问中国时,写了一篇叫做《自行车之后是什么》的文章。文中他提出了一个重要的问题,当中国的社会主义建设已经实现了为最广大人民生产生活的必需品,也就是实现温饱的时候,我们下一步应该生产什么?这个问题涉及到中国将来的社会主义道路是什么样的道路的核心问题。
事实上,中国的社会主义革命之所以能走到今天,恰恰是因为我们善于分析群众。我们不仅仅知道要去发动群众这件事情,我们也知道群众从来都不是一个整体,所以如何认识群众,如何发动群众成为了中国革命非常核心的问题。
我们的目标都是一致的,要把群众组织起来。但是如果不触动现有的阶级关系和发展方式,以及其背后的文化政治和其他关系,我们如何将人民群众组织起来?或者说,将人民群众组织起来之后,人民群众会不会愿意跟党走,党能不能去有效地回应群众的需求,能否实现群众最公平、正义和共同富裕的追求?在这里,“共同富裕”不仅仅是分配意义上的,还是从马克思对于生产消费关系和分配这一整套关系的思考出发,是从毛泽东对于如何在中国这一整套政治理想和理论框架出发的。最后,我认为今天的讨论是从政治和从治理出发,但最终应该落脚在经济上。只有这样,才能实现从人民当家作主到社会共同富裕。(作者是北京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讲师)
殷之光:毛主席1956年说的那句话令我非常感动
今年是英国的大选年,BBC做了一个四集系列纪录片,将这种具有普遍性的理想概括为四个关键句:有房住,有饭吃,有工作,和有希望。这四个问题,放在世界任何一个地方,都不错。但是,如何能够真正地到达到这种理想的途径则是特殊的。我们今天不少讨论,将这种具有普遍性的理想与具有特殊性的制度两者混淆了起来。将制度误会为一种承载着普遍性目标的万灵药,甚至将制度本身视为是普遍性的终极理想。这便忽略了制度的重要特性,即它实际上产生于特定空间与时间的语境下,是实践的产物。
《大道之行:中国共产党与中国社会主义》结尾用了一句话,叫做:“全世界的劳动者联合起来!全世界的屌丝互联起来!”之前人们把自己叫做劳动人民,认为这是一个光荣的称号,为什么我们今天叫自己屌丝呢?因为劳动者代表了我们上一代人所共有的、超越性的认同。这种认同建立在我们对社会历史本质问题的理解基础上。其体现的认识论是,劳动不但创造了世界,更在劳动之中,人类获得了自我价值确证。具有政治理想价值的“人民”观念,恰是在这种基础上建立起来的。而当我们将人类自我价值确证的基础替换为消费之后,我们也便从光荣的创造财富和未来的“劳动者”,变为受压制的无希望的“屌丝”了。《大道之行》的讨论超出了简单的制度问题争辩。
毛主席一直在谈为人民服务以及群众路线的问题。他1956年时说过一句话,特别令我感动。毛主席说如果我们中国人不把自己的生活建设好的话,那就得把自己开除球籍。如果没能提高自己的生活水平的话,那我们中华民族就对不起全世界各民族,我们对人类的贡献就不大。这种表述超越了二元论和简单内外观。在他看来,中国的问题就是世界的。为中国人民负责,同样也就是对人类负责。在他看来,中国革命的政治理想是追求普遍性的,但中国本身的历史与社会环境是特殊性的。从这种特殊性走向普遍性追求的过程则是实践的,是辩证的。恰恰是这种连接普遍与特殊的辩证过程是我们今天需要认真讨论的中国道路。(作者是英国埃克斯特大学助理教授)
何建宇:维护人民主体性,党和政府需与社会合作
本书在批判基础上的建设性主要有三个面向,第一个是面向现实,尤其是面向中国的现实,中国的现实有成就也有问题,不能用两个分离的理论体系去解释,而需要用同一个体系进行,因为成就和问题都是在同一种制度下形成的。第二个是面向人民,社会再组织需要突出以劳动人民为主体的人民主体性。第三个是面向未来,我们尝试着去探讨和想象未来的制度。
这些年,社会重建是个热点话题,社会管理、社会治理等主题迅速进入中国的话语体系之中。就社会治理而言,它应该有两个面向,即面向政府的同时,也面向市场。市场经济社会由国家、市场和社会三个部门组成。我们会去讲到政府与市场的关系,也会去讲国家与社会的关系,但是很少去讲市场与社会的关系。但实际上,社会的成长还有一个更基本的功能,即平衡市场力量,或者说平衡资本力量。我们在解决会问题的时候,改革后的思路往往是很市场化的。“小政府、大社会”实际上成了“小政府、大市场”。因此,在经历了30多年市场化改革之后,需要把社会关系依附于经济关系、把人依附于资本的关系,重新往回摆。这就需要政府承担发挥保护社会、促进社会自治的责任。
中国共产党所领导的社会主义体制当中,党和政府天然应该去跟社会合作,因为不论是党的宗旨、党的历史经验都强调且善于通过群众路线的方式深入到社会当中、去跟社会合作的。因此,在当下背景下,怎样去保护人民主体,保护人民的平等参与社会治理,是政党和政府所需要去思考的。(作者是新书作者、清华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教授)
鄢一龙:有必要为中国共产党重新“寻根”
本书大致可以概括为三个主题词,一是人民至上;二是共产党领导;三是走社会主义道路。这是中国道路和中国体制的“铁三角”。针对潘维老师序言中提到党的“烂根”的现象,我们有必要在北大这个党的发源地重新来“寻根”。产生这个问题与“三个化”有关,解决之道也要破解这“三化”。第一个“化”就是我们的政治体制的“精英化”。政治的精英化是全球同此凉热的现象,这本也无可厚非,但是任何政治体制都需要给普通老百姓提供舞台。我们党最初是要建立一个普通人民群众掌握权力的政权,最重要的组织就是通过人民代表大会,让人民代表代表人民来掌握最高权力。然而,现在各级人大代表中,真正的一线工农代表数量少,党组织也出现精英化的趋势,农民、工人党员比例已经不足40%。
第二个“化”是社会的“科层化”。科层化是韦伯说的现代社会的基石。但是科层化并不一定意味着“官僚化”。1933年,当时毛泽东同志带领军队打仗的时候,军队要求的纪律性要比企业、学校强多了,但是他当时还是要走群众路线。当时有一个排长,官僚习气比较重,他习惯打骂和侮辱士兵。毛泽东得知这个事情以后就专门开了一个军人大会,他在那个会上讲了一段话,值得我们铭记:干部和士兵只是分工上的不同,政治人格上一律平等,大家都是为了全国各族人民求解放,谋幸福这个共同目标走到一起的,因此,要严禁干部打骂士兵,这是第一条。第二,士兵自觉地服从尊重领导,服从指挥,遵守纪律。这个故事告诉我们,越是并肩作战的队伍,越是能够无往而不胜,这是人民军队根本不同与国民党军队之处。科层制和民主是可以兼得的。
第三个“化”是过度市场化。如何在市场化条件下保持党的主体性?本书中白钢提到一个重要的观点,就是在市场化的条件下保持党的主体性,要使党的立足点放在老百姓身上,而不是资本家身上。只有我们真正地实行人民民主,让劳动者享有管理国家、管理社会、管理企业的根本权利,共产党才能找到自己的根。(作者是新书作者、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助理教授)

微信扫一扫|长按识别,进入读者交流群
|
|
|
|
|
|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