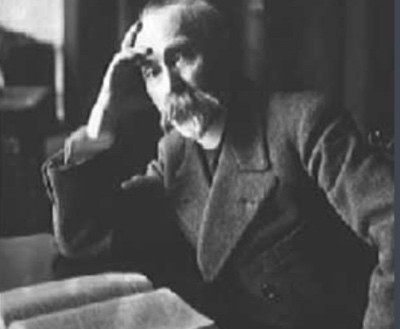普列汉诺夫真留有“政治遗嘱”吗?
1999年11月30日俄罗斯《独立报》发表了普列汉诺夫不为人知的“政治遗嘱”,在俄罗斯立即引起很大反响。围绕“遗嘱”的真伪问题,俄学者展开了热烈讨论。2000年中央编译局的《马恩列斯研究》第2期及以后几期刊登了“遗嘱”及有关争论文章的中译文,也引起我国学术界的关注。我国的一些学者怀着极大的兴趣阅读这份“遗嘱”,并就此写了不少文章。从目前所发表的文章看,几乎所有的作者都认为“遗嘱”确系普列汉诺夫所立,并称赞这是“先哲”的远见卓识。一些学者在不同的地方大量引用所谓“遗嘱”中的语句,并加以发挥,造成了一时的轰动效应。
这个“政治遗嘱”是如何出笼的呢?据称,“遗嘱”是物理数学博士、副教授,目前在非洲博茨瓦纳大学任教的俄侨尼·尼热戈罗多夫交给俄罗斯《独立报》的。他是从格·瓦·巴雷舍夫那里得到的这一“遗嘱”。巴雷舍夫自称是普列汉诺夫姐姐柳博娃·瓦连廷诺夫娜的远房亲戚。50年代巴雷舍夫刑满后在利佩茨克建筑中等技术学校任教,1958年尼热戈罗多夫在该校就读,是巴雷舍夫的学生。师生二人关系甚为密切,在交往中尼热戈罗多夫了解到他的老师藏有普列汉诺夫的“政治遗嘱”。巴雷舍夫对尼热戈罗多夫说,1918年4月因患结核病而卧床不起的普列汉诺夫,在弥留之际向自己的老朋友、孟什维克的著名活动家列·捷依奇口授了“政治遗嘱”。1918年5月普列汉诺夫去世后,该“遗嘱”由他的侄子谢·格·普列汉诺夫保存。1937年他的侄子被流放到西伯利亚,在集中营他遇到了巴雷舍夫。在他预感到生命即将结束的时候就把译成密码的“遗嘱”和其他一些文献一并托付给了巴雷舍夫(或者是告诉了他“遗嘱”当时放在何处),并向他讲清了解密方法。50年代巴雷舍夫译解了“遗嘱”,并一直保存到1974年他去世。1960年9月经巴雷舍夫允许,与他交往密切、相互信任的尼热戈罗多夫阅读并转抄了这份“遗嘱”。
面对这样一份有“先见之明”的“遗嘱”,我们首先需要搞清楚两个问题。第一,“遗嘱”是否确实存在,因为无论是普列汉诺夫的亲戚,还是保管他的档案材料、多年广泛宣传他的著作、力求完全客观地提出他思想中的所有细微变化的志同道合者,都不知晓有这样一份遗嘱。就连《独立报》主编维·特列季亚科夫在《独立报》刊登“遗嘱”时所写的按语中也提出这样的疑问:这真的是原件吗?证据何在?第二,要回答:如果普列汉诺夫确实关注俄国未来的社会民主主义,那么他给自己提出的目标是什么?又是什么促使他去写这样的“遗嘱”?是不是普列汉诺夫对社会主义、马克思主义和革命有了新的、对他来说是突然出现的理解,非要在临终前把这些讲出来?
让我们来看看俄罗斯历史学家对“遗嘱”的真实性问题是如何考证的。
2002年初夏,笔者有幸出席了在圣彼得堡召开的第六次纪念普列汉诺夫国际学术研讨会。其间,我在专访普列汉诺夫博物馆馆长塔·菲利莫诺娃时,曾问起有关“政治遗嘱”一事。她详细地向我们介绍了她对“遗嘱”是否真实的研究情况。她说:“早在准备发表普列汉诺夫的‘政治遗嘱’期间和发表之后,我都认真地对其真实性问题进行过反复研究,直到现在我仍旧认为这个‘遗嘱’是伪造的。”
菲利莫诺娃向我们证明道,普列汉诺夫博物馆历代工作人员都不知道有这样一份“遗嘱”。普列汉诺夫的遗孀罗·马·普列汉诺娃的档案也保存在普列汉诺夫博物馆,在她的档案中对此只字未提。普列汉诺夫的亲戚们对“遗嘱”也一无所知。更重要的是普列汉诺夫的遗产继承人,也就是他的妻子及两个女儿都从未谈起过这件事。
从菲利莫诺娃提供的情况看这个遗嘱的真实性确实值得怀疑。另外,菲利莫诺娃在她的《我们同时代人编造的文献》一文中谈到普列汉诺夫确实有个“遗嘱”,但绝不是《独立报》上发表的所谓“政治遗嘱”。菲利莫诺娃说:在普列汉诺夫博物馆(第1093全宗)中保存着一些文件,上面有他妻子作的标注:“若尔日(若尔日是普列汉夫的名字格奥尔基在法语中的发音)的最后想法”。这些文献无论在篇幅上还是在涵义上都根本不同于所发表的“政治遗嘱”。真正“遗嘱”只谈到了2000法郎这笔小小的资产(这笔款项的债券存放在日内瓦金库里)、他的藏书和个人物品以及他的著作遗产的版权问题。这个遗嘱总共几行字,是普列汉诺夫于1918年5月1日口授的,保存在彼得堡普列汉诺夫博物馆里。
菲利莫诺娃还分析道,如果真有这么个“政治遗嘱”,他的妻子绝对应当知道,因为她是普列汉诺夫生前最后几个月惟一与他朝夕相处的人,因此也不会长期保存在普列汉诺夫的侄子谢·普列汉诺夫手中。另外,所谓“遗嘱”记录人列·捷依奇是普列汉诺夫的老朋友,与普列汉诺夫的妻子密切交往长达23年之久,同她一起从事出版工作,并且是普列汉诺夫博物馆的创建人之一,很难想像他在这么长的时间里对如此重要的文件竟能守口如瓶。此外,普列汉诺夫博物馆第1097全宗是捷依奇本人的档案,在这些档案中也没有任何材料证明他参与过立遗嘱一事。更有说服力的是,1918年4月普列汉诺夫因患喉结核几乎不能说话,口授洋洋3万字的“遗嘱”恐怕不在情理之中,普列汉诺夫的妻子也不会允许。
从菲利莫诺娃提出的这些理由看,难道还不能证明这个“政治遗嘱”是伪造的吗?
另外,认为“遗嘱”绝不可能是普列汉诺夫所立的俄罗斯学者还从遗嘱内容上作了鉴定。
1. 从“遗嘱”中可以发现,我们当中很多人想从普列汉诺夫这位俄国第一个马克思主义者那里找到对俄国社会主义命运的预见。但是,普列汉诺夫本人能否口授出这些硬性的评定,值得怀疑。那个时代的马克思主义者对未来从不作带有任何具体时间的预测,普列汉诺夫当然也不会例外。他所表述的思想是西欧社会民主主义者在思考20世纪社会的社会主义改造前景时得出的结论。普列汉诺夫确实能够通过自己的思考沿着这一方向前进,但是事实证明,他已没有足够的时间和信息来思考俄国和欧洲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最后几年开始的社会演变的新过程。
2. 追随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普列汉诺夫不可能没察觉到,现实生活并没有证实马克思19世纪中叶的预断:在劳动者绝对贫困化、居民无产阶级化、灾难性的生产过剩危机和用暴力破坏旧社会制度这种机制下,资本主义可以比较快地过渡到社会主义。因此,普列汉诺夫的预断是极为慎重的,他拒绝俄国资本主义不会长久这一思想。普列汉诺夫根本不可能对社会主义运动作出新的解释。他也没有思考过向民主变革过渡的新机制、利用混合型经济形式、国家资本主义和国家社会主义、可以寄希望于反殖民主义运动、与议会制传统决裂等问题。
3. “遗嘱”在题目、结构和用词上处处可以看出现代人编造的痕迹,有相当多的语句完全不是普列汉诺夫及其晚期政治作品中惯用的,而是充斥于当今报刊上的术语和说法。比如:“所得税应是累进的,但不应使经营者感到窒息”,“海关政策应鼓励俄国生产者并促进国产商品提高质量”,“知识分子作为社会中最有学识的阶层的使命是把教育、人道和先进的思想带到群众中去。知识分子是民族的荣誉、良心和头脑……”等等。再如:“各种成分”、“人道化”、“国际冲突”等术语,在普列汉诺夫的语汇里是不存在的。而“俄国需要各种政治力量的团结、各种生产领域的多种成分、个人的主动精神、资本主义的进取精神和竞争、公正的上层建筑、民主化和人道化”这段话显然反映了俄国的现状。
4. 关于社会的人道化和历史的人道化、阶级对抗和矛盾趋于和解、知识分子是未来社会主义变革的领导者等思想是相当晚的时候才成为社会民主主义传统思想的。这方面的探索是20年代才开始的,而趋同论是50年代前半期才形成的概念,所以1918年4月普列汉诺夫不可能表述出这些思想。还有,当时俄国尚未发生国内战争,也未曾实行战时共产主义和新经济政策,没有借助共产国际的力量进行输出革命的尝试,那时还不曾有斯大林主义、法西斯主义,也未发生第二次世界大战和原子弹爆炸,因此普列汉诺夫“遗嘱”中关于这些问题的想法也是不可能的。
5. “遗嘱”中“关于列宁及其他一目失明的领导人”这一部分使人明显感到受了列宁几年后才口授的《给代表大会的信》和他对几个布尔什维克亲密战友的众所周知的批评性评价的影响。从普列汉诺夫对列宁的态度来看,他不可能对列宁作出“是一个伟大人物”的评价,虽然他确实不止一次承认过列宁的杰出才能。
6. “遗嘱”的某些部分与普列汉诺夫收入两卷集的《在祖国的一年》中的文章和《统一报》以及帕·阿克雪里罗得、亚·波特列索夫、波·尼古拉耶夫斯基等人所发表的专门论述普列汉诺夫的文章中的思想极为相似。因此可以认为,“遗嘱”的内容是对普列汉诺夫临终前一年某些著作和书的任意诠释。
根据上述俄罗斯学者对所谓“普列汉诺夫政治遗嘱”的考证和分析,不难得出结论:这个“遗嘱”不可能是真的。
【俄】Т.И.菲里莫诺娃、E.Л.彼特林科、С.B.秋秋金、A.A.切尔诺巴也夫
智效和 译
1999年11月30日,国家杜马选举前夕,《独立报》副刊《永久收藏》发表了Г.В.普列汉诺夫的《政治遗嘱》。它是物理数学副博士Н.И.尼热戈罗多夫(现在博茨瓦纳大学教书)和在1999年底前任国立利别茨克州方志博物馆分馆“普列汉诺夫陈列馆”馆长的А.С.别列让斯基提供付印的。与《政治遗嘱》一起,还发表了一组说明发现这个“文件”的复杂过程及其后来命运的材料。
报纸主编维塔利·特列季雅科夫向读者介绍普列汉诺夫的《政治遗嘱》时写道:“坦率地说,我们读过以后产生的第一个也是主要的问题是:这个文件的确是真的吗?证据呢?”找寻未能如愿:对读者负有道德义务的公布者本应提供原件的副本(复印的、影印的或电子版的),但编辑部没有拿到,而读者对文件本身存在与否,特别是遗嘱(何况是政治遗嘱)的形成,更是拿不出任何重要的事实予以认可或者推翻。
《独立报》的主编没有向读者隐瞒,确认《遗嘱》为真的别列让斯基的《鉴定与注解》,“多半是不能令人满意的”,还“需要历史学家和政治学家更深入的研究”。不过,有意思的是,尼热戈罗多夫在1999年12月8日致普列汉诺夫之孙、法国大使克劳德·巴托—普列汉诺夫的信,又提供了维·特列季雅科夫与前有所不同的看法。尼热戈罗多夫写道:“在《政治遗嘱》发表之前的两个月里,《独立报》主编仔细研究了文本的真实性,得出了文件属于普列汉诺夫的结论。持同样结论的还有A.别列让斯基(利别茨克普列汉诺夫陈列馆馆长)、A.戈尔捷耶夫教授(民族友谊大学教师),以及其他专家。别列让斯基先生写信给我说,菲里莫诺娃T.Т女士(我不认识她)不认为文本是真实的。但我相信,她要是读了这个文件,看法会改变的……这个文件的主要思想是,Г.В.普列汉诺夫倾向进化,否定革命带来的变化。他还以惊人的准确性预言,列宁在俄罗斯搞的社会主义即将成为过去。所有读过这一文件的人们都为Г.В.普列汉诺夫深邃的思想所震撼,并且认为,除了Г.В.普列汉诺夫本人,谁也不可能写出如此重要的文件。”(公布此信的片段得到了克·巴托—普列汉诺夫的许可,Т.И.菲里莫诺娃译自英文)同时,尼热戈罗多夫还对克·巴托—普列汉诺夫承诺,要给他捎去一份载有普列汉诺夫《政治遗嘱》的《独立报》。
克劳德·巴托—普列汉诺夫在1999年12月21日致尼热戈罗多夫的复信中写道:“至于我的祖父(按指外祖父——译者)Г.В.普列汉诺夫的《政治遗嘱》,我必须跟您说,我从来没有听说过这个文件。在祖母与我的交谈中从来没有提到过,她和祖父几乎每日交换的信件中也没有任何有关信息。我将向阿姆斯特丹和圣彼得堡,向普列汉诺夫博物馆(馆长是塔季扬娜·菲里莫诺娃)咨询有关普列汉诺夫遗嘱的事,但我怀疑文件的真实性,从来没有听说过。”
同一天,普列汉诺夫之孙给彼得堡的Т.И.菲里莫诺娃发来一信,并附有尼热戈罗多夫的信和他的复信的副本(上面我们引用了其中的片段):“尊敬的塔季扬娜,寄去尼热戈罗多夫先生来信和我的复信的副本。我不明白,为什么作为普列汉诺夫《政治遗嘱》这样的文件迄今仍然不为人知,包括我的祖母、妈妈和姨妈。由于这个原因,不管其内容如何(我从未见过也未读过),我都以为是伪造的。如果您对此了解到什么新情况,请告诉我。顺致最美好的祝愿克劳德和玛丽安娜,巴托—普列汉诺夫一家。”这里还想指出的是,别列让斯基和尼热戈罗多夫也找过《消息报》(想必是没有看上《独立报》编辑部的声望),际遇有所不同。消息报工作人员(这样称呼多半是由于“旧的、美好时代”的习惯)首先咨询了专家,而在弄清楚以后,断然拒绝发表这种“耸人听闻”的东西。特列季雅科夫在发表普列汉诺夫《政治遗嘱》的按语中建议专家对该“文件”作更深入的分析,我们响应这一建议,决定与《独立报》的读者分享自己对这个问题的看法。同时,我们想强调一下,我们之中的每一个人对普列汉诺夫的生平和活动以及他的著作遗产都有多年的研究。
总而言之,《遗嘱》究竟是打哪儿冒出来的,在哪里保存下来的?普列汉诺夫博物馆的同仁(所有几代人)都没有半点儿有关信息,在彼得堡普列汉诺夫博物馆保管的格奥尔基·瓦连廷诺维奇的遗霜Р.М.普列汉诺娃的档案也没有提到它。同普列汉诺夫博物馆始终保持着业务联系和友好交往的普列汉诺夫的亲属也对此一无所知。
普列汉诺夫博物馆(ф.1093)保存着有P.M.普列汉诺娃标注的文件——《饶尔热最后的看法》。文件无论其篇幅还是思想与发表的《遗嘱》大相径庭。顺便说一下,关于格奥尔基·瓦连廷诺维奇在彼得格勒(他被迫侨居国外37年后于1917年3月30日回到这里)生活的最后14个月,《对话》于1991年第6期、第8—15期发表了P.M.普列汉诺娃的回忆录《在国内的一年》,读者可以通过这本杂志获得足够充分的了解。
还有,50年代初从巴托—普列汉诺夫一家在巴黎的寓所窃走的文件,其组成和内容也间接为人所知,但是,其中并没有普列汉诺夫《遗嘱》。这也为上面引述的克劳德·巴托致尼热戈罗多夫和菲里莫诺娃的信所证实。
如果真有这个《遗嘱》,毫无疑问,P.M.普列汉诺娃就一定知道,她是在普列汉诺夫生命的最后岁月唯一与之寸步不离的人,是他的同道和朋友,并从1928年到1949年正式主持了普列汉诺夫博物馆的工作(1939年她去法国看望女儿,因战争滞留在那里并在10年后在那里去世)。
还要指出的是,为了安置普列汉诺夫的档案和个人图书,1928年在列宁格勒国立萨尔蒂科夫—谢德林公共图书馆专门组建了普列汉诺夫博物馆,在这里,这些年来一直保存着比公布者认为属实的《遗嘱》“叛逆”得多的文件。例如,在所谓“秘柜”中P.M.普列汉诺娃保存着自己与普列汉诺夫的私人通信。克劳德·巴托—普列汉诺夫证实,那里还有斯大林写给P.M.普列汉诺娃个人的信件(罗莎莉娅·马尔科芙娜出国甚至休假总是随身带着这些信件)。博物馆还存有直到不久以前根本不对研究者公开的文件。
因此,不能理解,作为似乎这一文件保存者的C.X.普列汉诺夫,格奥尔基·瓦连廷诺维奇的侄子,究竟凭什么把它留给自己,而不转交给他和家族成员都与之保持着联系的P.M.普列汉诺娃。
在这一事件中,Л.Г.德伊奇起的作用也是不清楚的。在23年的时间里,他与P.M.普列汉诺娃过从甚密(Л.Г.德伊奇在1941年死于疏散途中),并与她一起从事著述,是普列汉诺夫博物馆的创建人之一,要他隐匿如此重要的文件,或者不透露文件内容的信息,是不能想象的。还有,他在1922—1923年出差到法国,与普列汉诺夫的后人交涉向苏联转交格奥尔基·瓦连廷诺维奇的档案和图书事宜,有特别好的机会把《遗嘱》带到法国。再补充一点,在德伊奇的档案(普列汉诺夫博物馆ф.1097)里面也没有他参与普列汉诺夫制定《政治遗嘱》的任何痕迹。
还必须立即抛弃这样一种想法,即1918年4月普列汉诺夫尚能口授如此长的文字,当时他已几乎不能讲话了(格奥尔基·瓦连廷诺维奇患有喉结核)。由于这一原因,他的涉及不多的2000法郎金钱(存在日内瓦金库中相当于此数的债券)、图书和个人物品以及其著作遗产权利的真正的遗嘱,拢共只有几行字,是1918年5月1日普列汉诺夫口授的。遗嘱继承人是P.M.普列汉诺娃和女儿莉吉娅和叶甫根尼娅(遗嘱存在彼得堡普列汉诺夫博物馆)。
现在谈谈发表在《独立报》的《政治遗嘱》文本。我们认为,遗嘱的结构、论题、风格和用词,无可辩驳地证明这个文件是由我们当代人编纂的,而绝不会是格·瓦·普列汉诺夫,尽管文件中也有他的思想以及从普列汉诺夫作品中抄录下来的文字。在《独立报》发表的文字中,有太多今天这个时代所关注的东西,太多根本不属于普列汉诺夫及其作品特点的术语和用语,而这些倒是在如今的报刊常见的。
一些绝不是普列汉诺夫时代报刊的套话有,例如:“所得税必须促进生产,而不应使企业主感到窒息”,“关税要刺激俄罗斯生产者和促进提高本国产品质量”,“长期租赁(对俄罗斯人实行免费,对其他国家公民实行收费)是在最近几个十年里唯一的土地使用形式”,“知识分子作为社会最有教养的阶层,其使命是向群众进行教育,带给他们人文的和进步的思想。知识分子是民族的荣誉、良心和中枢……”等等。
《遗嘱》的下述之点分明说的是俄罗斯现在的情势:“俄罗斯需要各种政治力量的联合,需要在所有生产领域实行多种经济成分,需要私人的创新精神、资本家的进取心,需要非此不能提高质量和促进技术进步的竞争,需要公正的政治上层建筑、民主和人道化。”顺便指出,诸如“多种经济成分”、“人道化”、“民族冲突”等术语,在政论家普列汉诺夫的词典里是没有的。他也不会使用如此笨拙的用语,如“经济的、政治的和社会的权利公平”,因为普列汉诺夫是讲究修辞的卓越大师。
我们只是举了几个明显“非普列汉诺夫的”术语和用语的例子,而这类词语大量散见于整个《政治遗嘱》,并立即引起细心读者的关注。很说明问题的是,甚至轻率地在同一期《独立报》撰写了题为《“遗嘱”就是普列汉诺夫的》文章的А.С.别列让斯基,也预先说明,他相信文本的真实性,但不涉及《关于国家、社会主义和俄罗斯的未来》这一节,尽管他也不坚决否认这几页是普列汉诺夫的。
在《关于列宁和其他不正派的领导人》一节,明显存在列宁的、以其对亲密战友的批判著称的《致代表大会的信》的影响。我们今天所了解的普列汉诺夫对列宁的态度,抹杀了普列汉诺夫认为后者是“伟大的人物”的评价,尽管他多次承认列宁的卓越才能。要普列汉诺夫必须对他从来不认为是举足轻重的政治活动家的加米涅夫和季诺维也夫做出评价,尤其是对他根本不熟悉的布哈林的作用进行评价,预言他在列宁死后有可能成为“布尔什维克专政的领军人物”,这些同样值得怀疑。再重复一遍,此类谬误在发表的《政治遗嘱》中实在是多极了。
从公布的文本可以清楚地看出,普列汉诺夫在逝世前已经“成熟起来”,从大半生作为革命者变成了一个纯粹的伯恩施坦派进化论者。必须指出,这一说法如今能够经常从我国社会学家那里听到,他们援引普列汉诺夫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时期的立场,特别是1917年他号召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达成一致和相互让步。普列汉诺夫1914—1917年的著作,长期以来在苏联受到特别保管,如今已为广大读者所了解。他作为布尔什维克的反对派,和对1917年苏维埃活动的批判没有引起怀疑。但是,我们认为,引用“俄罗斯马克思主义之父”的具体著作甚至是他晚期的著作,不能证明他根本放弃社会主义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正如马克思所理解的那样,无产阶级专政与民主是不可分割的)。
普列汉诺夫对社会主义和革命的看法曾逐渐有所变化(就像恩格斯的看法在1890年代有所变化一样)。公认的是,普列汉诺夫坚决不接受列宁的《四月提纲》、不接受布尔什维克在俄罗斯进行社会主义革命的方针,因为俄罗斯,格奥尔基·瓦连廷诺维奇形象地说,还“没有磨出面粉”,以便随时烤制社会主义的“大蛋糕”。1917年,在世界大战的背景下,俄罗斯的大变革在他看来即使不是犯罪也是严重错误,是悲剧性的自我欺骗的结果。这就是问题的全部。然而,在确立了自始受到他谴责的布尔什维克专政以后,普列汉诺夫为什么又考虑到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仍然有效、不应修正,说“……不要灰心,从头再来,从A、B、C开始……”(见《对话》1991年第15期第101页)?虽然普列汉诺夫在1917—1918年在战争与革命的问题上原则反对布尔什维克和列宁的战术,但是,他至死仍然是革命的马克思主义者。对于马克思主义者来说,社会物质技术水平的发展和社会文化水平的发展不会取消革命改造的必要性,当然,改造的形式会有不同,并且必然伴随着国内战争和其他动荡。
发表在《独立报》上的《政治遗嘱》之所以根本不可能是普列汉诺夫的,原因还在于,作为一个学者和他那个级别的政治家,不会不明白,如此“预见”和“临别赠言”,以及稍嫌为晚的对自己错误的分析(也包括对列宁),在那种对“人的现象”进行评价的场合,完全是超越时间和地点的。而对普列汉诺夫来说,考察具体的历史现象和局势,遵守时空条件是最基本的。如同过去一样,未来也具有时间和地点特征。因此,普列汉诺夫有什么理由要向后人提出1918年的具体问题呢?普列汉诺夫对近百年后的事情做出评价能有什么实际价值,从而对当前的形势发生积极的影响呢?难道他的看法能改变已经发生的事情?不能。不过,《遗嘱》能影响人们的情绪,促使他们产生不当的认识和行为。我们在《遗嘱》最后一节看到,正是在这里普列汉诺夫企图前瞻100—200年。然而,马克思主义者从来不对某个具体期限的未来进行预测,普列汉诺夫也不例外。
格奥尔基·瓦连廷诺维奇本认为俄罗斯无产阶级是“历史的不幸者”,并用历史事实证明,俄罗斯无产阶级愿意去做一切有利于自己的事情,“不让任何人把自己置于更加不利的条件下”,而他又在不了解某个具体历史时刻会发生什么的情况下,允许自己去妄言未来的情势,这只有根本不了解思想家普列汉诺夫的人能有如此设想。
普列汉诺夫对马克思主义作为历史发展的哲学给予了高度评价,他总是强调,马克思正确地界定了资本主义以前历史发展阶段的实质和他那个时代资本主义形态的性质,指出了社会关系发展的趋势。但是,马克思、恩格斯和普列汉诺夫非常明白,这种发展“只是归根结底取决于经济”,承认历史过程发展前景具有选择性,存在各种偶然因素,等等。社会主义,正如马克思、恩格斯、普列汉诺夫和其后的列宁所了解的那样,应当是人类精神发展和有意识的选择的结果,而不仅仅是社会财富和技术进步积累的结果。
详细分析《遗嘱》的各个段落,我们认为是没有意义的。指出来源,看看每个看法和论点是打哪儿搬来的,这当然可以,不过,这将是白费工夫。《政治遗嘱》的编纂者利用了普列汉诺夫生平的实际事例和他所表达的论点和思想,又补充了许多在今天的社会政治背景下发生的变化,与此同时,强化了普列汉诺夫对1917—1918年事变看法的反布尔什维克指向。发表这件东西所选择的时机不是偶然的,尽管反共产主义,说实在的,如今是谁也不会吃惊了。
如果在广义上谈论格·瓦·普列汉诺夫的政治遗言,在这个词的哲学意义上谈论,那么可以说,伟大思想家在告别人世时,愿意把自己的祖国看作是强大的、独立的、统一的、民主的国家,她的人民是自由的和有教养的人民,而全人类则是和平和繁荣的共同体,人们按照人类简单的人道和正义的规则生活着。
这一给后人留下的遗言体现在普列汉诺夫全部大量的著作遗产中。为了把这个理想化为现实,他工作,他斗争。为此,我们深深地感谢他,并将永远怀念他。

微信扫一扫|长按识别,进入读者交流群
|
|
|
|
|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