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文斌 吴玉英:评刘再复关于莫言和诺贝尔文学奖的言论
文艺家不能用无端的想象描写历史
——评刘再复关于诺贝尔文学奖的言论
刘文斌 吴玉英
摘要:刘再复拿莫言获诺贝尔文学奖说事,鼓吹非科学的艺术“想象”观,其用心在于煽动作家“用无端的想象去描写历史”,将中共领导人民进行革命和建设的辉煌历程虚无化,以实现其不可告人的政治目的。莫言创作中滥用想象力,致使其作品出现了败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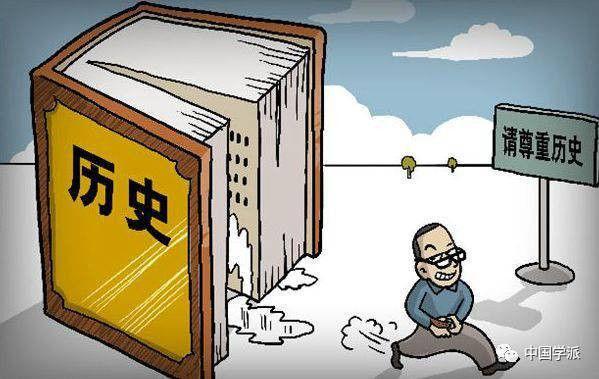
吴玉英(以下简称吴):刘老师,莫言获得2012年诺贝尔文学奖后不久,“出走美国”多年的刘再复在香港《镜报》发表了《莫言的震撼性启迪—写实、想象和叙事艺术的“三通”》一文,文中首先引经据典地搬出美国哈佛大学教授李欧梵关于我国当代文学的一番议论,并且发挥道:“李欧梵发现中国当代文学‘想象视野’不足,而莫言正在给以补充,非常有见地。其实,不仅当代文学,就‘五四’后的整个现代文学而言,也是缺乏‘想象视野’。现实主义有其优越性,但‘主义’过于强大,就削弱了想象力(我在评论金庸时,曾说金庸小说的一大功绩是填补了中国现代文学的‘想象力’的阙如)”。[1]我感觉刘再复的这些说法很不科学。
刘文斌(以下简称刘):刘再复的这些话的确充满了谬误。“想象”是指主体对脑海中已有表象进行加工而创造新形象的过程,其具体形式包括联想、幻想、虚构,是文学创作中离不开的心理活动。黑格尔早就说过:“ 真正的创造就是艺术想象活动。”[2]中外文学史上,绝对找不到一部“缺乏‘想象视野’”、“‘想象力’‘阙如’”的作品。这是文学常识范围内的事,无需赘言。至于刘再复所谓“五四”以后的“整个现代文学也缺乏‘想象视野’”的说法,同样不靠谱,众所周知,鲁迅的小说《补天》《奔月》《起死》,郭沫若的诗歌《凤凰涅槃》《天上的街市》《天狗》,毛泽东的诗词《念奴娇·昆仑》《蝶恋花·答李淑一》《七律二首·送瘟神》等等,都是中国现当代文学史上脍炙人口的名篇,它们难道都是在作者“缺乏‘想象视野’”、“‘想象力’‘阙如’”的情况下创作出来的吗?如此缺乏文学史常识的高论,竟然出自当年曾任文学研究所所长的刘再复之口,真是匪夷所思。
吴:刘再复贬损“五四”以后因“‘主义’过于强大”而“削弱(了)想象力”的“现实主义文学”,抬高“想象力惊人”的金庸、莫言的作品,这同样属于违反文学常识的低级错误吧?
刘:没错。学界普遍认为,文学创作方法主要是两种,即现实主义和浪漫主义。现实主义又称“写实主义”,强调在对人物和事件的如实描绘中发掘社会生活的本质;浪漫主义又称作理想主义,注重表现作者理想中的生活,在艺术表现手法上,以奇特的想象、大胆的夸张见长。这两种创作方法本身并无高下之分,中国文学史上的屈原、李白、吴承恩、蒲松龄、郭沫若等被称为浪漫主义作家,其体现于作品中的想象力,要比通常被称为现实主义作家的司马迁、杜甫、罗贯中、曹雪芹、鲁迅等人丰富得多,但我们难道能因此而得出结论,说前者作品的艺术价值比后者的更高吗?

吴:刘再复说莫言“之所以不同凡响,自成一大气象,就在于他不仅是‘讲故事者’(尽管他自称“讲故事者”),而且还是一个想象力惊人,表现力超群的‘魅惑者’。”[3]“想象力几乎是他的一切”。[4]这是否有点把想象力在文学中的作用夸大了呢?
刘:不是“有点”夸大了,而是无限夸大了,“想象力”也“几乎”成了刘再复评论作家作品的“一切”。其实,想象对于文学创作虽然重要,但却没有刘再复吹的那般玄乎,它并非决定作品艺术价值的唯一因素。我们不妨将刘再复赞美有加的“想象力惊人”的莫言,同他从未提及的路遥作个比较。路遥代表作《平凡的世界》运用传统现实主义创作手法,追求细节描写的准确性和真实性。小说完整地再现了社会转型时期纷繁多变的社会现象,真实地反映了社会底层奋斗者的悲欢离合和心灵世界,彰显了中华民族“自强不息”“厚德载物”的伟大精神,提供了鼓舞读者向上与向善的正能量,因而博得广大读者的喜爱。该书仅北京十月出版社2010——2013年,就出版发行了250多万册。2018年10月,新浪网“读者最喜爱的茅盾文学奖获奖作品”调查中,《平凡的世界》以71.46%的比例高居榜首;2012年2月,山东大学文学院在全国十省的城乡进行“茅盾文学奖获奖作品”接受调查,读过《平凡的世界》的读者占被调查者的38.6%,位居所有获茅盾文学奖作品之首。[5]北京大学邵燕君教授说过:“不管是在北大讲堂,还是在别的地方做报告,我会问在座的人谁读过《平凡的世界》。调查结果从没有出乎意料过———这本书是我们当代文学中流传最广的一部作品,尤其在底层。我记得在莫言刚获诺贝尔文学奖几个月后,我在一个武警部队做报告。那是一个特别大的礼堂,我问谁看过莫言的作品?没有多少人举手,再问谁看过《平凡的世界》?满场举手,齐刷刷的,吓了我一跳。”[6]
吴:2018年4月,我们学校(内蒙古师范大学)旧校区北门内的“宣传橱窗”中,公布了学校图书馆关于“2017年最受欢迎的汉文图书”调查报告(以馆藏图书借阅次数为据),结果是:路遥的《平凡的世界》位居榜首。位居前十名的其后九名依次为:当年明月的《明朝那些事》、陈忠实的《白鹿原》、卢梭的《爱弥尔:论教育》、列甫·托尔斯泰的《安娜·卡列尼娜》、乔斯坦贾德的《苏菲的世界》、米兰·昆德拉的《不能承受的生命之轻》、东野圭吾的《恶意》、霍达的《穆斯林的葬礼》、小仲马的《茶花女》。莫言的作品则榜上无名。
刘:文学创作中的想象,可看作是合乎规律的假想,而不是信马由缰地胡思乱想。黑格尔指出想象在文学创作中的重要性后,接着强调:“轻浮的想象决不能产生有价值的作品……没有深思熟虑的思考和分辨,艺术家就无法驾驶他所要表现的内容(意蕴)。”[7]作家对自己从现实生活中得来的材料进行“深思熟虑”的“思考和分辨”,对其创作中的想象是否合理至关重要。否则,就分不清哪些是反映生活本质的东西,哪些则是表面的、虚假的现象,而只能将其简单地堆积到一处,胡编乱造。这样写成的东西,势必歪曲生活,不但不能帮助读者正确地认识现实,并使其获得思想启迪,而且还会误导读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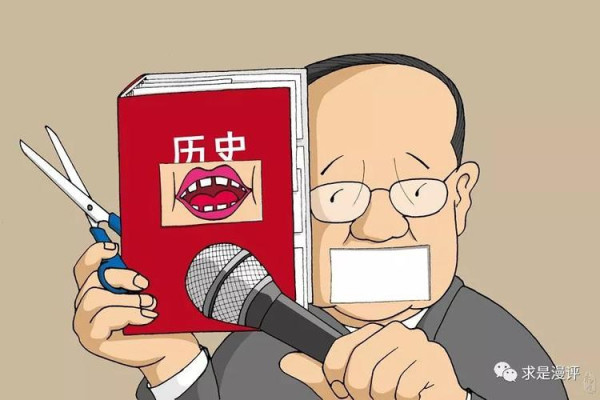
吴:刘再复在《全球化刺激下的欲望疯狂病》一文中,夸奖莫言、阎连科、余华“均把‘魔幻’、‘半魔幻’、极度夸张、黑色幽默等方式带入文本,以突出现实的荒诞属性。”[8]据他说,“西方20世纪的荒诞戏剧与荒诞小说均取得举世瞩目的成就,这些荒诞作品大体上可分为两种类型,一类是侧重于对荒诞的思辨,如贝克特的《等待戈多》;另一类是侧重于揭露现实的荒诞属性,如卡夫卡的《变形记》《审判》。无论是遥居海外的高行健还是留居中国的莫言、阎连科、余华,其作品都是侧重于批判现实的荒诞属性。而且,批判得极有力度,让人读后惊心动魄。”[9]
刘:我们知道,包括黑色幽默、荒诞派戏剧、荒诞派小说等在内的西方现代派文学,发轫于第一次世界大战前,盛行于两次世界大战之后,它反映了西方国家当时的社会危机和精神危机,也散布了虚无主义、悲观主义、个人主义、色情主义等错误思想。由于存在上述致命伤,西方现代派文学所含各个流派大都享年不长。即以刘再复津津乐道的荒诞派戏剧而言,由于它采用荒诞的手法,表现了世界与人类生存的荒诞性,具有很大片面性,致使它于上世纪50年代在法国诞生后,虽然在欧美各国产生过一定影响,但70年代初即走向衰落,前后不过只有20年左右。我国改革开放初期,一些人简单模仿西方现代派技巧创作的“伪现代派”作品,虽然当时曾得到过一些喝彩声,但时至今日,只是作为新时期文学发展中的一段弯路而被提起。
吴:您是说刘再复赞美西方20世纪荒诞派作品和莫言等人“侧重于批判现实荒诞性”作品的言论,都是些溢美之辞,不符合这些作品的实际吗?
刘:是的。贝克特的《等到戈多》及卡夫卡的《变形记》《审判》,通过夸张和象征的手法,表现了动荡中的旧世界存在的社会问题,具有一定认识作用,但它们又都存在致命的缺陷,“无穷的苦闷焦虑,极度的悲观绝望——成了现代派文学的基调。”[10]这种思想情绪,无疑会模糊人们的认识,瓦解人们的斗志,使之萎靡不振,阻碍其为改变世界而斗争。至于莫言的《酒国》、阎连科的《受活》及余华的《兄弟》等受西方“黑色幽默”“荒诞派小说”影响而创作的“侧重于批判现实的荒诞性”的小说,因其荒诞不经地“过度渲染社会阴暗面”,就像比例失调的哈哈镜,未能准确地反映社会生活,故而遭到广大读者的冷眼,只是被少数教授谈谈而已。而《酒国》则连教授们也很少谈及,只有刘再复等极少数人对它赞不绝口。
吴:刘再复对莫言小说中“挥洒自如,天马行空”般的想象力赞不绝口,并且特别指出:“最让我震撼的《酒国》《生死疲劳》和《蛙》,其想象力则几乎可以说抵达了极致。”[11]
刘:既然刘再复这样说,我们不妨对这三部小说做点分析,看看“其想象力”是如何“抵达了极致”的。

吴:刘再复说:“我非常欣赏《酒国》整部小说充满想象力,既充分现实,又超越现实,是典型的魔幻现实主义文本。”[12]刘再复这样介绍《酒国》的内容:“莫言的《酒国》写的是一个叫做‘酒国’的城市在现代化的激光照射下,完全变成了一座花天酒地的奢侈王国……酒国变成了吃人国:在酒席上吃红烧婴儿,在烹饪学院贩卖婴儿,在课堂里教授如何杀婴炒菜。吃人国里的女人再次怀孕仅仅是为了提供美餐原料即出售孩子,当被出售的孩子因水烫而哭闹的时候,妈妈所关心的并非孩子的痛苦而是担心烫伤的孩子会影响市场价格。”[13]
刘:从刘再复对《酒国》内容的介绍即不难看出,它不过是简单模仿西方小说技巧,讲述了一个荒诞离奇的故事。刘再复说它“超越现实”是真的,但说它“又是充分现实的”则不符合实际。诚如《莫言论》一书的作者张志忠教授指出的那样,《酒国》“给出的生活图景背离了人们的切身经验”,故而“在中国本土”,“很难让人们喜爱和认同”。[14]无独有偶,《莫言评传》的作者叶开先生也指出:“《酒国》虽然展现了令人眼花缭乱的文字表达能力和小说的结构能力,但‘酒国市’却跟普通人的情感产生了隔膜感,不能打动大多数人的心。”[15]陈众议研究员则直截了当地对莫言在《酒国》中滥用想象力提出批评:“莫言常使其想象信马由缰,奔腾决堤。《酒国》中的‘红烧婴儿’是其中极端例子。”[16]
吴:《酒国》出版十年后的1999年10月23日,莫言在日本东京大学的演讲中,说令他“感到骄傲”的“这部长篇《酒国》在中国几乎无人知道”[17],莫言2000年在美国科罗拉多大学演讲时又说:“此书(指酒国—笔者)出版后无声无息,一向喜欢喋喋不休的评论家全部沉默了。我估计这些叶公好龙的伙计们被我吓坏了。它们口口声声地嚷叫着创新,而真正的创新来了时,他们全部闭上了眼睛。”[18]不知您怎么看莫言的这些说法。
刘:莫言的上述说法,过高地估计了他的《酒国》,过低地估计了评论家们的鉴赏水平。评论家们面对《酒国》“全都闭上了眼睛”,并非因为他们“叶公好龙”,而是因为这部小说根本算不上“龙”,谈不上是什么“真正的创新”。作品讲述的荒诞故事,同当今中国的现实生活和十三亿人民的思想感情格格不入,书中大量露骨的丑恶描写,又令人浑身起鸡皮疙瘩,因而理所当然地遭到评论家和读者的冷眼。
吴:刘再复还吹嘘说,“酒国“主人公之一‘余一尺’之所以饮酒‘海量’,正因为体内藏着一只酒蛾,这种想象绝不亚于南美作家。”[19]
刘:他这又是在替莫言吹牛。众所周知,我国古典小说《西游记》中,就有孙悟空变成一只飞蛾,钻进铁扇公主肚子里,逼她交出芭蕉扇的描写。它表明我国明代作家吴承恩的“想象”,就已经“不亚于南美作家”了。刘再复的这种说法不但再次暴露了他崇洋媚外、数典忘祖的病态文化心理,也让这位“文学大师”又一次掉进了常识性低级错误的泥淖。
吴:关于莫言的《生死疲劳》,刘再复是这样说的:“后来莫言的想象视野不断扩张,想象力几乎是他的一切。到了《生死疲劳》,其想象视野与现实幅度的结合,更是达到了天衣无缝的地步,令人不能不叫好叫绝。”[20]“它通过一个在土改运动中被处决的名为西门闹的地主‘六道轮回’(先后投胎为驴、牛、猪、狗、猴,最后又投胎为人)的故事,呈现了从土地改革到改革开放的中国转型期的大动荡和悲喜歌哭。小说把巨大的历史沧桑与佛教轮回融合为一,然后作出神奇性的宏大叙述,令人读后不能不拍案叫绝,也令人不能不承认莫言巨大的叙事才能和艺术的原创性。”[21] 《生死疲劳》“绝对是百年来人类文学的经典极品。”[22]
刘:刘再复的上述言论仍然只说对了一半。他说莫言创作《生死疲劳》时,“想象力几乎是他的一切”是真的,但说这部小说中想象视野与现实幅度的结合“达到了天衣无缝的地步”,则不符合实际;他说《生死疲劳》显示出莫言“巨大叙事才能”是真的,但说这部小说具有“艺术的原创性”,则不符合实际。至于把《生死疲劳》说成是“百年来人类文学的经典极品”,则更是近乎于天方夜谭。
吴:请您讲具体些。

刘:常识告诉我们,文学作品由内容和形式两部分组成,二者难分难拆,相辅相成。刘再复对《生死疲劳》中的所谓“巨大历史沧桑”语焉不详,只是一味赞扬其“想象力”和“叙事才能”如何不得了。然而,思想内容正确与否及深浅程度,毕竟是衡量作品艺术价值高低不可或缺的重要尺度。而《生死疲劳》的思想内容却糟糕的很,根本经不起实践的检验。我们知道,20世纪中国革命的一个成就,就是通过土地改革彻底改变了农村的生产关系,不但终结了农村中的租佃关系与压迫性的经济结构,而且结束了土地兼并带来的治乱兴衰的历史循环。这是古老中国的一大变革。但是,莫言2006年3月与李敬泽对话《生死疲劳》时却说,这部小说中的蓝脸坚持单干、拒不加入互助组和农业合作社,“就象汪洋大海中的一道堤坝。到了20世纪80年代一分地,大家回头一想,还是那个单干户明智。”[23]。显然,莫言在这里又犯了“政治糊涂症”,他将上世纪80年代我国农村实行的土地联产承包责任制“分地”,同土地私有化的“单干”混为一谈,将其与“土改”和合作化对立起来,并据此否定农村“土改”和合作化的必要性。《生死疲劳》正是图解作者这一错误历史观的,“在小说中,蓝脸被塑造成坚持单干的一根筋,他在月光下劳作的场面具有诗意的美,而领导‘合作化’的洪泰岳,在改革开放后则成了一个失意者和‘复辟狂’。”[24]莫言在这部小说中通过六道轮回的结构、人畜互换的视角,将一个并不新鲜的故事讲述得虚幻奇诡、真假难辨,体现出他“惊人的想象力”和“巨大的叙事才能”,但把它说成“绝对是百年来人类文学的经典极品”,则绝对是“告别革命”论者满含政治偏见的胡吹乱捧。其道理很简单,“想象力”、“叙事才能”等艺术手段毕竟都是为表现作品内容服务的,都是为了更鲜明、更独特、更透彻地说人说事说理,如果作品中“惊人的想象力”和“巨大的叙事才能”,只是使作品讲述的假人假事歪理更具有迷惑力和欺骗性,则这种“想象力”和“叙事才能”不但一钱不值,而且会产生负面效应。陈晓明教授说《生死疲劳》的“全部叙事则是通过一个地主投胎为动物驴、牛、猪、狗来写它们对应的中国历史分别是‘土改’、‘大跃进’、‘文革’和‘改革开放’”,“莫言的这种叙事是对阶级斗争暴力的强烈批判”,“对阶级斗争的暴力除了把西门闹枪毙并变成动物外,没有对历史产生任何的改变,但却给家庭和人们的心灵留下抹不去的创伤。”[25]应该说,陈教授对《生死疲劳》思想内容的上述概括是基本准确的。问题来了,阶级斗争学说是马克思主义的一个基本原理,中共正是在这一基本学说指引下,领导人民群众进行新民主主义革命,才推翻了压在中国人民头上的“三座大山”,当家做了主人。《生死疲劳》却对“阶级斗争暴力”(不是“阶级斗争扩大化”——笔者)进行“强烈批判”,将它描写成“没有对历史产生任何的改变,但却给家庭和人们的心灵留下抹不去的创伤”,这就将马克思主义阶级斗争理论和中共领导人民开展的革命斗争一笔抹煞了。《生死疲劳》这种社会效果,想必是莫言始料未及的。
吴:莫言在小说《蛙》中,既通过人物之口宣传了我国实行计划生育政策的必要性,又通过作品主人公“姑姑”这一形象,揭露了一些工作人员粗暴野蛮的工作方法造成的恶果,还抨击了某些暴发户以“无性代孕”、“有性代孕”等手段实现其“超生”目标的非法行径。作品对我国实行计划生育这项“基本国策”中出现的问题,反映的真是够充分的,但读过这部小说后,却总觉得西方某些人士诬蔑我国计划生育“违反人权”的说法似乎不无道理。
刘:《蛙》的这种负面效应,原因在于作品中对计划生育政策的肯定,只有一些从报纸上抄来的议论文字,而作者在暴露计划生育工作中的问题时,却象刘再复说的那样,“把想象发挥到不可思议的地步”,[26]过度渲染社会阴暗面。莫言2012年在瑞典文学院的演讲中说:“姑姑确实是我写《蛙》时的模特,但小说中的姑姑,与现实生活中的姑姑有着天壤之别。小说中的姑姑专横跋扈,有时简直象个女匪,现实中的姑姑和善开朗,是一个标准的贤妻良母。现实中的姑姑晚年生活幸福美满,小说中的姑姑到了晚年却因心灵的巨大痛苦患上了失眠症,身披黑袍,像个幽灵一样在暗夜中游荡。”[27]当然,作者只取自己姑姑的职业和身份,塑造一个“与现实生活中姑姑有着天壤之别”的姑姑形象,这是完全可以的,并不违反创作的规律。问题在于,那个以“计生”工作人员身份出现在小说中的“专横跋扈,有时简直象个女匪”的姑姑形象,究竟有多少现实依据?这样一个近乎于冷血动物的人物,晚年却居然良心发现,深刻忏悔,认为自己“不但有罪,而且罪大恶极,不可救赎”,以至“身披黑袍,像个幽灵一样在暗夜中游荡”,人物思想性格的这种巨大变化究竟有多大可能性?评论家李建军指出:“魔幻现实主义激活了他(指莫言——笔者)的想象力,但也使他失去了对‘客观性’的敬意和感知能力,他无节制地放纵自己的主观而任性的想象力。”[28]的确,莫言常常不从生活出发,而是放纵自己的想象力,信马由缰地胡编乱造,以至将我国的计划生育政策描写成一场灭绝人性的闹剧、悲剧、惨剧。这种社会效果,同西方某些“人权卫士”诬蔑我国计划生育政策的言论有着异曲同工之妙。这也是多年遥居海外的刘再复对作者在《蛙》中“把想象发挥到不可思议的地步”情有独钟、赞不绝口的真实原因。
吴:我感觉刘再复大谈“想象力度”“想象视野”,竭力夸大想象在文学创作中的作用,他的真实目的不像是在对想象这一具体创作技巧做认真研究,而象是别有所图。
刘:没错。刘再复在其《全球化刺激下的欲望疯狂病》一文中,热情洋溢地赞美莫言的《酒国》、阎连科的《受活》以及余华的《兄弟》,夸它们“对现实的批判均带彻底性,三位作者的文本策略都是把自己的病态发现推向极致,其对现实与人性黑暗面的见证也都超越一般现实主义。”[29]他还说什么“这三部小说揭示的‘现实’均非常‘片面’,几乎完全看不到历史发展中的光彩,但获得一种‘片面’的深刻,这就是都深刻地见证现代工业文明的发展造成了人性的巨大病态和人性的整体异化。”[30]刘再复这些话的实质,就是煽动作家“超越一般现实主义”对作品真实性的诉求,最大限度地发挥自己的想象力,将我国社会生活中的某些“阴暗面”无限放大,肆意渲染,“推向极致”,直白地说,就是煽动作家将中共及其领导下的新中国“彻底”抹黑,以实现其不可告人的政治目的,用佛口蛇心这一成语比喻刘再复关于艺术想象的鼓吹,倒是贴切的。

吴:您这样说容易引起误解,以为您混淆了学术和政治的界限,所以,还是请您讲具体点,好吗?
刘:好的。刘再复说莫言的《酒国》、阎连科的《受活》以及余华的《兄弟》,“对现实的批判均带彻底性”,这几部作品“几乎完全看不到历史发展中的光彩”,“都深刻地见证现代工业文明的发展,造成了人性的巨大病态和人性的整体异化”。应该说,这些评价基本符合这三部作品的实际。但问题在于,三部作品中反映的社会生活,却同我们的社会生活存在太大的差距。众所周知,20世纪前半页,中共带领人民进行新民主主义革命,推翻了长期压在中国人民头上的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三座大山;新中国成立后,中共带领人民取得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伟大胜利,成功地发射了“两弹一星”,为实现“四个现代化”奠定了坚实的基础;粉碎“四人帮”后,中共又带领人民走改革开放之路,使得国民经济飞速发展,综合国力大大提升,人民生活极大地改善。新时期以来,中共在带领人民建设物质文明的同时,还带领大家进行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在全社会大力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各条战线的英模人物层出不穷。经常出现于各种新闻媒体的“最美乡村教师”“最美乡村医生”“最美少年”“时代楷模”“感动中国年度人物”以及被习近平总书记赞誉为“干惊天动地事,做隐姓埋名人的民族英雄”的科学家[31]等等,都充分证明这一点。无需讳言,中共在领导人民进行革命和建设中,也确曾出现过“反右派”“大跃进”“文化大革命”这些重大失误或带有全局性的失误,“现代工业文明的发展”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实行,也确曾给精神文明建设带来一定的负面影响,造成某些“道德沦丧”现象。然而,任何不坏偏见的人都会承认,我们的成就是主要的,失误是次要的,二者是九个指头和一个指头的关系。作家可以而且应该暴露我们现实生活中的“阴暗面”,以使中共和人民群众更好地总结经验,但不可只见树木,不见森林,一叶障目,不见泰山,“把自己的病态发现推向极致”,将我们日新月异、欣欣向荣的伟大祖国描绘成“几乎完全看不到历史发展的光彩”的黑暗王国、人间地狱,将我们的伟大人民描绘成“人性整体异化”的“欲望的动物、金钱的动物”,对其进行“彻底性”批判。那样做只会误导读者,使其丧失“四个自信”,不利于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
吴:刘再复对《酒国》《受活》《兄弟》这三部小说内容的概括,似乎存在可商榷之处。他的《全球化刺激下的欲望疯狂病》一文,前面说“三部小说……都深刻见证现代工业文明的发展造成了人性的巨大变态甚至人性的整体异化”,后面又说“这三部小说都写了一些守持道德底线的纯朴的中国人,以《兄弟》为例,一兄一弟就分道扬镳,和李光头不同,宋钢的传统人性并没有消失。”面对他同一篇文章中的这两种相互牴牾的说法,我们真不知道说什么才好?
刘:我们说过,自相矛盾、自打耳光,这早已成为刘再复学术生涯中的一种常态,我们对此不能太较真。重要的是,文艺家要坚持以唯物史观指导自己的创作,正确地反映历史。我们要牢记习近平总书记的指示:“历史给了文学家、艺术家无穷的滋养和无限的想象空间,但文学家、艺术家不能用无端的想象去描写历史,更不能使历史虚无化。文学家、艺术家不可能完全还原历史的真实,但有责任告诉人们真实的历史,告诉人们历史中最有价值的东西。戏弄历史的作品,不仅是对历史的不尊重,而且是对自己创作的不尊重,最终必将被历史戏弄。只有树立正确历史观,尊重历史、按照艺术规律呈现艺术化的历史,才能经得起历史的检验,才能立之当世,传之后人。”[32]
注释:
[1][3][4][8][9][11][12][13][19][20][21][22][26][27][29][30]刘再复《莫言了不起》,第43页,第46页,第44页,第31页,第31页,第37页,第44页,第28页,第44页,第44页,第39页,第95页,第94页,第113页,第31页,第27页,北京:东方出版社,2013年4月;
[2][7]黑格尔《美学》第一卷,第357页,,第358—359页,北京:商务印书馆,1979年;
[5]厚夫《为什么路遥作品历久弥新?》,《文艺报》,2013年5月27日;
[6]郝庆军《<平凡的世界>:历史与现实》,《文艺理论与批评》,2015年5期;
[10]陈燊《也谈现代派文学》,《同异集——论古典遗产、现代派文学及其他》,第150页,漓江出版社,1989年;
[14]张志忠《论莫言的小说》,《文学评论》2013年第3期;
[15]叶开《莫言评传》第313页,郑州:河南文艺出版社,2008年;
[16]陈众议《评莫言》,《东吴学术》,2013年第一期;
[17]莫言《在东京大学的演讲》,莫言《用耳朵阅读》,第8页,北京:作家出版社,2012年;
[18]莫言《我在美国出版的三本书》,莫言《用耳朵阅读》,第45页,北京:作家出版社,2012年;
[23]《李敬泽与莫言对话<生死疲劳>》,莫言《碎语文学》,第272页,北京:作家出版社,2012年;
[24]李云雷《华丽而苍白——评<生死疲劳>》,李斌、程桂婷《莫言批判》,第395页,北京:北京理工大学出版社,2012年;
[25]陈晓明《“在地性”与越界——莫言小说创作的特质和意义》,《当代作家评论》2013年第1期;
[28]李建军《直议莫言与诺奖》,《文学自由谈》2013年1期;
[31]习近平《在中国科学院第十九次院士大会、中国工程院第十四次院士大会上的讲话》,《光明日报》2018年5月29日;
[32]习近平《在中国文联十大、中国作协十九大开幕式上的讲话》,《光明日报》2016年12月1日。
(作者简介:吴玉英(1980年~),女,内蒙古呼和浩特市人,现为内蒙古师范大学文学院副教授,文学博士。刘文斌(1944年~),男,内蒙古巴彦淖尔市人,内蒙古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

微信扫一扫|长按识别,进入读者交流群
|
|
|
|
|
|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