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百壮士之真真假假
88年前的这个时候,淞沪抗战正在激烈进行中,无数先烈为国牺牲,理应发文给予纪念,只是淞沪抗战题目太大,就说说八百壮士吧。
以前说过,因至今坊间仍有关于八百壮士的种种讹传,现根据新发现的史料再说一回。有不妥处,还望方家指正。

一、留下这八百壮士的目的是什么
国军88师师长孙元良、参谋长张柏亭【张柏亭是参谋长还是参谋主任,待考,这里权当参谋长】都有回忆录存世,已经将这一问题解答得十分清楚。1937年10月26日上午,孙元良接到第三战区副司令长官顾祝同(司令长官由蒋介石兼)要其率88师坚持闸北的电话,孙在电话中表示不同意见后,又派参谋长张柏亭前往顾祝同处当面陈情。下面即张的回忆中记载的顾祝同当时所说的话:
“国际联盟十一月初要在日内瓦开会,会中接受我国控诉,将讨论如何制止日军的侵略行为,所以,委员长有意要贵师在闸北作战,把一连一排一班分散,守备市区坚固建筑物及郊区大小村落,寸土必争,要敌人付出血的代价;并相机游击,尽量争取时间,唤起友邦同情。”
顾的话,要点就在最后六个字:“唤起友邦同情。”
此时的情况是,大场已于25日失守,闸北我军疲惫不堪,难以再形成有效的阻击,故决定放弃,而以主力退到南翔一带,一部退至苏州河(当时叫吴淞江)以南,组织新的防御。可九国公约会议召开在即,就这样放弃闸北,到时在列强面前不好说话,所以必须得留下若干部队在闸北坚持,以在国际会议上求得列强的同情和支持。留下哪支部队呢?委员长决定留下88师。
但委员长的意见88师的孙师长不同意,经与顾副长官讨价还价,最后决定留下该师的一个团。
26日23时,在与第88师事先沟通后,第三战区下达了第7号作战命令:
“(1)本军以达成持久抗战之目的,除以一部据守铁道沿线附近诸要点外,将南翔以东阵地逐次转移于吴淞江南岸。
“(2)中央军应派队固守北站附近彭浦、真茹车站暨南新线真茹镇、倪家巷诸要点,极力妨害敌军之前进。其北站附近据点,则由第88师派兵1团担任之,于上海西站、丰田纱厂、北新泾、姚家渡之线,沿吴淞江南岸,与左翼军联系,迅速布置新阵地。另于杜家宅、钱家宅、七家村、花家宅之线,沿虬江南岸占领前进阵地。(下略)”
命令中要求,是要88师留下的这一个团“极力妨害敌军之前进”。不过这就是官话了,几十万生力军都无法阻挡日军的进攻,以如此疲惫不堪的一个团能起到什么作用?但也只能这么说,总不能把“唤起友邦同情”写到作战命令中去吧。
命令下达后,孙师长在执行时打了折扣,没能按命令要求派兵一团,而是仅派524团的一个营,即该团1营担负此项任务。
八百壮士就是这么留下来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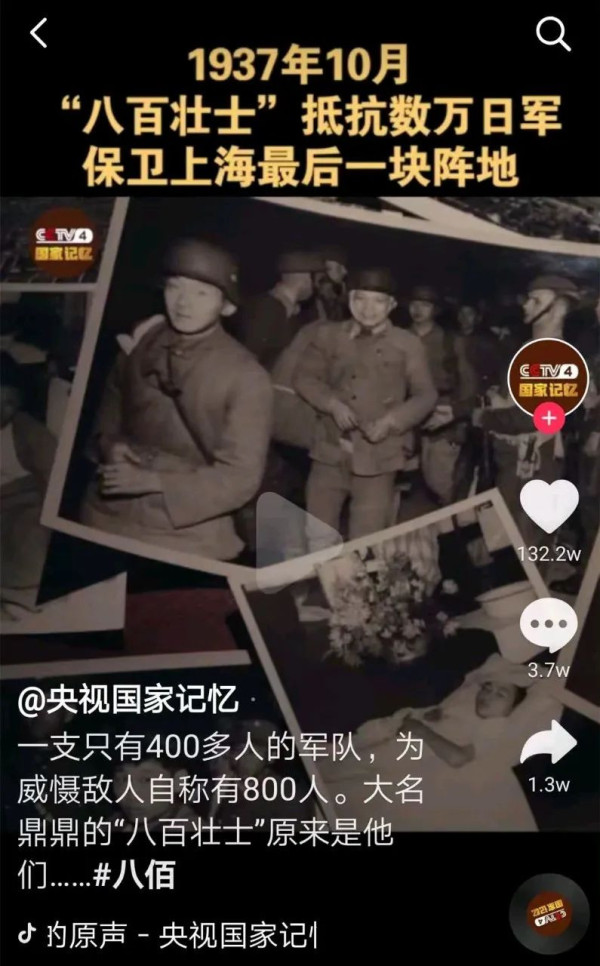
二、抵抗数万日军?保卫上海最后一块阵地?
前几年,为配合电影《八佰》造势,央视一个抖音号上,用醒目大字写着“八百壮士抵抗数万日军,保卫上海最后一块阵地”,引来疯狂点赞。
这当然是错的。
四行仓库并非上海最后一块阵地。八百壮士26日夜或27日晨进入四行仓库,30日夜或31日晨撤离,31日当天,仓库即被日军占领。
在这四天当中,淞沪战斗仍在激烈进行。在真如、在南翔、在金山卫、在龙华、在枫泾、在浦东等等,都有我重兵集结。即便在31日四行仓库失守,八百壮士被解除武装以后,也还有几十万将士成建制战斗在大上海这块土地上。到了11月12日,整个上海方告弃守。
既然四行仓库不是大上海的最后一块阵地,八百壮士自然不是全上海的最后一支孤军。
八百孤军,在10月31日之前,只是对闸北而言,因为在此之前只是闸北我军大部队已经转移。只是到了11月12日全军撤退后,被困在租界的八百壮士才成为全上海的孤军。
至于这“抵抗数万日军”吗……说啥好呢……有点让人无语。
闸北占领后,日军对四行仓库这一个营的兵力,几乎是不怎么理会,陆军并没有一兵一卒留下,而是继续向前发展进攻了。留下进攻四行仓库的只是海军陆战队的一个大队,而这个陆战大队也只是扫荡四行仓库外围后,进攻便不太积极,而改以围困为主了。
中日双方记载的关于四行仓库的战斗都极简略,寥寥数笔而已。
当然这绝不是说四行仓库没有战斗,有战斗,但战斗不惨烈,双方投入兵力都不多,飞机、重炮、坦克等都未参战,伤亡也都不大。原因是此时大场已经失守,闸北已经沦陷,日军的攻击重点已不在这里,而转移到苏州河往南了。
11月1日,谢晋元在孤军营接受中外记者采访时说道:
“四行堆栈内,除有若干沙袋外,并无如许尸体,我在内士军,共为四百二十名,撤退时为三百七十七人,其中除有十余名已殉难外,余者受伤入医院治疗中”。
11月2日,孙元良通过朱绍良转蒋介石电报称:
“死守闸北部队遵令于凌晨零时开始退出,至三时廿分全部到达预定地点。武器交由英军保存。除死三十五名,伤五十四名外,其余暂住跑马厅英兵营内。”
孙师长和谢团附关于孤军伤亡的数字不吻合,应是对战斗起止时间的统计不同所致。孙元良的统计,应是包括了杨瑞符营从上海北站到四行仓库转移途中伤亡的数字。
从孤军战死的数字看,也能揣测到战斗的强度了。以这个伤亡数,完成抵抗数万日军的任务,这得喝多大才能想得出来呀!
四行孤军的作战,没能达成第三战区命令的要求,不过这个谁都不意外,也怪不得孤军这个营,第三战区在拟定这个命令的时候,也压根就没有指望过。

三、524团1营是不是加强营
关于孤军524团1营的建制,有文章说是加强营,此说不一定准确。所谓加强单位,系指战时除建制单位外,又有另外的单位临时编入接受其指挥而形成的作战编组。但524团1营不是这样,该营在进入四行仓库时,其编制序列:
营长,杨瑞符。
一连,连长上官志标;
二连,连长邓英;
三连,连长石美豪;
机枪连,连长雷雄。
三个步兵连,一个机枪连,都是建制内单位,没看到有怎样的加强。
11月1日,有记者采访负伤在医院治疗的营长杨瑞符,杨称孤军的全部重火器计有轻机枪27挺,重机枪6挺,高射机枪2挺。以当时的编制,这27挺轻机枪和6挺重机枪都是一个步兵营编制内的,但这2挺高射机枪在不在编制内,待考。
如果非要说杨营是加强营,那么极有可能就是因为这两挺高射机枪的原因。但就因这两挺高机而将其称作加强营,真的很勉强。
该营接到独守四行仓库的命令时,有官兵423人(一说453人)。因当时闸北我军正在溃败,在向仓库集中过程中,又有伤亡和掉队,进入仓库时,实有420人(一说414人)。
至于为什么要将这四百多人说成八百人,自然是为了迷惑敌人,这个很好理解。但具体出处,又有多种说法。据该营士兵陈德松回忆:
“(27日)晚上八时左右,一位外籍记者通过租界守军,送一张纸条给谢团长,问四行仓库守军有多少人,团长答复有八百人,当天阵亡两人,伤四人。”
而该营营长杨瑞符1939年发表的《孤军奋斗四日记》中,则说:
“(28日)我们的伤兵,因为医药困难,所以在电话通了之后,就请外面向美驻军交涉,请代设法在本晚将伤兵运出去,果然有传令兵来报告,负伤士兵可以出去了。我当嘱咐出外就医的士兵说:你们出去,有人问四行仓库究竟有多少人,你们就说有八百人,决不可说只有一营人,以免敌人知道我们的人数少而更加凶横,后来哄传全世界的八百孤军的数目,就是这样来的。”
还有其他说法,但大同小异。

四、八百壮士的亮点在哪里
八百壮士的留守没能达到蒋介石预想的效果。蒋的本意,是准备以牺牲一个师的代价,来换取友邦的同情,实现对日本的制裁。这是当时他特别看重的一环,就在11月1日,其还在战地对参战部队师以上将领训话时强调:
“九国公约会议将于11月3日在比利时首都开会,这次会议对国家命运关系甚大。我要求你们做更大努力,在上海战场再坚持一个时期,至少十天到两个星期,以便在国际上获得有力的同情和支持。”
但事与愿违,还没容等到友邦的同情,却先引起了友邦的“惊诧”。因为四行仓库紧临公共租界,列强们不高兴在这里打仗,因而没等九国公约开会,就逼迫着蒋政府下令要八百壮士撤离了战场。蒋介石的这一企图落了空。其后到了九国公约会议时(11月3~24日),也没能制裁日本,也没给中国以任何实际意义上的支持。
八百壮士的抗敌行动,不管从军事上说、从政治上说,所起的作用都不大。
但是,四行孤军的留守却收获了一个意外的、超级巨大的效果,什么效果?振奋人心的效果。这一效果极大地鼓舞了全中国人民的斗志和信心。而这,大概是当初任何人都没有想到的。
由于特殊地理位置的原因,八百壮士的战斗有了一个当年绝无仅有的现象,什么现象呢?现场直播。四行仓库紧临公共租界,日军投鼠忌器,不敢把枪炮弹打到租界里去,这就给了许多躲在租界里的中国公民和各报社记者一个直接观赏并跟踪报道壮士们杀敌的大好机会。
早在进入四行仓库的第二天,八百壮士的事迹便通过各大报纸传遍大江南北、长城内外。特别是这期间又发生了一则女童军杨惠敏送旗的小插曲,这不经渲染即自带煽情的一幕,更使八百壮士的事迹倍增戏剧色彩,又进一步使这一传播在民间沸腾。从10月28日以来,有关八百壮士的报道连篇不断,其产生的爆炸般效果,远超十四年抗战任何一场战斗。
说到这里不能不服这传媒的力量。就在八百壮士坚守四行仓库的稍后,距此很近的苏州河畔也在打仗,而且打得特别激烈和残酷。在这个方向上,日军第3师团、第9师团联袂上阵,105毫米加农炮,120毫米榴弹炮,150毫米榴弹炮次第登场,交战双方反复厮杀,死伤特别惨重。光日军第3师团第34联队在这次渡河作战中就战死285人,重伤538人。第九师团整个渡河作战中伤亡达2804人,而我军光是税警总团,就由战前的25000多人打得只剩下不到2000人。从作战规模上、从双方投入兵力上、火器上、从伤亡大小上,都远远不是四行仓库作战能比得了的。
可惜的是因为当年没能被大众传媒给予报道,或者报道了但没能炒作起来,于是到了今天,四行仓库的作战几乎是妇孺皆知,可有几人知道不远处规模和激烈程度强过仓库战斗百倍不止的另一场战斗?
当年对于八百壮士暨杨惠敏献旗的报道,有炒作的成分。不过这样的炒作还是应该给予肯定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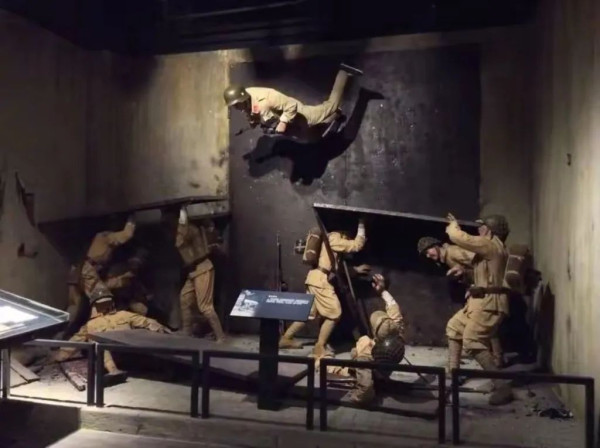
五、关于负弹跳入敌阵的陈树生之有无
近些年来,头条、抖音等自媒体上,关于陈树生负弹跳入敌盾牌方阵的故事,就和八百冷娃跳黄河、七千娃娃兵战松山、军统七姐妹宁死不屈殉国异域的故事一样,正在长热不衰地传播着。
还不仅仅是自媒体呦,今年4月6日,央视七频道也播出了这一壮举。节目中,国防大学的一名军事专家和四行仓库抗战纪念馆的馆长,就对陈树生其人其事给予了高度肯定和赞扬。
陈树生其人其事真的存在吗?
让我们看看当年孤军官长的说法。
1937年11月1日,也就是孤军撤出四行仓库的第二天,524团1营——就是八百壮士这个营——营长杨瑞符因腿部受伤住进了医院。在医院里,当记者问到在四天的战斗中表现最突出的有哪些时,杨回答:
“那天投弹炸死许多敌人的是排长殷求成干的,他因未用棍子打电筒,被敌击伤了右手……我们对官兵,只求能达到任务,这次坚守的都很有决心,谁派到任务,谁都可以达到。殷排长机会好,所以表现好……”
他想了想又说:
“还有一位上官连长和汤医官,因为移防时都在他处,直到二十八日才经过许多艰苦视死如归地赶来,钻进了四行仓库,与大家决心共存亡,都是很可佩服的。
“另外还有第三连陈排几个弟兄,在敌人堵门来攻时,他们在敌机枪猛射中英勇奋战,趴在地上弄了一脸灰,起来擦擦眼,又向敌还击,待敌机枪又射,又隐蔽到地上。这样更番苦战的精神,都很不可多得。”
看到没,表现最突出的,就这三件事了。
这三件事和负弹跳入敌盾牌方阵相比,哪一个更能给人留下深刻记忆,更能彰显国军的英武,三岁小娃娃也能做出对比,对吧。可在一群记者的追问下,杨瑞符挤牙膏一般说出上述这三件事,却没有说陈树生负弹跳入敌阵这惊天地泣鬼神的英雄壮举,这说明了啥?
说明了啥,说明陈树生这人这事儿,根本就不存在。
有人不高兴了,质问,杨营长没说有陈树生这回事儿,可也没说没有陈树生这回事儿,你咋就认为没有这回事儿呢?
打个比方,张三问李四,你家最好的交通工具是什么,李四回答说是一辆电动三轮车。他没说有轿车,可也没说没有轿车,那他家到底是有轿车还是没有轿车呢?
对于这个问题,只要脑袋没让驴踢过,是个人就不会搞错吧?
有人拿出了书面证言,证明有人亲眼看到了陈树生负弹跳入敌盾牌方阵,这怎么解释呢?
在类似孙春龙、樊建川之流的一帮人的操弄下,最近这些年的确新出现了很多髦耋老兵口述的或手写的惊人“史料”。关于陈树生,就有九十多岁的八百老兵手写的证言,有九十多岁的上海老住户手写的证言,都证明他们亲眼看到了陈树生绑了手榴弹跳入敌阵。
治史,对于回忆或口述史料,和对待档案史料一样,也有一个比对印证的问题,也有一个去伪存真的问题,特别是对同一事件互相矛盾的不同记述,因为肯定有一个假的,就更必须得做出信什么不信什么的选择。
杨瑞符以外,八百壮士所属的88师师长孙元良、524团团长韩宪元,在当年都曾接受以八百壮士为主要内容的采访,孙元良在回忆录中,也对八百壮士有很详细的记述。可孙师长也好,韩团长也好,都不曾说到有绑了手榴弹跳入敌阵这样的事儿。
孤军团长谢晋元(孤军撤入租界后,谢受委为团长),不仅多次接受采访,给媒体留下对四行仓库的战斗记述,也曾著有文字,报告孤军的战斗经过,谁又能在他的字里行间找到负弹跳入敌阵这样的事儿。
四行孤军是有组织撤退到租界的,退入租界后并未与外界隔绝,中外大大小小媒体给予了热烈关注。不仅对官长,对士兵也有大量采访报道,报道连篇累牍,可有一字一句说到过有陈树生其人其事?
没有,一字一句也没有,谁不信你们就去档案馆或图书馆找找看。
半个多世纪后,却像是变魔术似的冒出了个陈树生,你信吗?
我不信。我信谢晋元、杨瑞符及四行孤军官兵们八十年前所说的,不信这些年新冒出来的。
除非特别愚蠢的,那些坚称陈树生真有其人的,他们内心其实也不信,他们比谁都更清楚那些新冒出来的证言是咋回事儿。为啥如此这般呢?呵呵!醉翁之意不在酒,你懂的。
关于陈树生的段子,笔者曾写有专门文章给予拆穿,这里不展开。

六、八百壮士的兵员及风貌
88师和兄弟的87师、36师,是蒋委员长的御林军,亲训师,是这些年网上讹传的德械师。所以不管是电影电视剧还是其他文艺作品,都将八百壮士描绘成满员德盔,全部德械,训练特别有素的部队。当然作为文艺作品,这样表现无可厚非,但须知历史并非如此。
淞沪战场,中国军队的牺牲特别巨大,部队减员了补充、减员了补充,就跟添油一样。88师作为最早到达战场的部队,到10月26日,已经经过了六次补充,部队成分中老兵伤亡殆尽,已不足十之二三。据10月下旬补进第524团第一营的新兵樊城回忆,他编入该部时,第524团“每连一般只剩五六个人,最多也不过七八个人”,除此之外,都是新兵。524团第一营,有两个连就是整个从湖北通城保安团刚刚补入的新兵。而所谓的老兵,亦不过比湖北通城这批兵稍早进入88师而已。至于战前经德国人训练的那批老兵,到此时还有没有十分之一,我看都够呛。
坚守四行仓库的八百壮士,由于新兵成分多,其战斗力已经很成问题。88师参谋长张柏亭对大场失守后该师的战斗力说得很形象,“正如一杯茶,初沏时味道很浓,经过六次冲开水,冲一次淡一次,越冲越淡。”
这些刚刚补入的新兵,作战的技术、战术都不能和德国人帮助训练的最初的88师士兵同日而语。绝大多数新兵未经过战阵,很多新兵没见过机枪,有些新兵甚至连步枪都没打过。
至于军服、枪械,自然也肯定不会是电影中表现的那个样子。一次、二次、五次、六次的补充,每次都能有战前调整师那样的哔叽军服、35钢盔,你信吗?再说了,咱当过兵的都知道,不管你多么漂亮的军服,只要经过半天的摸爬滚打,又是泥又是土那就没法看了。
在坚守四行仓库这四天中,英雄们最苦最累的、占时最多的,不是打仗,而是修筑工事。前边说了,四行仓库的战况相对来说并不激烈,但因为大家都认为这一坚守将会是很长的时间,所以谢团附、杨营长等都是连日连夜督促官兵赶修工事。至少到28日之前,包括谢晋元、杨瑞符在内,没有人睡过觉,除了打仗就是一刻不停地赶修防御工事。那太苦太累了!有些士兵干着干着就睡着了,摔醒了又继续干。
有军迷网友说四行仓库是钢筋水泥建成,墙体坚厚,不用修就是工事,没必要劳神费力再去修它。对此我有点无语。既然是军迷,还是建议找一本筑城教材来自己看一看,看看一座具备防贼防盗功能的仓库和一处具备战术价值的防御工事有怎样的不同。
修工事自然是很脏的活,用杨瑞符的话说,弟兄们穿着短裤,满身泥污,“都像从土里爬出来的一样。”而且出于长期坚守的考虑,仓库内严禁官兵用水洗脸洗脚,就连小便也都储存了起来,以备急需。你可以想象,那些当兵的一个个会是怎样的形象了。
但也许是感觉这像农民工一般的干活不刺激,缺乏视觉冲击力,也许是像前述伪军迷那样认为四行仓库不用修本身就是工事,因而这让人心疼也让人感动的画面几乎被所有艺术家的镜头给忽略了。
我丝毫不反对影视剧中把官兵们打扮得光鲜靓丽,也丝毫不反对把镜头对准最刺激也最具观赏效果的刀光血影,我只是想说,真的战场不是那么回事儿。

七、八百壮士的结局
八百壮士的悲壮,不是在战时,恰恰相反,在四行仓库那四天的战斗是壮而不悲的。八百壮士的悲,悲在进入租界以后,而这,却往往又是电影电视剧等文艺作品不愿意表现的。
八百壮士在四行仓库只打了四天,而在进入租界后却被关押了整整四年。
四年之后又是怎样呢?更惨。
1941年12月8日,日本突袭珍珠港,太平洋战争爆发。
10日,上海伪市长陈公博写信给孤军代理团长雷雄,要孤军参加汪精卫的“和平运动”,遭到严辞拒绝。
28日,日军突入孤军营,将手无寸铁的孤军官兵全部抓捕,押解到月浦机场拘禁。
1942年2月9日,敌人又将孤军全部押解到新龙华游民习艺所,强迫重体力劳动,做苦工。
没过多久,为拆散孤军的组织,日敌又将孤军中的50人转押到南京光华门,60人转押到孝陵卫,100人转押到杭州,50人转押到溪口,50人转押到南洋的新几内亚等地,其余关押在南京原老虎桥第一监狱的俘虏收容所。被分散到各地的孤军,均强迫做苦工,其间受尽侮辱与虐待。
日本投降后,有少部分孤军士兵回到了重庆,据说有9人。由南洋做苦工的36人回到了上海。后又陆续有孤军士兵聚集到上海,达百余人。
此时的八百壮士,历经八年的摧残,能侥幸活下来已经十分不易,至于工作生活,则大都无着无落。在这方面,谢晋元夫人凌维诚女士,利用自身的影响做了很多的好事,比如托人帮助安排部分人的工作、接济部分人的生活、供给部分人的回家路费等等。
不知道为什么文艺作品都要刻意回避这些曾经为中国人大长了志气的壮士们的苦难结局。

八、关于谢晋元的留守
谢晋元是广东蕉岭人,黄埔四期毕业,淞沪开战时,先任262旅参谋主任,后接替负伤离职的前任黄永淮任524团中校团附。
查当年国军编制,除骑兵旅外,步兵旅、炮兵旅、独立旅均不设参谋长,只有一个中校参谋负参谋长之责。但在运作中,经常出现旅参谋主任一称,有些独立旅还有参谋长之称。到底是明确的职务还是仅作为变通的称呼,待考。这里权且认作参谋主任。
有人可能不解,由旅参谋主任到团附,这不是降职了吗?不不,旧军队的参谋长不像今天我军这样,它的编制职衔比较低。一般来说,军的参谋长低于师长,和旅长平级;师的参谋长低于旅长,和团长平级或略高;旅的参谋主任低于团长,和营长平级或略高。旅的参谋主任和中校团附相比,差不多,可看作等同或略低。也就是说,谢晋元由旅的参谋主任调任中校团附算不算升职不好说,但绝对不是降级。
在踞守四行仓库时,已经出现了谢团长一称,但谢晋元真的被任命为团长,是在撤入租界后。有说就在孤军撤入租界的当天,也就是10月31日,蒋介石中央明令晋升谢晋元为上校团长,晋升上官志标为中校团附,晋升雷雄为营长。原营长杨瑞符此时已因伤离队。
有文章为了拔高谢晋元的英雄形象,说师长布置任务时,谁都不想留下,只有谢晋元主动站了出来,这是错误的。谢晋元、杨瑞符等都是临危受命,事先并不知道,也没有所谓的开会商讨留守人选那么回事儿,时间也不允许。
另外,在整个淞沪战役期间,可以说是国民党军抗战中士气最高的时期。不论是中央军还是杂牌军,官兵们都是前仆后继,争先恐后,包括刚刚补入的新兵,也都是争着抢着要求上阵杀敌,中下级官兵中还极少出现贪生怕死畏缩不前的行为,说谁都不想留下牺牲,也不符当时的情况。
有两件小事,可以看出当时官兵的自觉牺牲精神。因为要一营留守四行仓库的命令来得很突然,26日晚11时作战命令下达,不容片刻停顿当晚就要全营进入仓库做好防御准备,而各连位置比较分散,那时的通信联络又只能靠传令兵,以至于当营长受领任务后,仓促间,其传令兵未能找到一连三排、三连和机枪连,命令未能传到。这几个单位也没能找到营长的指挥位置,看到大部队都在往苏州河南转进,便跟着别的部队一起行动。待到了27日早上,得知一营的任务是留下死守四行仓库后,即全部返回自觉归队。而因故短时离队的一连连长、营部医官和机枪连的一个排长,则是到了28日,才又自行进入四行仓库归队。
明知留下就是牺牲,仍然义无反顾地主动归队,这事要是搁在1940年以后,就悬了。
国民党军在抗战中士气败落,是后来的事。

九、关于孙元良在八百壮士这件事儿上的表现
孙元良是八百壮士的直接上官,88师的师长。据其在回忆录中所称,在接到顾祝同转述蒋委员长要88师留在闸北死守的电话后,孙答:
“我不同意。为什么呢?如果我们死一人,敌人也死一人,甚至我们死十人,敌人死一人,我就愿意留在闸北,死守上海。最可虑的是,我们孤立在这里,于激战之后,干部伤亡了,联络隔绝了,在组织解体,粮弹不继,混乱而无指挥的状态下,被敌军任意屠杀,那才不值,更不光荣啊!第八十八师的士气固然很高,并且表现了坚守闸北两个多月的战绩,但我们也经过五次的补充啊!新兵虽然一样忠勇爱国,但训练时间短,缺乏各自为战的技能——这是实际情况,所以我不同意。”
孙元良在历史上名声并不好,已经有太多的文章在骂他。但一码归一码,在八百壮士留守四行仓库这件事儿上,我倒没看出他做得有什么不妥。不仅没有不妥,恰恰在这个问题上,我反倒认为他比蒋介石、顾祝同等整得更明白。用他和他参谋长的话说,既然没准备打赢,而只是做出牺牲给友邦看,那么牺牲一个团和牺牲一个师没什么区别。我认为这话说得没错。
524团第一营集中踞守四行仓库,不是三战区的意思。按三战区的要求,是要这一个团分散配置,以连、以排甚至以班为单位开展游击战,在已经沦陷了的闸北敌后骚扰、迟滞敌军的进攻。88师则考虑到这些新兵,不管从思想上、组织上、军事技术上,从哪说都不适宜分散在敌后游击,故而没有按战区的要求做分散配置,而是选定建筑结构特别坚固的四行仓库,将全营做集中固守。我认为88师这么做也还是没错。
当过兵的网友都知道,新兵和老兵的心理素质并不相同,新兵很怕分散,分散后往往六神无主,战斗力将会大打折扣。何况在敌后打游击,也不是国民党军的特长。而利用公共租界对日军使用兵力和火力上的限制和四行仓库的坚固结构,将基本不具战场经验的数百新兵做集中固守,肯定比几十个人十几个人的分散出去更能形成战斗力。
总而言之吧,不管他内心真实的想法如何,从客观运用上看,我认为孙当时这一系列的处置是理性的,合乎实际的,不应该给予指责。至于在这之前和之后他的所作所为,那是另外一码事儿了。

微信扫一扫|长按识别,进入读者交流群
|
|
|
|
|
|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