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振铎与中国图书馆事业的发展
郑振铎与中国图书馆事业的发展
全根先

郑振铎(1898—1958),笔名西谛、郭源新等,原籍福建长乐,生于浙江永嘉,我国现代著名作家、文史专家,新中国文化战线的重要领导人。早年在北京参加五四运动,与瞿秋白等人创办《新社会》杂志。1921年与茅盾等人组织文学研究会,主办《文学旬刊》。次年,主办中国最早的儿童读物《儿童世界》周刊。1923年后,长期主编《小说月报》,并先后在上海大学、燕京大学、暨南大学任教。抗战期间,留居上海,抢救民族文献,与胡愈之等人组织“复社”,出版进步书籍。建国后,历任中国科学院文学研究所、考古研究所所长、国家文物局局长、文化部副部长,全国政协委员。作为文化界的名人、新中国文物事业的奠基者和缔造者之一,郑振铎与中国图书馆事业有着不解之缘,并为之做出了独特贡献。
无私捐助,丰富馆藏
郑振铎与我国图书馆事业发展的关系,一直可以追溯到20世纪30年代。根据北京图书馆(1998年正式更名为国家图书馆)馆史资料,郑振铎曾多次为该馆捐书。如1931年7月至1932年6月《国立北平图书馆馆务报告》记载:“本馆自十八年(1929)改组,每年于国庆日举行图书展览会……二十年秋,以南省水灾奇重,特提前于九月十九日及二十日两日举行,除陈列本馆旧藏及新购珍本外,并承平、津藏书家如傅沅叔、朱翼庵、周叔弢、邢赞庭、朱逷先、郑西谛、孙伯桓诸先生之赞助,以其藏书加入展览。”[1]1932-1933年度报告称,向该馆赠书的人士主要有:“……郑振铎、蒋复璁、刘复、刘节、黎锦熙、谢国桢、丰子恺、谭新嘉、苏宗仁、爨汝僖等。赠书机构主要有工商部等。”[2]1933-1934年度向该馆赠书的人士主要有:“……郑振铎、臧克家、瞿熙邦、爨汝僖等。赠书机构有上海市政府等。” [3]另据《北京图书馆馆史资料汇编》(1909--1949)记载:1947年6月10日及7月15日,袁同礼馆长曾两次致函郑振铎,对其赠书表示感谢。[4]
另外,1935年郑振铎在上海任暨南大学文学院院长期间,还担任该校图书馆馆长。他把自己的办公室特地安排在图书馆内,人们经常看到他和图书馆人员一起工作。为了让他们提高学术研究和业务水平,他还创办了《国立暨南大学图书馆馆报》,并带头在上面发表论文,一直坚持到上海沦为“孤岛”的“最后一课”(1941年12月)。抗战期间,他还曾在上海为时在重庆的国立中央图书馆抢购善本图书。所购之书,有的辗转运到重庆,有的运往香港大学冯平山图书馆寄存。这批书后来几经周折,于1961年运到北京。
1949年10月,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文化部成立,在文化部下设文物局,负责管理全国文物、博物馆、图书馆事业,郑振铎任局长。郑振铎十分重视图书馆事业的发展,提出各省、市、自治区都必须建立一个具有相当规模的图书馆,坚持向群众开放,并为各科专家、学者提供便利;不能把图书馆仅仅办成消极的图书保存单位,应该打开大门,面向群众,为读者服务。在国立北平图书馆改名为北京图书馆(国家图书馆)后,其日常工作由郑振铎直接领导。他非常关心图书馆的发展,从领导班子的配备,到各项重要规划的实施,甚至善本、珍籍的补充入藏,都事必躬亲,关心备至。
1951年,居住在香港的陈清华生活出现一些困难,欲将所藏部分珍贵图书出让。消息传出,美国人、日本人都想收购。为了不使这批珍贵善本流失海外,时任国家文物局局长的郑振铎闻讯后,一面紧急向上级报告情况,争取财政支持,一面通过香港《大公报》社长费彝民和文物鉴定专家徐森玉之子、记者徐伯郊等,与陈清华协商,并会同北京图书馆版本目录学家赵万里,终于在1955年购回第一批陈氏藏书104种,其中包括被誉为“无尚神品”的南宋世彩堂校刻的《昌黎先生集》《河东先生集》,北宋刻递修本《汉书》,南宋乾道七年(1171)建安蔡梦弼东塾校刻的二家注本《史记》,蒙古宪宗六年(1256)碣石赵衍校刻的唐李贺《歌诗编》,蒙古乃马真后元年(1242)孔元措编刻的《孔氏祖庭广记》等。这批陈氏所藏古籍,早已成为国家图书馆珍贵藏书。
1958年10月,郑振铎在出国访问途中因飞机失事不幸遇难后,其夫人高君箴女士带领全家遵循先生“化私为公”遗志,将郑先生一生节衣缩食、费尽心力收藏的17224部、94441册珍贵图书及手稿、日记等全部捐献给国家,由北京图书馆珍藏。为方便读者阅览,北京图书馆当即着手编辑出版《西谛书目》。郑振铎的这批藏书,不仅品种繁多,而且价值极高。其藏书宋元明清各代版刻都有,而以明清版本居多,手写本次之。其主要类别,有历代诗文别集、总集、词集、俗文学、版画,以及各种社会经济史料等。
大体说来,郑氏藏书中,有版画近千种,南宋嘉定年间刊本《天竺灵签》、明万历年间程氏滋兰堂刻彩色套印本《墨苑》、清康熙年间原刻初印本《芥子园画传》等,是各时期版画的代表作。收藏散曲66种,其中明钞本《张小山乐府》、明嘉靖课刻本《秦词正讹》等,“不但是很有名的,而且是非常罕见的”。俗曲有明代民歌代表作《山歌》和清代民歌代表作《白雪遗音》等。所藏小说,《西谛书目》著录682种,其中以明刊本《忠义水浒传》最负盛名,为现存《水浒》本子中最古、最完整者。另有两回本《红楼梦》,属于抄本系统,红学界称为“郑藏本”或“郑本”。
由于郑振铎本人侧重于戏曲研究,其藏书中戏曲类图书所占比重最大、最著名。尤其是明版插图本的戏曲更为出色,仅见的珍本不在少数。赵万里先生在《西谛书目》“序”中,列举了刘龙田本《西厢记》、汪氏玩虎轩本《琵琶记》等,并认为“是其中白眉”。所藏讲唱文学作品,主要包括“宝卷”和“弹词”“鼓词”。宝卷明写彩绘本《目连救母出离地狱生天宝卷》等是较早的本子,且为现存最早以“宝卷”为名的本子。弹词以清康熙刻本明杨慎撰、张三异增订的《廿一史弹词注》为目前所见最早。
此外,郑振铎所藏的诗文别集和总集,数量也相当可观,计2401种,其中以清人著作为多,约占诗文集总量的50%。地方诗文集有202种,不少是长期被人们忽视的,经他发掘出来,遂得重见著录。

滞留“孤岛”,抢救文献
在郑振铎不平凡的一生中,他抗战期间滞留上海“孤岛”,不惜冒着生命危险,抢救民族文献,避免其大量流入海外,是值得大书特书的。他说:“假如有人问我:你这许多年躲避在上海究竟做了些什么事?我可以不含糊的回答他说:为了抢救并保存若干民族的文献。” [5]当时,东南各省著名藏书家所藏古籍大半散入上海旧书市,美、日及伪满汉奸都在纷纷攫取。美国国会图书馆东方部主任赫美尔甚至扬言:“中国珍贵图书,现在源源流入美国,举凡希世孤本,珍稿秘藏,文史遗著,品类毕备,”将来要研究中国历史、哲学等,“或将以华盛顿及美国各学府为研究所矣。” [6]对此,郑振铎异常愤怒和忧虑,决心不惜一切代价,给予有力回击。1938年5月,郑振铎为国家抢救购置了一部极为珍贵的《脉望馆抄校本古今杂剧》。1939年底,他亲自起草并联合张咏霓、张菊生、何柏丞等人,给时在重庆的国民党政府教育部和管理中英庚款董事会等处写信。1929年1月5日,他又给重庆当局拍去一份电报,痛陈江南文献正处劫难之中,强烈要求当局拨款予以抢救。当时,恰好南京中央图书馆存有一笔法币约百万余元,是战前中英庚款董事会拨给该馆的建筑费,该馆尚未动土,即因战乱迁移。重庆当局于是决定将这一款项用于抢救文献,并指派中央图书馆馆长蒋复璁潜往上海与郑振铎等人相商。1月19日,在张元济家中,郑振铎、张元济、张咏霓、何柏丞、张凤举、蒋复璁等人开会,宣布成立文献保存同志会,并由郑振铎执笔制订了办事细则。其具体分工为:张凤举与郑振铎负责采访,张元济负责鉴定宋元善本,何炳松、张咏霓负责保管经费。
郑振铎虽分工负责采访,但实际所做的,要远远超出他的职责范围。自文献保存同志会成立之日起,郑振铎除了在暨南大学授课外,所有课余时间都投入到抢救工作中。他整日接待书商,常常为购书款的多少而与书商讨价还价,煞费苦心。每天收来之书,还要进行核查、登记、编目,然后装箱运送。为了预防不测,对于重要的孤本、珍本,他还设法录副,或影印,或拍照晒印,工作相当繁重。为了动员更多的爱国文人一起加入到“抢救”工作,6月25日,郑振铎还发表了《保卫民族文化运动》一文,号召爱国进步文化工作者“要在这最艰苦的时代,担负起保卫民族文化的工作”。[7]
1941年4月,在历经一年多采访后,郑振铎终于结束了图书购置工作,开始编制“善本书目”,可谓是马不停蹄。他曾这样记述:“一年以来,瘁心力于此事,他事几皆不加闻问。”尽管工作相当艰苦,但是,他想得到这么多的好书,一切都抛之脑后。他不无自豪地说:“我辈所得,有数大特色:一是抄校本多而精;二是史料多且较专;三是唐诗多且颇精。” [8]
接着,郑振铎便开始忙于装书、寄书。这是一件相当繁重且危险的工作。上海沦为“孤岛”后,日本即派特务进驻上海邮务管理局,每天检查往来信件。当时,郑振铎发出的邮件很多,大都和抢救古籍有关,一旦被查出,抢救古籍之事将功败垂成。恰好当时唐弢(文学家)为邮局邮务员,郑振铎便通过他将购书印书的有关邮件寄到重庆、香港,以避免敌伪的检查。唐弢每天有机会在日寇检查邮件离去之后、邮袋封口之前,将委托付邮的信件投入邮袋后封口,这样万无一失。此后到重庆、香港的邮件都是走这条路,并安全抵达。
郑振铎说:“国际形势一天天紧张起来,上海的局面更一天天的变坏下去。我们实在不敢担保我们所收得图书能够安全的庋藏,不能不作迁地之计。首先把可列入国宝之林的最珍贵古书八十多种,托徐鸿宝(森玉)先生带到香港,再由香港用飞机运载到重庆去。整个打包邮寄的工作,整整地费了我们近两个月的时间。” [9]1941年6月,徐鸿宝带着第一批抢救得来的善本书赴香港。不久,他又来电催郑振铎携第二批善本书去港。原本准备先行离沪的郑振铎由于手头事多,放心不下,决定暂时不走。8月初,运书工作基本结束。
12月7日,日本轰炸珍珠港,太平洋战争爆发。次日,日军进占“租界”,上海“孤岛”最后沦陷。在暨南大学上完“最后一课”后,郑振铎的“抢救”工作也随之被迫停顿。12月16日,郑振铎离家避难。他说:“我没有确定的计划,我没有可住的地方,我没有敷余的款子。只随身携带着一包换洗的贴身衣衫和牙刷毛巾,茫茫的在街上走着。这时候我颇有殉道者的感觉,心境惨惶,然而坚定异常。” [10]
从1940年春至1941年冬,郑振铎等人为国家抢救了大量珍贵的民族文献。江南著名藏书家,包括常熟瞿氏铁琴铜剑楼、常熟赵氏旧山楼等所藏图书,凡有散出的,大都归为国有,计珍本图籍3800余种,约18000余册,其中宋元刊本300余种。“虽不能说‘应有尽有’,但在‘量’与‘质’两方面却是同样的惊人,连自己也不能相信竟会有这么好的成绩!” [11]当时国立北平图书馆《馆藏善本图书目录》录有善本书仅3900种,而文献保存同志会抢救的珍本图籍却相当于当年国立北平图书馆馆所藏之数,其成绩相当可观。叶圣陶说:“当时在内地的许多朋友都为他的安全担心,甚至责怪他舍不得离开上海,哪知他在这个艰难的时期,站到自己认为应该站的岗位上,正在做这样一桩默默无闻而有意义极其重大的工作。” [1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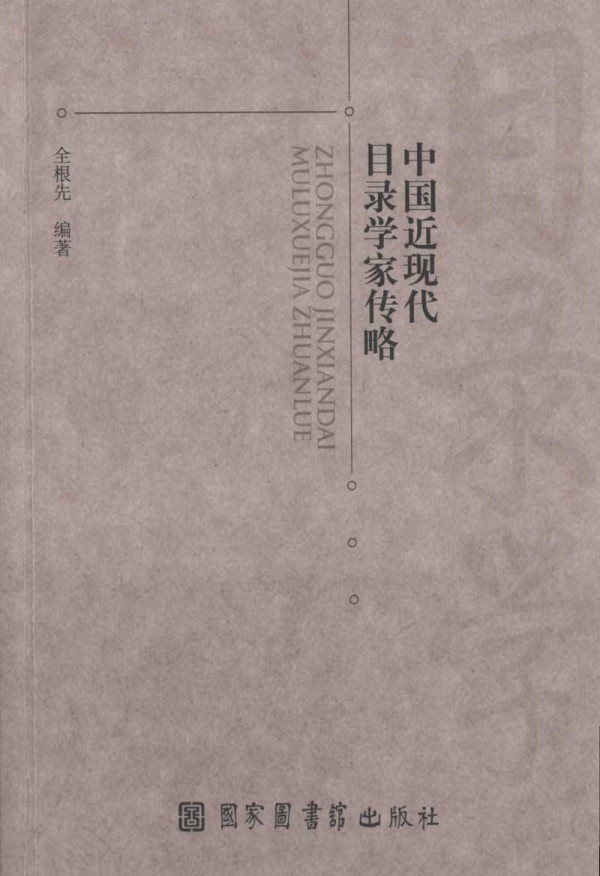
编撰书目,卓然成家
郑振铎非常重视书目的作用。他说:“版本目录的研究,虽不就是学问的本身,却是学问的门径。未有升堂入室而不由门径者,也未有研究某种学问而不明了关于某种学问的书籍之‘目录’‘版本’的。而于初学者,这种‘版本’‘目录’,尤为导路之南针,迷路的明灯。有了一部良好的关于某种学问的书籍目录,可以省掉许多人的暗中摸索之苦”。[13]因此,他一生都在研究目录学,并亲自编撰书目,为我们留下了一批宝贵的目录学遗产。
郑振铎编撰的书目,其数量之多,涉及学科之广,学术价值之高,为现代目录学家中所罕见。据统计,郑振铎一生所编撰的书目达30余种,内容涉及外国文学、古典文学、俗文学、社会学、美术史等多个学科。早在20世纪20年代,他就编撰了《文学研究会丛书目录》《关于俄国文学研究的重要书籍介绍》《关于诗经研究的重要书籍介绍》《中国小说提要》等目录学著作。30年代,他编撰了《元曲叙录》,以及他自己的藏书目录《西谛所藏善本戏曲目录》《西谛所藏散曲目录》等。40年代,他编撰了《远碧楼善本树木》《中国版画史样本》,以及反映他自己藏书的《清代文集目录》等多种书目。
建国以后,尽管公务繁忙,他仍然坚持书目编撰工作,编撰了《文学基本丛书目录》《中国文学读本目录》《唐人文集目录》《宋人文集目录》《清人文集目录》、《元人文集目录》《清词集(附清词话集)目录》《征访丛书目录》(未刊)等。这一时期的书目,以收集、介绍唐宋以来各代文集为主,有的是稿本。
郑振铎编撰的许多书目,特别是一些专科目录,具有十分重要的价值。如他编撰的关于俄国文学和苏俄社会的研究书目,关于《诗经》研究、版画目录等,多为该领域书目先期之作,为这些专科目录的编撰提供了宝贵的经验和资料。他的书目著作许多是在开展学术研究过程中产生的,具有较高的学术价值,对后人有借鉴作用。如《清代文集目录》,是他长期搜求清人文集、进行清代著述研究的一个结晶。此书收录清人文集836种,比北京图书馆所编《清代文集篇目索引》还多500余种。又如他编的《中国版画图录》,资料十分丰富,已成为今天难得的宝贵资料。
郑振铎的书目编撰,方法多样,注重实用。其中完全由他自己收集资料、编撰而成的书目,占他所撰书目的绝大部分。前面提到的多种书目,均属此类。利用他人成果,经过他整理、编辑而成的书目也有多部。如《远碧楼善本书目》,是他根据刘晦之的《远碧楼经籍目录》选编而成。刘晦之的《远碧楼经籍目录》,凡32卷、12册,收书24000部,内容繁杂,编目不尽合理,郑振铎评其为“龙蛇莫辨”,“择焉不精”,“庞杂无伦”,“翻检不易”。为了记录、保存古籍,郑振铎在原书基础上,编成《远碧楼经籍目录》5卷,使之更为合理,方便易用。
此外,他还为收藏、阅读过的许多图书撰写了题跋。这些题跋,实际上是他撰写的高质量的提要目录。他撰写的题跋,内容非常丰富,除介绍书的内容和价值外,还记录他对于版刻的品评、得书经过和读书心得等,有很高的学术价值。如他的《劫中得书记》《劫中得书续记》《明清二代评话集》《漫步书林》等,其价值是一般提要书目难以比拟的。
建国以后,郑振铎直接主持全国图书馆工作,对于书目编制十分重视。他不仅自己编撰书目,1950年他还组织有关专家、学者制定了新中国第一部图书分类法,并为它写了前言。50年代,针对一些图书馆长期积压图书、影响读者利用的实际情况,他说:“关于整理编目,应该是‘卑之无甚高论’,不要高谈什么式的分类法,只要能找到书就行。”“大型图书馆则不妨先行按大类上架,甚至全不分类即行上架,然后再编著者、书名、分类三个索引。” [14]这里,非常明显地表明了他急读者所急、尽力方便读者使用的编目思想。
但是,这不是说他不重视图书分类法的编制;相反,他主张图书馆对藏书应进行科学的、便于使用的分类。他说:“我们要有的是一种新的分类,明了而妥当的分类。” [15]他曾对邵瑞彭等人的《书目长编》分类上的失当作过中肯的批评:“希望将来编者将此书再版时,至少须看看几本靠得住的图书分类法”。[16]对于古籍目录,他说:“古书的分类编目,大可不必中外统一。”“古书的分类,还是不要多生枝节,老老实实地照四库编目,先行编出来,供需要使用这些书的人应用为是。” [17]他编撰的书目,都是在既考虑图书分类的科学方法、又切合实用的前提下编撰的。
在书目著录方面,他主张从详,以便向读者提供更多的文献信息。他曾在《小说月报》上发表专文,对沈乾一所编《丛书书目汇编》予以评论,提出希望“有志于此书(编撰丛书书目)的人,将丛书收罗完备,分为书名索引、著者索引,并于见收于几种丛书的各书之下,注明哪种丛书所收的最完备,或哪几种本子有何不同。”[18]在书目著录中,他尤其注重记录版本。他收书“不尚古本、善本,唯以应用与稀见为主”。他说:“研究较专门之学问,版本之考究,仍不能忽视。彼轻版本者,其失盖与专视版本者同。” [19]所以他自己所编撰的书目,大多对书的版本情况有详细的记述。
今天,我们传承和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应当铭记像郑振铎这样的老一辈学者的辛苦付出,继承他们的遗志,脚踏实地的工作,为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而尽自己的绵薄之力。
参考文献:
[1] [2] [3]国立北平图书馆编:《国立北平图书馆馆务报告》(缩微品),国家图书馆全国图书馆文献缩微中心。
[4]北京图书馆业务委员会编:《北京图书馆馆史资料汇编》(1909-1949),书目文献出版社1992年版。
[5] [6]李性忠:略论郑振铎抢救祖国文化典籍上的巨大贡献,见《图书馆论坛》2001年第2期。
[7] [9]韩文宁:抢救民族文献----郑振铎先生对中国古籍文化的贡献,《图书与情报》1999年第2期。
[8]陈福康主编:《郑振铎年谱》,书目文献出版社1988年版,第187页。
[10] [11] [12]郑振铎:西谛书话,三联书店1983年版,546、536、3页。
[13]郑振铎:《中国小说史料序》,见孔另境编《中国小说史料》,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年版。
[14] [17]郑振铎:谈整书,见郑尔康选编《郑振铎书话》,北京出版社1996年版。
[15]郑振铎:研究中国文学的新途径,见《中国文学研究》,商务印书馆1927年版。
[16]邵瑞彭:《书目长编》,成文出版社(台北)1978年版(影印本)。
[18]沈乾一:《丛书书目汇编》,文海出版社(台北)1970年版。
[19]郑振铎:《劫中得书记·痦堂乐府》,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年版(影印本)。
(本文原载全根先:《中国近现代目录学家传略》,国家图书馆出版社,2011年版,此处有删节修订。)

微信扫一扫|长按识别,进入读者交流群

|
|
|
|
|
|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