翻译出版不能为反华学者及其著作洗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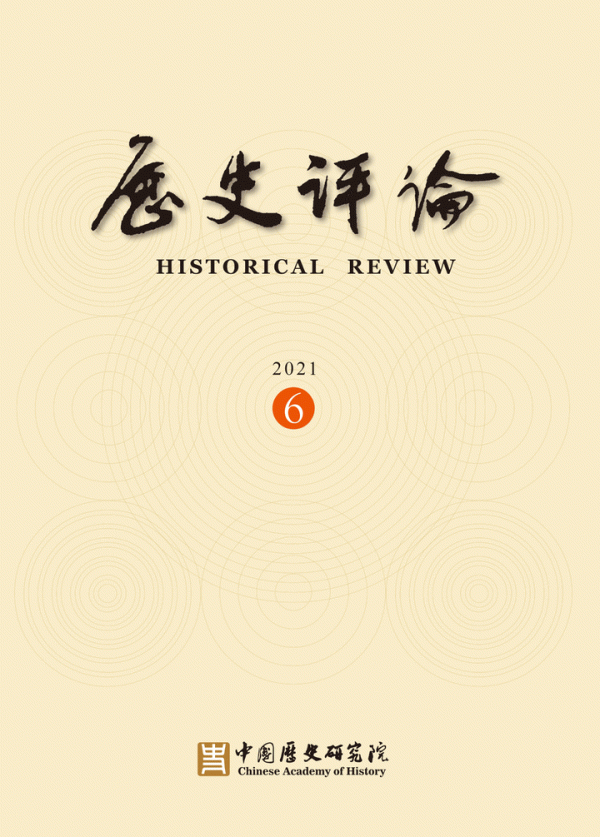
白桂思原著中诸多攻击中国主权、煽动中国边疆地区“独立”的狂悖之言,在中译本里均被节译、改写,甚至直接删而不译。这种做法具有很大的误导性和危害性,不仅使白桂思这样一位对中国偏见颇多的人士摇身一变为“中立学者”,还容易使读者丧失对该书其他内容和全书主题的应有警惕。
2009 年,美国印第安纳大学欧亚研究者白桂思(Christopher I.Beckwith)的英文著作《丝绸之路上的帝国:青铜时代至今的中央欧亚史》(Empires of the Silk Road: A History of Central Eurasia from the Bronze Age to the Present ,以下简称《丝绸之路上的帝国》)由普林斯顿大学出版社出版。原著甫一出版,笔者便阅读了该书,读后深感这是一本打着学术旗号恶意攻击中国主权、煽动边疆地区“独立”的书籍。2020年10 月,某出版集团出版了该书中译本,使笔者颇为疑惑。笔者比对中译本和原著后发现,译者显然已经意识到原著涉及中国的内容存在许多歪曲历史事实、甚至无视中国领土主权的严重问题,因此对相关内容进行了大幅度删改。由于译者未对原著的谬误及删改情况进行必要的说明,这种改译不啻为一种对原著和作者“真面目”的伪装或“漂白”,使无暇或无力阅读原著的读者受到欺骗和蒙蔽。除此之外,原著的另一重严重危害——宣扬印欧人至上的种族主义论调——却被完全保留下来。本文将对此作一澄清。
散布分裂中国言论
《丝绸之路上的帝国》最严重的现实危害在于,全书充斥着大肆攻击中国主权、分裂中国领土的狂悖之言。如原著第281页在谈及第二次世界大战前的中国革命形势及新中国的民族政策时,谬说连连。但在中译本中,这些内容均被改写,甚至直接被删除。
在谈及内蒙古自治区时,白桂思只字不提20世纪20年代以来内蒙古各族人民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积极投身反帝反封建斗争的光辉历史,径称:
Mongolian and Chinese communist revolutionaries had already taken control of Inner Mongolia by 1949. On December 3, 1949, Mao declared the country to be a part of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而在译著中,上述内容被改写为:
中国共产党在1949年已经解放了内蒙古。1949年12月2日,内蒙古自治政府改称内蒙古自治区人民政府。
译文与原文表达的意思完全相反。白氏用的是“控制”(take control of )而非“解放”(free/liberate)来定性新中国对内蒙古自治区的主权,同时刻意将内蒙古界定为“国家”(country),即“在1949年12月3日,毛(泽东)宣布这个国家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部分”。这种表述显然反映了白氏一贯所持的中国边疆地区不属于中国的政治立场,而这却被中译本完全抹去了。不仅如此,中译本所谓“内蒙古自治政府改称内蒙古自治区人民政府”,根本就不见于原文。
原著在述及西藏时称:
The Tibetans became increasingly nervous about the growing power of the Chinese communists, who openly threatened to invade their country. Internal politics and the youth of the new Dalai Lama prevented any effective measures being taken until it was too late.
In 1950-1951 the Chinese invaded Tibet with an enormous modern army. The Tibetans, outmanned and outgunned, were forced to surrender. But the Tibetans could not in any case have withstood the Chinese communists, who by the time of their victory over the Nationalists in 1949 had one of the largest, most modern, battle-hardened armies in the world.
在译著中,上述文字被表述为:
1950年至1951年,人民解放军开进西藏,西藏和平解放。到1949年解放战争胜利之时,中国人民解放军已经是当世人数最多、装备最精良、作战经验最丰富的陆军之一。当时西藏的地方实力断无任何机会阻挡他们解放西藏的步伐。
对比可知,原文中根本没有使用译文中两度出现的“人民解放军”(PLA)一词,而采用“中国人”(the Chinese)和“中国共产党人”(the Chinese communists)的表述。白桂思将解放军进藏一事定性为所谓的“中国人入侵西藏”,还诈称在此之前“中国共产党人已经公开威胁要入侵西藏”,其反华政治倾向昭然若揭。白氏描述解放军进藏的关键性动词“invade”,是“入侵”或“侵略”之意,但译文中统统被改成政治意义和感情色彩完全相反的“解放”一词。
白桂思在述及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时,更是变本加厉,妄称:
The East Turkistan Republic survived until late 1949, when the communist Chinese army marched in and occupied the country. It was incorporated back into the colony of Sinkiang (Xinjiang).
而在译著中仅仅只有一句与原文意思完全相反的话:
1949年底,人民解放军进入新疆,新疆解放。
原文主语是无视中国主权并具有殖民主义色彩的“东突厥斯坦”,并将解放军进入新疆描述成英语的“occupy”,即中文“占领”之义,而“解放”一词在整段表述中并未出现。可见,白氏根本不认同解放军解放新疆,故其随后就污蔑新疆的政治地位相当于“殖民地”(colony)。
除了歪曲史实外,白桂思还“发明历史”,他在原著第281页最后一段写道:
Similarly, East Turkistan was soon flooded with millions of Chinese. They took over the country from the Uighurs and other peoples, who had nowhere to flee to and no sympathy from major world powers such as the United States or from the United Nations or other world organizations.The Uighurs periodically attempted to fight back, but the Chinese outnumbered them and freely used their overpowering military force against them.
中译本中完全没有这段内容,因为原文表达的是“数百万计中国人接管了‘东突厥斯坦’这个‘国家’,导致当地民众既无路可逃,又得不到其他大国或世界组织的同情,只能周期性地自发反抗,结果遭到人数上远远多于他们的中国人及其武装力量的肆意镇压”。
除了上揭例证外,原著第263、282、286、292、306、310、312页等,也存在诸多攻击中国主权、煽动中国边疆地区“独立”的狂悖之言,在中译本里均被节译、改写,甚至直接删而不译。这种做法具有很大的误导性和危害性,不仅使白桂思这样一位对中国偏见颇多的人士摇身一变为“中立学者”,还容易使读者丧失对该书其他内容和全书主题应有的警惕。
以印欧人中心主义贬低其他文化
白桂思写作此书的另一个目的,是宣扬印欧人中心主义。
首先,白桂思以殷墟出土的马车乃外国输入的假说为基础,臆想当时有一小群操印欧语的双轮战车武士进入黄河中游地区,与当地人通婚,并发生语言的融合,最终使得上古汉语中有大量印欧语成分。因此,他臆断殷周时期汉语的系属有两种可能:一是其本身就是印欧语,二是受到了印欧语深度影响的东亚本土语言。当白氏作出如上判断时,并没有举出任何实证,仅用一句“最近对于上古汉语的研究成果支持如下观点,即在商代甲骨文中有大量印欧语成分,且与原始印欧语清晰相关”(原著第47页),就轻易搪塞过去。
值得注意的是,白桂思在其他研究如《汉藏问题》(“The Sino-Tibetan Problem,” Medieval Tibeto-Burman Languages, Leiden: Brill,2002, pp. 113-157)中,承认自己所提出的原始汉语与印欧语存在起源联系的观点并未得到确证。然而在《丝绸之路上的帝国》中,他以近乎肯定的语气,发表这一既未被自己证实、亦未得到学界公认的偏激之说,可见其治学态度颇不严谨。因此,该书根本不是严谨可信的学术研究成果,而是试图对读者灌输错误意识形态的洗脑之作。
即便商代马车的制作及使用原理确实来自域外,也不能说明当时黄河中游地区就已经出现颇有作为的印欧人移民群体,更不像白桂思在书中别有用心的宣传——“外来的印欧人带来了战车,对商文化产生了强势的影响乃至商王朝的建立可能与他们有关”。这就如同在中世纪,包括四大发明在内的不少中国科技成果传入欧洲,并不等于当时欧洲已有大量中国移民定居。
其次,该书世界史观也完全有违基本历史事实。白桂思罔顾史实,荒诞不经地臆造出了一个所谓的“现代文明”(modern civilization)概念,而且,这个“现代文明”又不等于人们通常理解的工业文明。他提出,“现代文明的起源可以追溯到4000 年前印欧人在欧亚大陆中心地带发起的大迁徙”,这些“原始印欧人”具有活力(dynamic)、不安现状(restless),从中央欧亚一路迁徙,对外到处征服,结果才创造出延续至今的“现代文明”或“现代世界的文化”(modern world culture),并中断了包括中国在内的四大文明古国的继续发展(原著第318—320页)。
事实上,除了中华文明从未因印欧人等任何因素中断之外,上述观点至少还有三个错误。
第一,在当下学界,原始印欧人和原始印欧语概念的适用时段为公元前3500年前后,远远早于原著中所说的公元前2千纪。这一常识性错误,说明白桂思对这一领域完全不熟悉。
第二,伊斯兰教兴起后,从伊朗以西(包括古埃及和古巴比伦文明所在区域),到北非摩洛哥等马格里布地区的主体文化、语言,是与印欧人及印欧语皆无关系的闪米特系阿拉伯文明及阿拉伯语,而闪米特人并非起源于“中央欧亚”地区。
第三,书中被白桂思极度夸大的雅利安系印度—伊朗人创造的文明,在近代以来同样经历了衰落,以致人们实在无法将其与“现代文明”对应起来,其中以印度为主的南亚次大陆更是完全沦为英国的殖民地,伊朗也长期处于半殖民地社会。
笔者认为,这种一方面在翻译中大量删改原著中某些明显的敏感文字,极力“漂白”书中错误观点,另一方面又在根本观点(如印欧人中心论、中华文明断裂论等)上一仍原著之旧的做法,极不可取。这不仅导致了不明就里的自媒体推荐该书中译本为“好书”,甚至个别报刊还以中译本的出版为由头,专门组织对白桂思的所谓“学术”专访,并发布于网络媒体以咸使知闻。对这种为害深远的舶来的历史观,我们不可不慎;而对只知其然、不知其所以然的翻译和推介,我们更应警惕。
作者单位:中央民族大学历史文化学院

微信扫一扫|长按识别,进入读者交流群
|
|
|
|
|
|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