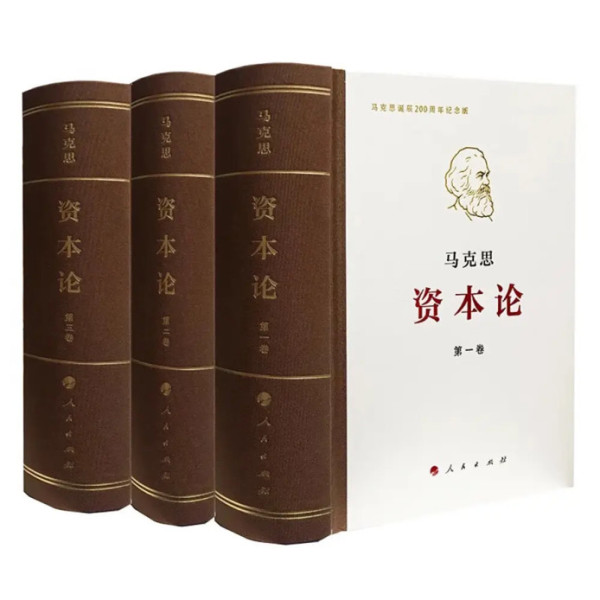马克思恩格斯是如何批判对《资本论》的各种恶意曲解的?
摘要:《资本论》的传播史很大程度上也是一部被误读史。对《资本论》的误读在不同阶段有不同表现,基本可以归纳为“研究方法”“主要理论”“学术态度”三种。马克思和恩格斯还在世时,就着重批判了这三种误读,因而,回溯马克思、恩格斯的相关批判具有重要理论启示和现实意义。当前相关研究应汲取马克思、恩格斯在批判中所体现的智慧,即以文本为依据、以说理为基础进行反驳;在反驳中树立的科学态度;在科学研究中营造良好的学术学风。
《资本论》的传播史很大程度上也是一部被误读史。自第1卷德文版发表以来的一个半世纪,《资本论》始终处于“被攻击或辩护,被解释或歪曲”[1](p.31)的境地。其中,关于《资本论》的研究方法、劳动价值理论、剩余价值理论、“转形”问题等的争论最为激烈且持续时间最久。这些争论最早可以回溯到马克思和恩格斯时期。马克思、恩格斯撰写《资本论》的“序言”和“跋”的原因在于:一是进行理论说明和自我反思;二是对曲解、误读和诋毁《资本论》的观点进行批判。马克思在《资本论》第1卷德文第二版跋中批判误读《资本论》方法的观点。恩格斯在《资本论》第1卷德文第四版序言、《资本论》第2卷序言、《资本论》第3卷序言中批判误读《资本论》主要理论的观点。期间,马克思、恩格斯还针对性地撰写了《评阿·瓦格纳“政治经济学教科书”》《马克思和洛贝尔图斯》《答布伦坦诺的文章》《价值规律和利润率》等论战性文章,以及通过书信指导其他理论家撰写了一些批判性文章。然而,这些被马克思、恩格斯批判过的观点在历史上反复出现,部分观点甚至一再重提一百多年前学者为否定《资本论》的科学性而提及甚至捏造的各种论据。正因如此,回溯马克思、恩格斯批判各种误读《资本论》的观点,对我们更准确地把握《资本论》的思想和时代价值具有重要意义。
一、《资本论》问世以来一直处于被误读境地
马克思在《资本论》第1卷德文第一版序言中就预测到《资本论》会招致敌人最激烈的批评和攻击。《资本论》的历史遭遇证实了这一点。
(一)资产阶级学者从学术角度的攻击
自《资本论》第1卷德文版问世以来,对其误读大致可分为对“辩证法”性质和“唯物主义”性质的误读两类。由于不理解“辩证法”的性质,一些学者将《资本论》的方法归为“演绎法”,莫里斯·布洛克(Maurice Block)称《资本论》运用的是“分析的方法”,茹尔·孚赫(Jules Faucher)和卡尔·欧根·杜林(Karl Eugen Dühring)将《资本论》的方法视作“黑格尔的诡辩”,弗里德里希·阿尔伯特·朗格(Friedrich Albert Lange)将《资本论》的方法幼稚地形容为“材料中的自由运动”。由于不理解《资本论》方法中“唯物主义”的性质,还有一些错误观点责备马克思“只限于批判地分析既成的事实”,[1](p.19)俄国评论家发表的《卡尔·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批判的观点》一文,虽然正确认识到《资本论》的方法是辩证法,但不理解研究方法和叙述方法的内在统一性。
19世纪70年代至恩格斯逝世期间,讲坛社会主义者攻击《资本论》的劳动价值理论、剩余价值理论、“转形”问题等,甚至恶意诋毁马克思本人。阿道夫·瓦格纳(Adolph Wagner)在《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第一卷。国民经济的一般性的或理论性的学说,第一部分:基础》一书中误读了劳动价值论,错误阐释了马克思的“交换价值”概念,最后将马克思的价值理论与李嘉图的费用理论相混淆。约翰·卡尔·洛贝尔图斯(Johann Karl Rodbertus)庸俗化理解了剩余价值理论,制造所谓“剽窃”言论,否定马克思剩余价值理论的原创性。阿尔基·洛里亚(Achille Loria)对《资本论》的攻击从第1卷一直持续到第3卷。在《资本论》第1卷出版后,洛里亚妄称马克思从未真正打算写《资本论》续卷,只是以此作为欺骗读者的手段。1885年、1894年,面对恩格斯陆续整理出版的《资本论》第2、3卷,洛里亚并没有承认失败,反而变本加厉攻击《资本论》中的价值理论。他认为,马克思的价值学说建立在“自觉”诡辩的基础上,并指责《资本论》第1卷与第3卷之间存在着难以克服的矛盾,比如剩余价值理论与利润率普遍相等的事实相矛盾、生产价格规律同价值规律相矛盾,甚至造谣《资本论》第2、3卷是恩格斯编造的。为彻底否定《资本论》的科学性,讲坛社会主义者路德维希·约瑟夫·布伦坦诺(Ludwig Joseph Brentano)则另辟蹊径,从学术规范和学术态度等方面对《资本论》展开指控。
(二)社会主义营垒内部撕开误读《资本论》的裂缝
在第二国际时期(1889—1914年),尤其是恩格斯逝世后,《资本论》乃至马克思主义理论遭到了严重误读。这些误读更多出于自称马克思、恩格斯“学生”的理论家。面对资本主义的新变化和无产阶级革命实践的新走向,以爱德华·伯恩施坦(Eduard Bernstein)为代表的修正主义者对马克思主义进行“修正”,很大程度上否定了有关劳动价值、剩余价值和平均利润率趋于下降规律的主要理论。
以伯恩施坦为代表的修正主义者将《资本论》看作一种失效的“假说”,用“具体”的改良理论逐步解构《资本论》的革命因素。首先,他们批评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哲学基础——唯物史观和历史辩证法,主张“回到康德”,企图消灭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革命内涵和唯物主义原则。其次,他们误读《资本论》中的劳动价值理论、剩余价值理论、平均利润率趋于下降规律等。伯恩施坦断言劳动价值论是“纯粹的思维的构想”,缺乏现实可行性,剩余价值理论更加成为“单纯的公式,成了一个以假说为根据的公式”。[2](p.89)同时,伯恩施坦只将平均利润率看作偶然性的“实际事实”,而不是看作规律性的“理论结构”,认为资本并不总是追求利润最大化。这不仅暴露出伯恩施坦企图否定资本主义剥削的实质,也表现出他对《资本论》所运用的“科学抽象法”的无知。最后,伯恩施坦认为恩格斯在《资本论》第3卷增补部分对价值问题的说明同样“缺乏令人信服的证明力”。[2](p.90)
与此相对,以卡尔·考茨基(Karl Kautsky)为代表的“正统派”和以格·瓦·普列汉诺夫(Georgi Plekhanov)、奥古斯特·倍倍尔(August Bebel)等人为代表的“左派”,坚决批判了修正主义。“正统派”根据许多统计材料批评修正主义对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的反驳毫无根据,并用垄断条件下工人斗争条件不断恶化的事实回击修正主义对利润率平均化的攻击。“左派”指出伯恩施坦的唯心主义历史观和形而上学思维方式,揭露了伯恩施坦反对马克思主义的基本手法。但是,无论是“正统派”还是“左派”,都重视对《资本论》第1卷“生产过程”的研究,缺乏对《资本论》三卷的整体性研究,时常会把《资本论》误读为“经济决定论”。
(三)形成东西方马克思主义解读《资本论》的两条不同路径
十月革命后,解读《资本论》主要有两条不同路径:一是“东方马克思主义”(主要指苏俄及后来的苏联),在构建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过程中对商品生产、价值规律、再生产理论等产生了一定程度上的误读;二是“西方马克思主义”开启的以“重新发现马克思主义”为口号的学术研究,在对《资本论》进行人本主义解读的同时,忽视其唯物主义性质。
十月革命胜利后,《资本论》在苏俄以及此后苏联的传播和研究中获得了新生政权的大力支持。但如何运用《资本论》指导社会主义国家经济建设,是一个全新课题,这一度导致“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消亡论”出现,认为社会主义经济建设中已不存在价值和商品的关系,所以不再需要研究以价值和商品关系为主题的政治经济学。列宁批评了这一观点,指出“即使在纯粹的共产主义社会里不也有Ⅰv+m和Ⅱc的关系吗?还有积累呢?”[3](p.619)这一批评,对于正确认识和发展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具有重要指导意义。
十月革命的胜利也开启了西方马克思主义对《资本论》进行学术解读的契机。安东尼奥·葛兰西(Antonio Gramsci)在《反〈资本论〉的革命》中认为,十月革命的胜利是“反对卡尔·马克思的《资本论》的革命”。[4](p.8)葛兰西并不是要彻底否定《资本论》,而是反对第二国际理论家阐发的“经济决定论”,企图从主体维度重读《资本论》。但这就容易在强调主体能动性的同时抽掉历史唯物主义基础。作为早期西方马克思主义的奠基者,格奥尔格·卢卡奇(György Lukács)和卡尔·柯尔施(Karl Korsch)侧重从“阶级意识”和“劳动”出发对《资本论》进行解读,期望恢复马克思主义中的历史辩证法。但由于缺乏对辩证唯物主义的理解,早期西方马克思主义者对《资本论》的解读逐渐走向人本主义。此后,西方学派尤其是法兰克福学派继承了早期西方马克思主义理论中的人本主义,从文化批判的角度解读《资本论》。这样的解读凸显了《资本论》文化批判功能,但也容易变为纯粹的道德说教。
在“重新发现”马克思主义的过程中,西方马克思主义十分注重对马克思原著的阅读。这一方面为研究《资本论》提供了新思路,另一方面也为怀有不良政治企图的人提供了可乘之机。20世纪30年代,随着《马克思恩格斯全集(历史考证版第1版)》的出版,西方学界掀起了重新解释马克思的浪潮。其中,《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的发表,对于重新认识《资本论》产生了重大影响,一些学者据此制造“两个马克思”对立说。随着《马克思恩格斯全集(历史考证版第2版)》的出版发行,西方学界出现了三卷本《资本论》从来都没有真实存在过的声音,认为由恩格斯整理出版的第2卷和第3卷改变了马克思的本意,主张按照马克思的原始手稿编辑《资本论》。这已经不是重新认识《资本论》了,而是要彻底消解《资本论》。
(四)企图“改造”“超越”《资本论》
在新科技革命推动下,资本主义社会发生了巨大变化,由此出现了一些《资本论》中没有论及的经济现象。以适应“新现象”为由,有的学者主张“改造”马克思主义,尤其是改造《资本论》的核心概念、主要理论、研究方法,甚至提出要“超越”《资本论》。[5]
第一,“重新界定”《资本论》中的概念术语。“剩余价值”就是《资本论》区别于古典政治经济学的核心概念。面对当前关于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争论,部分学者主张变换术语以减少争论。保罗·巴兰(Paul Baran)和保罗·斯威齐(Paul Sweezy)在《垄断资本》中尝试用“经济剩余”代替“剩余价值”,埃内斯特·曼德尔(Ernest Mandel)在《晚期资本主义》中尝试用“剩余利润”代替“超额剩余价值”。
第二,“改造”《资本论》中的主要理论。20世纪70年代以来,资产阶级经济学家对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展开了新一轮攻击。基于资本主义经济变化,许多学者以“边际生产率”“生产要素”“供求价值论”“服务经济”等“代替”或“改造”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价值向生产价格的“转形”问题是资产阶级学者攻击马克思劳动价值论的重要靶子。森岛通夫将《资本论》第2卷中的再生产公式理解为《资本论》的核心内容,并把它同第1卷中的劳动价值论对立起来。利润率趋向下降的规律也遭到了资产阶级经济学家的“重新改造”。资本有机构成的提高,是马克思论证利润率趋于下降规律的关键,但琼·罗宾逊(Joan Robinson)用(c+v):(c+v+m)置换c:v,歪曲了资本有机构成提高的原理。同时,罗伊·哈罗德(Roy Harrod)等人提出“中性的技术进步”概念反对马克思的利润率趋向下降规律。
第三,“重新解读”《资本论》的研究方法。有些学者为“颠覆”《资本论》,“重新解读”《资本论》的研究方法。克里斯多夫·阿瑟(Christopher Arthur)就是代表。阿瑟立足于“新辩证法”,对《资本论》中的辩证法进行修正,企图重新诠释价值形式、劳动价值理论和剩余价值理论。“新辩证法”所谓“新”是相对于苏联教科书体系中的“旧辩证法”和早期西方马克思主义的“历史辩证法”而言。阿瑟用黑格尔《逻辑学》中的“存在论”“本质论”“概念论”对应《资本论》中的“价值”“货币”“资本”,将三者的抽象运动看作辩证内容,建立体系辩证法。阿瑟认为,这样可以使《资本论》的叙述方式更具清晰次序、更加注重总体性。
二、马克思恩格斯批判误读《资本论》观点的主要维度
总结百余年来对《资本论》误读的历程,可以发现误读者中既有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反对者,也有其支持者;误读的对象在不同阶段有所不同,但是基本可以归结为“研究方法”“主要理论”“学术态度”三方面。马克思和恩格斯在世时就批判了这三方面误读,因而,以文本为依据,回溯马克思、恩格斯的批判,具有重要意义。
(一)对误读《资本论》方法的批判
马克思在《资本论》第1卷德文第二版跋中总结性地写道:“人们对《资本论》中应用的方法理解得很差”,[1](p.19)并列举了当时流行的各种关于方法的评论。这些评论中,马克思最为欣赏亨利·考夫曼(Henry Kaufman)的《卡尔·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批判的观点》一文,因为考夫曼较为正确论述了马克思的唯物辩证法,并且认识到研究方法和叙述方法的区别。但是,在对该问题的理解上,考夫曼还是有一定局限性,比如他割裂《资本论》研究方法和叙述方法的内在统一性,混淆了马克思辩证法和黑格尔辩证法的本质区别。马克思从三方面重点回应了考夫曼对《资本论》的误读。
第一,从研究方法和叙述方法的统一性角度出发批判了考夫曼对《资本论》叙述方法的曲解。考夫曼认为《资本论》的研究方法是“实在论”,叙述方法则是“德国辩证法”。为回应考夫曼的误读,马克思从工作内容和逻辑顺序上对两种方法做了区分。在工作内容上,研究工作就是“必须充分地占有材料,分析它的各种发展形式,探寻这些形式的内在联系”,[1](p.21)而叙述工作就是呈现出“一个先验的结构”,[1](p.22)即理论框架和体系。在逻辑顺序上,研究工作是叙述工作的基础,先于叙述工作。但是,马克思强调“在形式上,叙述方法必须与研究方法不同”,[1](p.21)也就意味着二者实质上具有内在联系,即:“研究工作和叙述工作都需要遵循辩证法的一般原则,二者在根本上是同一认识过程的不同方面而非割裂的两段过程。”[6]简单说来,研究方法和叙述方法是唯物辩证法在逻辑上的展开和历史上的表达。
第二,从唯物辩证法和唯心辩证法的根本区别出发批判考夫曼混淆了自己与黑格尔辩证法的区别。面对“《资本论》的叙述形式是德国辩证法”的指责,马克思没有急于同黑格尔辩证法划清界限,而是从“扬弃”角度分析了自己的叙述形式与黑格尔辩证法的关系。马克思公开承认自己是黑格尔的学生:“在关于价值理论的一章中,有些地方我甚至卖弄起黑格尔特有的表达方式。”[1](p.22)但马克思也强调:“我的辩证方法,从根本上来说,不仅和黑格尔的辩证方法不同而且和它截然相反。”[1](p.22)在黑格尔那里,概念、范畴等是绝对精神运动的产物,具有客观实在性。在马克思这里,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以及与它相适应的生产关系和交换关系才是研究对象。《资本论》的叙述虽然以范畴、概念呈现出来,但是这些范畴和概念是在充分占有资本主义社会有机体的各种材料的基础上,运用抽象法,通过去粗取精、去伪存真、由此及彼、由表及里得到的。
第三,从辩证法的合理性角度出发批判考夫曼对黑格尔辩证法的简单否定。在《资本论》第1卷德文第二版跋的最后部分,马克思对辩证法进行了经典阐述:“辩证法,在其合理形态上,引起资产阶级及其空论主义的代言人的恼怒和恐怖,因为辩证法在对现存事物的肯定的理解中同时包含对现存事物的否定的理解,即对现存事物的必然灭亡的理解;辩证法对每一种既成的形式都是从不断的运动中,因而也是从它的暂时性方面去理解;辩证法不崇拜任何东西,按其本质来说,它是批判的和革命的。”[1](p.22)正因为马克思发现了黑格尔辩证法的合理内核即“内在否定性”,才能用“资本内在的否定性”解剖和分析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及其生产关系和交换关系,才能把握和表达资本主义社会人类的生存状况,才能揭露和拆穿资本主义永恒性的谎言。由此,马克思在《资本论》序言中将唯物辩证法比作“柏修斯的隐身帽”——不同于资产阶级经济学家借用“隐身帽”紧紧遮住眼睛和耳朵来否定妖怪的存在,马克思要用“隐身帽”杀死美杜莎。
(二)对误读劳动价值论和剩余价值论的批判
劳动价值论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核心论题之一,也是发现剩余价值规律的重要基础。瓦格纳在《政治经济学教科书》中误读了并大肆攻击马克思的劳动价值理论。为此,马克思撰写了《评阿·瓦格纳的〈政治经济学教科书〉》,对瓦格纳进行了回击。
一是批判瓦格纳采用唯心主义态度对待基本经济问题。瓦格纳研究经济问题的核心概念是“价值一般”,认为“‘价值’这个普通的概念是从人们对待满足他们需要的外界物的关系中产生的”,[7](p.406)而人们的需要则是“受理智和良心的指导”。[7](p.396)瓦格纳坚持的是唯心史观,这也决定了他对待基本经济问题的态度也是唯心主义的。瓦格纳在《政治经济学教科书》中玩弄语言游戏,从“使用价值”一词中拆分出具有“价值一般”含义的“价值”,再宣称“使用价值”是“价值”的重要内容,决定着商品的交换价值,然后把原先省略掉的“使用”一词重新放在“价值”前面,这样就得到了“使用价值”。瓦格纳通过概念的同义反复论证自己的经济学理论,目的是说明价值和劳动无关,掩盖资本家剥削工人剩余劳动的真相。
二是指出瓦格纳对《资本论》观点的错误理解。瓦格纳认为马克思将商品划分为使用价值和交换价值,然后发现交换价值中存在着共同的社会实体(工人的劳动),最后将交换价值置换为价值一般。在瓦格纳看来,马克思的价值理论的错误之处在于“过于片面地注意仅仅一个决定价值的因素……费用,而没有注意另一个因素,即有用性、效用、需要因素”。[7](p.402)基于以上分析,瓦格纳认为马克思的价值理论来自李嘉图的费用理论。面对误读,马克思加以回击,指出交换价值既不是价值一般,也不是商品价格;交换价值只是价值形式,不是价值本身。马克思清楚表述了商品价格很少与价值相一致,因为它除了受价值因素影响外,还受其他因素影响。马克思强调自己的研究对象不是价值,而是商品。使用价值和价值统一于商品,不能离开商品抽象谈论价值概念。马克思也指出他的理论与李嘉图的费用理论具有本质区别,“李嘉图实际上把劳动只是当做价值量的尺度来考察,因而他看不到自己的价值理论和货币的本质之间的任何联系”,[7](p.400)所以李嘉图并不会像马克思那样,对价值本身进行历史性和实证性研究。
当《资本论》第1卷出版后,洛贝尔图斯妄称马克思剽窃了他在《关于我国国家经济状况的认识》中的观点。之后,他在书信中进一步明确指出,马克思剽窃的部分就是剩余价值理论,因为剩余价值的产生问题最初在他的《第三封社会问题书简》中进行了更简单明了的说明。马克思逝世后,资产阶级庸俗经济学家将此种谣言当作事实大肆宣扬。为维护马克思的声誉,恩格斯在《哲学的贫困》德文第一版序言中对洛贝尔图斯进行了批判。之后,在《资本论》第2卷序言中,针对马克思剽窃洛贝尔图斯的剩余价值论这一诽谤,恩格斯“提出有决定意义的证据”[8](p.10)加以批驳。
一是从经济思想史角度论证了洛贝尔图斯并不是剩余价值学说的首创者。洛贝尔图斯自诩为剩余价值理论的首创者,然而,在经济思想史上,洛贝尔图斯之前许多经济学家都注意到了剩余价值问题。洛贝尔图斯以将剩余价值的产生归为“租”为傲,但其实此观点在李嘉图等人中早有涉及。然而,马克思逝世后,洛贝尔图斯的追随者“竟把那些在亚·斯密和李嘉图那里就可以读到的东西,煞有介事地硬说是马克思从洛贝尔图斯那里窃取来的”,[8](p.19)这一事实暴露了这些经济学家惊人的无知。
二是从经济思想史角度出发论证了马克思的剩余价值论并非抄袭自洛贝尔图斯。恩格斯从马克思创立剩余价值论的时间线出发,驳斥了洛贝尔图斯及其追随者对马克思“剽窃”诬陷,明确指出,马克思是在1859年前后才知道洛贝尔图斯的三本小册子的,而在此之前,马克思对洛贝尔图斯的著作一无所知。在《哲学的贫困》和《雇佣劳动和资本》中,马克思就已经熟悉和掌握了剩余价值学说和劳动价值学说。马克思对于洛贝尔图斯的一般剩余价值理论的态度,可以从《政治经济学批判(1861—1863年手稿)》中《剩余价值理论》部分的一处笔记看出。马克思写道:“洛贝尔图斯先生首先研究在土地占有和资本占有还没有分离的国家中什么情况,并且在这里得出重要的结论说:租(他所谓租,是指全部剩余价值)只等于无酬劳动,或无酬劳动借以表现的产品量。”[8](p.13)可见,洛贝尔图斯的“租”是极不确定的,与马克思的剩余价值论有本质区别。
三是从剩余价值学说发展史角度论证了马克思对剩余价值论的独特贡献。为说明马克思在剩余价值学说发展史上的贡献,恩格斯用化学史上氧气的认识过程加以类比说明。对于氧气的认识,经历了“传统燃素说—普利斯特和舍勒析出氧气—拉瓦锡发现氧气”这一过程。对于剩余价值论的认识,经历了“重商主义者的‘剩余价值产生于产品价值的加价’—古典经济学家和庸俗经济学家对剩余价值具体形式的研究—马克思通过对剩余价值的一般研究发现资本主义生产的秘密”这一过程。与拉瓦锡一样,马克思与前人的最主要区别是“在前人认为已有答案的地方,他却认为只是问题所在”。[8](p.21)因此,马克思根据剩余价值研究了全部既有经济范畴。基于此,马克思首次阐明了李嘉图学派的难题,成为第一个阐明剩余价值实际形成过程,建立详尽货币理论和合理工资理论的经济学家。
(三)对《资本论》第1卷和第3卷内在关系误读的批判
洛里亚对马克思的主要攻击是:以《资本论》续卷欺骗读者;剩余价值理论与现实中的利润率平均化相矛盾;用生产价格规律“否定”价值规律。对此,恩格斯一一进行了驳斥。
一是通过整理发表《资本论》第2卷和第3卷以事实来反驳洛里亚“马克思经常拿《资本论》续卷来威胁读者”的观点。按照方法论要求,马克思在《资本论》第1卷中没有论及利润率平均化同价值规律之间的内在统一性,而是将之放到第3卷中讨论。洛里亚等人言之凿凿地宣称:“马克思甚至没有闪过写这个续卷的念头”“这第二卷很可能是马克思在拿不出科学论据时使用的一种诡计。”[9](pp.21-22)1885年和1894年,恩格斯整理和出版了《资本论》第2卷和第3卷,用铁的事实击溃了洛里亚对马克思的诽谤。面对这一事实,洛里亚仍认为:“马克思在发表他的光辉著作以后就没有打算写什么续卷。说不定,他原来就是想把他的巨著交给他的继承人去完成,而自己不担负什么责任。”[10]言外之意即《资本论》续卷乃恩格斯伪造。针对洛里亚的发难,恩格斯进一步阐明了《资本论》第1卷和第3卷的内在联系:第3卷论述的资本主义生产总过程中的剩余价值实现问题是对第1卷论述的剩余价值生产问题的补充和完成。
二是批判洛里亚对价值理论同利润率平均化现实相矛盾的责难。在《资本论》第1卷出版后,洛里亚断言价值理论同利润普遍相等这个事实不可能同时成立。但当面对《资本论》第3卷中解决了价值规律和利润率问题后,洛里亚以商业利润为支点错误地认为,凭借“非生产资本”的魔力“转瞬之间就把那个他在10年前宣告为不能解决的问题解决了”。[9](p.23)《资本论》第3卷序言指出了洛里亚的“非生产资本”的主要理论错误。首先,洛里亚“这种‘非生产资本’究竟从何处得到权力,使它不仅可以从工业家手里抢走他们的超过平均利润率的这个额外利润,而且还把这个额外利润作为地租塞进自己的腰包”。[9](p.23)其次,洛里亚根本不清楚自己所说的“非产业资本”与产业资本间的关系,“非生产资本”只不过是他混不下去时玩弄的“可怜的把戏”。
三是以逻辑与历史相统一的方法驳斥洛里亚对《资本论》生产价格规律同价值规律相矛盾的指责。1895年,洛里亚继续发表《卡尔·马克思的遗著》一文,歪曲《资本论》第3卷存在生产价格规律同价值规律相矛盾的问题,称其为“重大的理论上的破产”。恩格斯在《资本论》第3卷增补的《价值规律和利润率》中批判了洛里亚眼中的“价值”。洛里亚认为,“价值不外是一个商品同另一个商品相交换的比例”,[9](p.1007)他将价值等同于价格,从而将价值视为纯粹由供求关系决定的现象。按照这一理解,如果把两个商品交到一个没有供求关系的第三者手中,就可以得出价值可能是“零”这一荒唐结论。恩格斯运用逻辑与历史相统一的方法,结合资本主义的发展历史,说明了通过利润平均化过程实现价值规律向生产价格规律的转化。在简单商品生产时期,支配商品生产的规律还是马克思所说的价值规律。到了资本主义机器大工业生产时期,随着机器的大量使用,就会出现资本有机构成较高的部门的利润率低于资本有机构成较低的部门的现象。但是,“这种高有机构成部门的存在和发展是社会生产发展的需要,这就决定这时的商品就不能再按照价值出售”,[11]也就需要价值规律向生产价格规律转化。
(四)对诋毁马克思学术态度的批判
1872年,柏林《协和》杂志匿名发表了《卡尔·马克思是怎样引证的》一文,指责马克思在《资本论》第1卷论述“资本主义积累的一般规律”使用的例证中随意“增添”了一句话,即“财富和实力这种令人陶醉的增长……完全限于有产阶级”。[1](p.38)之后,布伦坦诺及其追随者围绕这条引文对马克思展开了20余年的学术指控。
在认清了布伦坦诺等人企图以《资本论》一处引文的错误来诋毁马克思经济学的科学性的真实目的后,恩格斯在1890年以铁的事实驳斥“马克思引文捏造论”,使“任何人也不敢再怀疑马克思写作上的认真态度了”。[1](p.44)
第一,恩格斯认真核对马克思的著作和当时新闻报道,证明马克思在形式和实质上都既没有“增添”,也没有“删掉”引文作者的讲话。首先,针对布伦坦诺指责马克思随意“增添”引文的指责。恩格斯除援引马克思之前列举的报纸外,还继续列举了像《每日电讯》《先驱晨报》《晨邮报》《每日新闻》《旗帜报》的报道。这些报道不是转述了马克思所“增添”的这句话,就是“以在形式上比较扼要”的说法转述了它。其次,针对布伦坦诺转头指责马克思为使《泰晤士报》的意思与《汉萨德》的相反,故意删掉了《泰晤士报》中的“亦即其数据以我认为十分确切的材料为根据的增长”这个附句。[1](p.38)布伦坦诺认为这个附句至关重要,说明了引文作者所说的财富增长限于有产阶级的原因是工人阶级免缴所得税。恩格斯从《资本论》中摘录了被布伦坦诺指责删掉的地方:“从1842年到1852年,国内应纳税的收入增加了6%……在从1853年到1861年的8年内,如……则增加了……”[1](p.751)这证明了马克思没有删去这个附句。
第二,在《资本论》第1卷的三篇序言中,恩格斯阐述了马克思的引证方法和引证意义,表明其具有严谨性和科学性。《资本论》中的引证方法并不为人所了解,但确实很独特。恩格斯在第三版序言和英文版序言中介绍了这一方法。在单纯叙述和描写事实的地方,引文只是简单的例证,比如对英国蓝皮书的引用;大多数情况下,引用其他经济学家的理论观点,只是为了确定一种经济理论“是什么地方、什么时候、什么人第一次明确地提出的”,[1](p.30)从时间和首倡者两个角度说明其在经济史上的较为重要的成就。马克思和布伦坦诺争论的焦点在于“引用官员的讲话是以官方事后公布的定稿为标准,还是以演讲人现场发表的讲话为依据?”[12]马克思本着从第一手资料入手的原则,坚持以演讲人现场发表的讲话作为依据。之后,恩格斯在第四版序言中谈到在校对《资本论》引文的过程中,只发现一处引文可能由于马克思写错书名没有找到出处。可见,马克思在引证时非常严谨,《资本论》的引文有充分的说服力。事实上,布伦坦诺之所以像水蛭一样紧紧吸住这唯一的一条引文不放,恰恰证明了“他们非常清楚地知道‘卡尔·马克思是怎样引证的’”。[13](p.154)
(五)对为《资本论》辩护过程中出现的误读的批判
面对资产阶级学者和讲坛社会主义者对《资本论》误读、歪曲甚至诋毁,也有一些马克思、恩格斯的朋友和支持者予以回击。但在回击过程中,他们由于未真正理解《资本论》或受对方观点影响,也对《资本论》产生了一定程度的误读。
在《资本论》第3卷序言中,恩格斯专门总结和评价了当时关于价值转化为生产价格的“转形”问题解决方案。德国社会民主党人康拉德·施米特(Conrad Schmidt)是第一个试图解决这一问题的人,《在马克思的价值规律基础上的平均利润率》一文中,他试图从“市场价格的细节”出发,证明价值规律与平均利润率现象并不矛盾。施米特将总产品分为“预付资本的补偿物”和“剩余产品”两部分,其中“预付资本的补偿物”部分的价值和价格是相同的,“剩余产品”的出售价格是证明“转形”问题的关键。他将剩余产品的出售价格定义为一般利润率和资本总量的乘积,认为这样就使价值和生产价格相等了。恩格斯对此评价道:“施米特在问题已经临近解决的时候走上了这条岔路,因为他认为,他无论如何必须找到一个数学公式,来证明每一单个商品的平均价格是符合价值规律的。”[9](p.16)这样并没有捍卫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理论,反而在事实上曲解和抛弃了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在利用《资本论》前两卷的结论来解决“转形”问题时,乔治·斯蒂贝林(George Stiebeling)捏造了一个所谓的“固定的利润率”理论,并认为该理论应该根据实践进行修正。恩格斯在肯定斯蒂贝林用意的同时指出:“一个人如果想研究科学问题,首先要学会按照作者写作的原样去阅读自己要加以利用的著作,并且首先不要读出原著中没有的东西。”[9](p.26)
1884年,保尔·拉法格(Paul Lafargue)为一篇批驳文章寻求恩格斯的建议。在给拉法格的信中,恩格斯指出了其中存在的主要错误,比如“利润是活劳动的合法产儿”,这一表述并非捍卫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反而是对庸俗经济学的附和。因此,恩格斯最后建议拉法格“从头至尾精心重读《资本论》,把所有谈到庸俗经济学的地方都标出来”。[14](p.199)
三、马克思恩格斯批判各种误读《资本论》观点所体现的智慧
时至今日,部分攻击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人还在重复着那些马克思、恩格斯早已批判过的陈词滥调。正因如此,系统研究马克思主义创始人对各种误读《资本论》观点的批判,具有重要现实意义。
(一)以文本为依据、以说理为基础反驳对《资本论》的重大误读
通过批判对《资本论》方法的误读,马克思、恩格斯阐明、澄清了唯物辩证法。对于《资本论》方法的认识和争论,直接关乎对《资本论》研究目的、研究对象、概念体系和马克思本人学术立场的理解。《资本论》的方法是什么?马克思辩证法和黑格尔辩证法是什么关系?马克思在《资本论》第1卷第二版跋中已经给出了答案。我们应该按照马克思的精神实质回答当前关于《资本论》方法的争论,正确认识根本方法与具体方法的关系,正确认识马克思的《资本论》与黑格尔的辩证法的关系。
通过对误读《资本论》主要理论的批判,马克思、恩格斯捍卫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基石。通过批判对劳动价值理论的误读,马克思反驳了把商品的价值与交换价值、使用价值相等同的论调,阐明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基本范畴。通过批判对剩余价值理论的误读,恩格斯驳斥了荒谬的“马克思剽窃论”,捍卫了马克思剩余价值论的原初性和创新性。通过批判对《资本论》第3卷的生产价格理论“否定”《资本论》第1卷的价值理论的误读,恩格斯指明了马克思的反对者对资本主义商品经济实际过程的无知,并从逻辑与历史相统一角度论述了价值转化为生产价格的必然性。
通过批判捏造《资本论》的引文错误,马克思、恩格斯揭露了学术性指控的实质是政治阴谋。虽然这场指控在恩格斯的批判中结束了,但针对恩格斯“篡改”《资本论》的学术指控从未消失,对此,我们除应从学术角度用铁的事实予以反驳以外,还应从政治角度揭露这场学术指控的虚伪性。
(二)在反驳误读过程中树立科学的批判态度
马克思、恩格斯对各种误读《资本论》观点的批判,目的不是证明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权威性,而是捍卫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科学性。
“理论批判的科学性首先在于理论本身的科学性。”[15](p.102)马克思逝世后,面对讲坛社会主义者对劳动价值论的肆意诋毁,恩格斯在予以回击的同时,也对劳动价值论进行了补充完善。值得注意的是,在对洛里亚进行批判时,恩格斯既没有认为马克思的理论臻于完美,也没有认为反对者的理论一无是处。恩格斯认为,马克思在《资本论》第3卷第10章对价值转化为生产价格的历史的和逻辑的论述,只做了一个“大概轮廓”的说明,“如果马克思来得及把这个第三册再整理一遍,他毫无疑问会把这段话大大加以发挥”。[9](p.1015)作为《资本论》第3卷的整理者,恩格斯对“转形”问题有着深入研究,因此自然承担起了“较为详细地谈谈”的任务。基于《1861—1863年经济学手稿》、与马克思关于“转形”问题的通信、《资本论》第3卷手稿等文本,并结合1865年到1895年间资本主义的发展变化,恩格斯写作了《价值规律和利润率》这一“增补”,对“转形”问题做出个别较为重要的补充。
同时,恩格斯在批判对手前也会认真阅读对手的著作。即使面对洛贝尔图斯,恩格斯也尽可能发现他理论中的可取之处。1884年,恩格斯审阅考茨基的《洛贝尔图斯的〈资本〉》一文后,在致考茨基的信中写道,《关于我国国家经济状况的认识》“确实是他写的所有著作中最好的一本……我很高兴把它来看了一遍”。[14](pp.190-191)拉法格想要写一篇批判反对者的书籍的文章而寻求恩格斯帮助时,恩格斯并没有立即给出建议,而是回信写道:“我必须有那本书,要弄到那本书,我必须知道准确的书名。请立即把书名告诉我,以便去订购。”[14](p.185)充分占有材料是批判的前提,也是严谨求实学风的内在要求。可见,恩格斯是尽可能寻找对手的合理之处,不断丰富和完善自己的理论。此外,恩格斯晚年在面对将马克思主义“教条化”和“绝对化”的理论倾向时,有时也从自身的不足展开反思:“青年们有时过分看重经济方面,这有一部分是马克思和我应当负责的。我们在反驳我们的论敌时,常常不得不强调被他们否认的主要原则,并且不是始终都有时间、地点和机会来给其他参与相互作用的因素以应有的重视。”[16](p.606)
(三)在科学研究中养成良好的学术学风
很多人对《资本论》有诸多误读,很大原因在于没有读过或者没有读懂。对此,习近平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中明确指出:“这是一种不负责任的态度,也有悖于科学精神。”[17](p.12)
第一,原原本本精心研读原著。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都十分重视阅读原著。有时遇到学者还没有阅读或理解就胡乱批评,马克思感叹:“咳,这些人哪怕是能读懂也好啊!”[16](p.619)列宁在《卡尔·马克思》中按照时间顺序罗列了马克思和恩格斯的38部著作,按照对待马克思主义的三种态度整理了评述马克思主义的相关文献。针对有人觉得马克思主义著作高深晦涩从而心生畏惧,列宁说:“第一次阅读时不明白的地方,下次再读的时候,或者以后从另一方面来研究这个问题的时候,就会明白的。”[18](p.24)
第二,结合历史语境与整体内涵解读原著。当前造成误读马克思主义的原因之一,就是脱离特定历史语境,把一些原理当作马克思理论的全部。有时原理只是抽象结论,如果只知其然不知其所以然,就容易产生误读。比如“我不是马克思主义者”这句话,如果不结合历史语境,就会将其误读为“马克思反对马克思主义”。但马克思和恩格斯之所以排斥“马克思主义”一词,是因为论敌加以歪曲,产生了误读。只有回到原著,了解时代背景和历史条件,才能从整体上把握马克思主义理论,才有可能避免相对主义和主观主义。
第三,科学把握现实问题与原著之间的关系。毛泽东非常重视读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但他强调“精通的目的全在于运用”。[19](p.815)这就要求我们要带着问题去读原著,以便思考问题“是如何理解的,是如何加以解决的,哪些已经得到解决,哪些尚未解决”。[20]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就是这样去阅读和研究前人著作的。正因如此,才形成了“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发展史”,而不是“马克思理论发展史”。当前,如何运用《资本论》指导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完善是重大问题。有人认为,《资本论》研究对象是过去的资本主义经济及其运动规律,与当代经济无关;有人认为《资本论》是关于人的解放科学方法的著作,只为研究当代经济提供了方法和目标;还有人将《资本论》“绝对化”,将个别论点当作绝对真理。这都是在运用《资本论》层面产生的误读。科学的做法应是正确认识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与马克思创作《资本论》时的历史条件所具有的共性和区别,共性的地方对于当前经济建设具有直接指导作用,区别的地方则要在坚持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原理的前提下,根据实践来创新。
参考文献略
(本文原载《毛泽东邓小平理论研究》2023年第7期,授权红色文化网发布)

微信扫一扫|长按识别,进入读者交流群
|
|
|
|
|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