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革新:警惕中日文化交流中的私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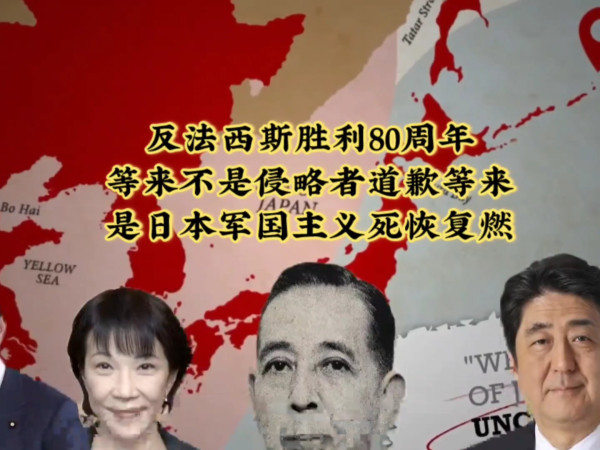
某社会科学期刊曾发表一篇题为《论坂井洋史的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的奇文,在对日本学者坂井洋史的《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的诠释、跟进、推介中,与坂井洋史一唱一和,抹黑中国的“‘现在’合法化”政权,叫嚣要“剔抉”“排斥”“20世纪中国文学”“‘现代性暴力’对人的精神伤害”,并要以此来“建立与暴力性坚定抗衡的文学史研究主体,进而奠定中日知识分子对话基础,促进中日文化与文学交流与对话”。从该文主要政治倾向来看,就是中日“公知”沆瀣一气,打着“文化交流”的幌子,追捧和“接轨”日本右翼文化,煽动知识分子对抗和颠覆中国的“‘现在’合法化”政权和中国共产党的主流意识形态,必须予以批判。
坂井洋史,日本东京人氏,1959年生。学术博士。日本一桥大学大学院言语社会研究科教授,并担任中国“巴金研究会”研究员、上海大学文学院文化研究系校外委员。有《忏悔与越界——中国现代文学史研究》、《脱轨与启示——中国现代作家研究》、《巴金的世界》、《现代困境中的文学语言和文化形式》等多部著作出版。有网文称他“从研究安那其主义(即无政府主义)为出发点……,贯通二十世纪中国文学,给了他一种澄明而透彻的穿透力……”等等。
以前,笔者对这位东洋学者知之为零,对其著作也未曾涉猎;至于该文的作者,也是仅从“作者简介”中,知其为文学博士、文学院讲师。从他这篇文章来看,其文艺倾向,与笔者过去多次批判过的该刊某些“小书生”的文章,如《“红色文艺”的困境》、《知识分子立场和现代性承担》等等如出一辙。所不同的是,该文无论是引用坂井洋史文本的原话,还是对坂井洋史观点的跟进、复述、吹捧,完全“虚无”日本侵略者在我国犯下的滔天罪行,强力推行日本“公知”粗暴干涉中国文化自主,煽动中国知识分子反共、反政府、反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对此,笔者摘录其中能代表他们基本政治倾向的若干观点、语句,予以剖析、研判,掀开其“语言面纱”的遮盖,看看里面包藏的是什么货色、祸心!
一、所谓“警惕”“现代性暴力”和“剔抉”“排斥机制与现代性暗部”,矛头直指中国无产阶级专政的“现政权”
作为对“巴金研究会”一位日本研究员的研究,该文在其“内容提要”和第一章,都谈到“坂井洋史从巴金研究入手,以‘安那其主义’为出发点,贯通20世纪中国文学,警惕‘现代性暴力’对人的精神伤害”一类词语,所表达的核心思想就是由于国家“‘权力’暴力性使然”,巴金只能从“感情深处”“认同”“‘权力’暴力排斥机制”,是巴金的“思维模式”所“遵循的‘现代性’”,造成了“巴金缺席文学史”的政治原因。实质就是他们容不得巴金晚年之前,由信仰无政府主义,转变、成长为信仰共产主义的无产阶级革命作家;容不得他对日本侵略军对中国人民残酷杀戮的刻骨仇恨;容不得他那颗“向着祖国的心”和对新中国欣欣向荣的欢欣鼓舞;容不得他“爱真理、爱正义、爱祖国、爱人民、爱生活、爱人间美好的事物”的人文情怀!……
该文第一章《文学史排斥机制与现代性暗部的剔抉》写道:“1990年代以后”“中国社会向大众化转型,知识分子被迫从中心退守到边缘,他们的言论被埋没在众声喧哗中”,原因就是“‘权力’暴力性使然”。这里所谓的“‘权力’暴力性”,就是他们恨之入骨、务必要“剔抉”掉的中国“现代性暗部”,即中国无产阶级专政的社会主义人民政权、中国共产党的主流意识形态,特别是抗日战争以来,中国人民激发出来的伟大爱国主义精神!
查阅有关资料得知,该文以上提到的“1990年代以后……”,是指当年国内部分知识分子,面对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期的一次“人文精神大讨论”,内容包括“对马克思主义人道主义的反驳并试图寻求超越的努力”,指责中国当代文人“精神状态普遍不良,人格萎缩,趣味粗劣,想象力匮乏和思想、学术的失语”之“各种因素合力造成的”和“文化人自身原因”造成的“精神伤害”等等。该文在这里不过是“借题发挥”“移花接木”,即借这次(从内容上看)并无积极意义的“大讨论”的话茬,与坂井洋史“中国文学史研究”“接轨”,贩卖坂井洋史中国文学研究的私货罢了。
为达到“剔抉”新中国“‘权力’暴力性”和“现代性暗部”,中日两“公知”先是拿我国高等教育文学史教材开刀。《刘文》引用坂井洋史的原话说:“1949年后……被纳入高等教育正规课程的中国现代文学史,为了适应强化国家体制的意识形态要求而将‘现在’合法化,及时地发挥排斥机制,将有损于政权合法性和书写秩序的异端因素通通排斥掉,成为中国革命史的有机组成部分和为国家服务的意识形态机器”,之后,该文紧接着就以十分肯定的语气说:“坂井洋史的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中,对现代性暴力的警惕一直是自觉的追求”,并对他攻击我国政府的谬论大加吹捧,说:他(坂井洋史)认为“剔抉出作为‘排斥’的结果而被遮蔽的诸多因素,把它们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就是文化批评的主要任务之一,也是文学研究和文学史研究的主要目标”!
一个曾经疯狂地侵略中国、抱着在中国建立“大东亚共荣圈”的狼子野心、给中国人民造成巨大灾难的国家的文化学者,不但要“剔抉”和“排斥”新中国高等教育教材里的“中国革命史的有机组成部分和为国家服务的意识形态机器”,而且还要“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这种粗暴干涉我国文化教育事业的文字,活脱一副文化侵略者、法西斯主义嘴脸。联系近年来,国人大量揭露的我国中小学课本里“鬼子学雷锋”、武士道的“岳母刺字”插图等问题,有理由认为,被该文推介的坂井洋史对中国高等教育教材的“剔抉”和“排斥”,是一种法西斯主义文化渗透。令人奇怪的是,作为中国的“文学博士”南通“大学文学院讲师”的该文作者,对此不但不加以抵制、批判,反而对人家要把新中国“高等教育正规课程”中“适应强化国家体制的意识形态要求”“剔抉”掉的主张大加“追捧”,这不就是打着“文化交流”的幌子,“接轨”外国文人在“高等教育正规课程”中对中国“‘现在’合法性”的我国国家政权的颠覆吗?
这里不禁要问:中国人民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经过百年来艰苦卓绝的革命斗争,其中包括14年的抗日战争,把日本帝国主义赶回了东洋老家;用3年时间,推翻了美帝国主义武装的蒋家王朝,建立了新中国,在这种情况下,我们“为了适应强化国家体制的意识形态要求”,发挥必要“排斥机制”,把“高等教育课程的中国文学史”教材中“有损于政权合法性”的“异端因素通通排斥”掉,使这些教材“成为中国革命史的有机组成部分和为国家服务的意识形态机器”,这有一丝一毫的“不合法”吗?该文作者作为中国文化学者,却附和着日本右翼文人的腔调,要把我们“适应强化国家体制”的“‘现在’合法性”“剔抉”掉,“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并以此作为“文化批评的主要任务”和“文学研究和文学史研究的主要目标”,这不就是要把1949年建立起来的人民共和国这个“‘现在’“合法性”的“国家体制”“剔抉”“排斥”掉吗?
“什么人站在革命人民方面,他就是革命派,什么人站在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方面,他就是反革命派。”(1)日本洋人和该文作者,如此丧心病狂地要“剔抉”中国高等教育教材中“国家体制的意识形态要求”,又是站在了什么立场上?其反革命派的嘴脸,不是非常清楚吗?
二、煽动中国知识分子“警惕”“现代性暴力”、对抗思想改造,要他们“从主流、集体的意识形态中解放出来”
该文在第二章,推介坂井洋史的《忏悔与越界:知识分子精神史勾画》的文章中,肉麻地吹捧坂井洋史“对现代性暴力如此警惕,时时提防暴力对人的精神的伤害,目的是揭示20世纪中国在向‘现代’转变过程中,现代性暴力对知识分子思想的潜在控制,进而阻碍知识分子认识当下中国转型”的胡言乱语。
他们极力攻击所谓“现代性暴力”和“现代性暴力对知识分子思想的潜在控制”,就是攻击我人民民主专政的国家政权,反对我们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爱国主义民族精神,对自己国家的知识分子,进行思想政治教育。他们对我国政治思想教育,横加干涉、评头品足、指手画脚,明明是打着“文化交流”的幌子,推行文化霸凌主义,企图用他们的“暴力”对中国知识分子进行“控制”,却反咬一口、倒打一耙,把“控制”知识分子的帽子扣在中国政府的头上。
怎样“提防”“现代性暴力”对中国知识分子的“精神的伤害”,和怎样防止“现代性暴力对中国知识分子思想潜在控制,进而阻碍知识分子认识当下中国转型”呢?
一是把中国知识分子接受共产党的教育,提高政治思想觉悟,服从国家领导,服务于国家、服务于人民,污蔑为向国家、即他们所说的“现代性暴力”的“忏悔与越界”。在他们看来,只有消除中国知识分子对国家的这种“‘忏悔’和‘越界’”,才能使他们摆脱“现代性暴力对知识分子思想的潜在控制”——这就是公开反对中国知识分子学习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和党的方针政策,反对知识分子在思想改造的“强烈纠葛”中,实现“自我”与国家、民族、人民相融合,即他们所说的向“现代性暴力”即国家的“忏悔与反省”。据说这样的“忏悔与反省”,与“中国现代文学史的现代性暴力有莫大的关系”!这种“莫大的关系”,就是他们十分害怕的中国知识分子接受“民族精神的塑造”、“激发爱国热情”!这就是他们极力反对知识分子思想改造,反对“忏悔”和“越界”的险恶用心!(请注意他们的重要要用语:“民族精神的塑造”、“激发爱国热情和民族主义”、“为祖国而工作”等等)
二是推崇崔健的摇滚音乐,吹捧崔健“扮演了一个神一样的启蒙者角色。他所有的努力便是将一群人从主流、集体的意识形态中解放出来”;然而,他们马上又以十分惋惜、十分不满足地口气责备说:“更值得警惕的是,中国知识分子对崔健摇滚的解读,忘了抵抗的终极是对自己的否定”!把这话说白了,就是他们认为崔健的摇滚演唱,虽然受到“一群人”的狂热追捧,使“一群人”“从主流、集体的意识形态中解放出来”,但这还是不够!“更值得警惕的”是中国知识分子不能“忘了抵抗的终极目的”,是在于防止“对自己的否定”,尤其是不能忘记思想改造的“现代性暴力,使知识分子“忏悔与越界”所带来的“精神的伤害”!这是明目张胆地煽动知识分子抵制思想改造,对抗人民民主专政的社会主义国家制度。
三是污蔑我国知识分子接受思想改造,是在“安稳中偷生”和“精神侏儒化”。该文特别推崇坂井洋史所谓“把人虚构的制度(国家等)放在‘人’之上,这种思维模式带来的恶果是知识分子在内心深处认同个体屈服于外在的权威,这不但为知识分子的悲剧性命运埋下伏笔,更使其接受只有外在权威才能给个体带来价值的潜在观念,否定了个体努力的意义,以至于知识分子在依附权威的安稳中偷生,导致知识分子精神的侏儒化,并反过来限制了知识分子对今天纷繁缭乱的文化和社会现象面前深层次思考的能力”!
这里,需要认真“翻译”一下:这位日本右翼学者和该文的作者,首先是把知识分子改造思想,叫做“个体屈服于外在权威”,会使“外在权威”给“个体”带来“价值的潜在观念”;其次是把人民当家作主的新中国,叫做“人虚构的制度(国家等)”,而中国知识分子与这个“人虚构的制度”“共享”,就会使知识分子“失去”“自我”;其三是他们把我国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意识形态,叫做“纷繁缭乱的文化和社会现象”,会使知识分子“在依附权威的安稳中偷生,导致知识分子精神的侏儒化”,也就限制了他们对于今天的中国的“深层次思考的能力”!归根结底、总而言之、要而言之,他们就是反对中国知识分子改造思想,就是鼓励、煽动知识分子反共、反国家、反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其险恶用心可见一斑。
“人民大众开心之日,就是反革命分子难受之时。”(2)以笔者之见,无论是“内鬼”还是“外鬼”,他们都容不得中国人民的胜利,尤其对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的伟大胜利、对推翻国民党反动派的统治,建立人民当家作主新中国,他们始终抱着一种仇恨心理。作为日本右翼文人,有这样思想意识,发表这样的文章、议论,本不值得大惊小怪,问题在于,作为中国知识分子,又是大学文学院讲师的该文作者,何以会把屁股坐到坂井洋史一边去,与洋人唱着同样仇恨中国政府、污蔑中国文化的腔调,引偏中国知识分子做人、为文的方向呢?
按照常理,中国知识分子在共产党领导下,在取得了伟大胜利的自己的国家、本土,把“自我”的“内部自然”,与建设社会主义祖国的“外部自然”“共享”“融合”和“同化”,塑造“民族精神”、“激发爱国热情和民族主义”,坚持文艺“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的方向,这,何罪之有?广大知识分子与人民群众融合,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实现“建立现代民族国家”的“现代性最重要的目标”,怎么就成了“在依附权威的安稳中偷生、导致知识分子精神的侏儒化”、“丧失了自我”呢?
值得一提的是,坂井洋史和该文这些“鬼画符”语言,与笔者多次批判的国内“公知”、某些“小书生”的所谓“知识分子既不能屈服权威,也不能皈依民间”,而要他们“离开庙堂和民间”“独立地站着”,用知识分子的“话语立场”去抵抗“权威话语”(3)的论调,与他们多年来攻击广大文艺工作者坚持“文艺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的创作方向,是什么“为逃避政治压力,而做的“文学之化装”、“心是口非”,是什么“对独特时代历史政治”的“趋附”、“狭隘”、“迎合”、“粉饰”’、“靠近”(4)等要知识分子“转变立场”的论调,不是如出一辙吗?特别是在党的十八大以后,还发表多篇此类虚无主义文章,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
三、构建与“权力暴力”相抗衡的文学史研究的“主体队伍”,以防止知识分子被“意识形态化”
该文在第三章《构建抗衡现代暴力性文学史叙述与研究主体》中,“提醒”中国知识分子说:尽管坂井洋史对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中,要“剔抉”的“着力点”看似很多,但必须“抓住”坂井洋史最为关注的“中国、亚洲现代化是怎样的过程以及对人们影响的这些大问题,也只有在抓住这些大问题的基础上,敏锐地意识到无处不在的‘权力’之暴力性并坚决与之抗衡的研究‘主体’才能建立起来。”
什么叫做“抓住”中国和亚洲的“大问题”?建立什么样的“抗衡”“‘权力’之暴力性”的研究“主体”呢?就是要中国知识分子与日本右翼文人勾结起来,对抗中国人民民主专政的社会主义国家政权,与被他们污蔑为“权力暴力性”进行“坚定抗衡的文学史叙述”,——这,不但是中国的,而且是“中国和亚洲的‘大问题’”!在中外文化学者图谋建立与中国“‘权力’之暴力”相“抗衡”的研究“主体”中,突然又拉上了“亚洲”,其意义可能更加深远,这会不会让人想到当年那个“大东亚共荣圈”的军国主义美梦呢?
对于怎样建立“抗衡”“‘权力’之暴力性”的研究“主体”?该文通过推介坂井洋史对不同年代的文本的“探讨”,给出的答案仍然是按照坂井洋史的主张,必须“清理出知识分子在现代性扩张中不自觉的彻底自我否定(忏悔)”,和“主动认同现代性所构筑的外部真理(越界)”!因为只有“清理出”中国知识分子的这种“‘忏悔、越界’的心理”,才能使他们在文学史叙述中,把只讲“唯一的故事”变为把“焦点集中在不同的故事上”。
这里,他们要知识分子“放弃”的“唯一的故事”,就是知识分子通过思想改造,自觉与人民群众打成一片,在共产党领导下建设伟大祖国的政治思想觉悟,就是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只有“放弃”对自己的国家的“唯一的故事”,才能“引导读者把聚焦点集中在不同的故事”和“不同文学史景观”上面!
为了使知识分子放弃讲中国“唯一的故事”,而把“聚焦点集中”在他们反共、反国家、反人民的“不同的故事”和“不同的文学景观”上面,该文再次引用坂井洋史的原话,说“作为文学史研究的主要原则,对于‘内在研究’的执着是防止研究的僵化和意识形态化(或意识形态的图解化)的最有效的手段之一”。他们“通过赛金花由‘毒妇淫妇’,变成‘民间爱国女英雄’正面形象重写”的例子,给中国知识分子出主意:“历史要依靠叙述和文本而被‘物化’,就逃不脱被重写和改造的命运”。这里是说对旧文本的改编和重写,但这种改编和重写,绝不是用篡改、捏造、造谣的手段改变原创作品的政治立场、政治倾向。可是,这位洋大人和我们中国这位推崇者,则是要求中国知识分子“发挥自己的想象力,对文本多样性的解读,培养‘距离感’和‘远近感’,以防止把历史‘抽象化’”。揭穿了说要他们就是要通过发挥“想象力”,通过对文本对“解读,使读者懂得对谁与谁产生“远近感”,归根到底是要通过对文本的“解读”,使读者产生对共产党和人民政府的“距离感”,这就是公开挑拨人民群众与党和政府的关系!反革命的阶级本性暴露无遗、狐狸的尾巴终于露出来了。
四、鼓吹建立“具有真正意义”的中日学者对话,内外结合,达到瓦解“本土”民族精神的目的
该文的结尾只有一个自然段,却单列了一个标题,即《结束语:中日学者对话的可能性》,他写道:“对坂井洋史来说‘老外’研究中国现代文学这种多此一举的行为,其意义就在于从旁观者视觉,冷静地指出中国本土研究者因为缺乏审视被语境规定自我身分的中立性姿态给研究带来的局限,进而奠定中日知识分子理性对话的基础。也只有从这个层面理解坂井洋史的良苦用心,他的中国现代文学研究才具有特殊价值,才更值得我们本土的学者研究和学习。”
该文在给中国知识分子上课:坂井洋史作为日本的一位“旁观者”,都能“冷静指出”“中国本土研究者”,由于“被语境规定的自我身份”的“中立性姿态的局限”,服从、服务于“现政权”的“中立性的错误!这种“旁观者”的深度观察,多么“具有特殊价值”,多么值得中国“本土的学者研究和学习”?
看到了吧?该文作者对板井洋史这位日本“老外”“旁观者”对中国知识分子“多此一举”的“关心”,是何等的感恩戴德!而对“当局者迷”的“中国本土研究者”、中国知识分子又是何等的不屑与轻蔑?这里,无论是日本人学者,还是中国“讲师”,他们这种对中国知识分子“提醒”的“良苦用心”,明明是在利用日本右翼文人的反动言论,煽谋颠覆中国社会主义制度!
多年来,特别是近40多年来,国内外阶级敌人对我国知识分子接受思想改造,拥护、学习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语境规定”,抱着极端仇视的态度,他们把中国知识分子执行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叫做“局限”!在他们看来,只有“中国本土研究者”从这种“局限”中“解放出来”,站到反叛的立场上,才算是“理解坂井洋史的良苦用心”,才是理解了坂井洋史“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的“特殊价值”和“其意义”!
这个结尾、全文总结,完全是重复坂井洋史一贯的腔调,他们最害怕“中国本土”知识分子与中国现代性的“融合”、“同化”;最害怕“中国本土”知识分子抛弃所谓“个体”之“自我丧失”而“融入”国家的“大我”;最害怕他们用中国共产党的意识形态“语境规定”讲中国“唯一的故事”;而只有把“权力暴力”“语境规定”的“唯一的故事”“剔抉”掉,换成他们“不同的故事”、“不同文学史景观”,才能“奠定中日知识分子对话的基础”,活脱一副卖国主义、汉奸文人的嘴脸!
进行中外文化交流,学习、借鉴外国优秀文化,是改革开放的题中应有之义。但如果像坂井洋史和该文所主张的那样,以“剔抉”“排斥”中国“文化自信”、颠覆国家政权来“奠定中日知识分子理性对话的基础”,那就绝不是什么“文化交流”的,而是彻头彻尾的叛国行为!
对于许多中国公民来说,喜欢读中外文学作品,而对于“文学史”研究,可能多数是“门外汉”。但作为中国公民,我们懂得一个最基本道理,就是爱国,就是坚决反对给“鬼子”充当代言人、带路人,这是作为中国人起码的良知,也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重要内容。恰恰是在这个重大的原则问题上,该文突破了起码的民族底线,与坂井洋史穿了“连裆裤”,滑向了卖国主义文化的泥坑。
在上世纪三、四十年代中国人民抗日战争和此后多年来描写抗战文学作品中,人们没少看到歪戴礼帽、腰里挎着“王八盒子”、跟在日本军官的马屁股后面出主意、献殷勤、领着鬼子搜查、杀戮我人民子弟兵和同胞的“胖翻译官”式的人物;今天我们却在中国人评介、吹捧日本人对中国文学史研究的文章中,看见这样为敌对势力文化侵略唱赞歌的“学者”!
注释:
(1)《毛主席语录》第13页
(2)《毛泽东选集》第5卷1977年4月版同上第159页
(3)《社会科学论坛》2013年第10期《“红色文艺”的困境》
(4)《社会科学论坛》2016年第2期《以‘现实主义’解读‘古典主义的趋附与狭隘》
2025年8月2日

微信扫一扫|长按识别,进入读者交流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