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文木:与美国“脱钩”后,谁是我们的敌人,谁是我们的朋友?
学习毛泽东《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

1925年,国民党准备与共产党“脱钩”,依靠国民党已成惯性的陈独秀等一时间不知所措,四处奔走,劝说国民党不要与共产党“脱钩”,理由是没有与共产党合作,国民党也会有较大的损失。与此同时,毛泽东开始考虑在与国民党“脱钩”后,我党需要依靠和团结的力量及其配置问题。为此他写作《中国社会各阶级分析》一文,在该文的开篇处就开宗明义地提出:
谁是我们的敌人?谁是我们的朋友?这个问题是革命的首要问题。中国过去一切革命斗争成效甚少,其基本原因就是因为不能团结真正的朋友,以攻击真正的敌人。
谁会想到,毛泽东在1925年提出的“首要问题”竟在美国准备与中国“脱钩”的2025年再次重演。可以预料,今后我们的斗争如果“成效甚少”,那一定还是“因为不能团结真正的朋友,以攻击真正的敌人。”
那么我们今天真正的敌人是美国吗?既是也不是。
我们今天所说的“美国”一般指的是作为帝国的美国,我们称它为“美帝国”,美帝国的政治核心力量不是白宫而是华尔街。它们是列宁所说的“帝国主义”的政治力量在今天的延续。
另一部分是作为民族的“美国”和作为人民的“美国”,这两个“美国”受着“美帝国”的压迫,因而它们的存在在不同程度上有其合理性,它们与中国的关系既有统一的方面,也有矛盾的方面。我们与“人民的美国”有更多的统一性,比如2024年2月25日在以色列驻美大使馆前的那位为抗议美国支持以色列的政策而自焚美国军人布什内尔,以及参与“占领华尔街”运动的美国人民,就是为“人民的美国”而斗争的。布什内尔在被烧时高喊“解放巴勒斯坦”,这样的诉求就与中国人民的利益有很高的契合度。
对于“民族的美国”,中美间在地缘政治上既有统一的方面,也有矛盾的方面。比如尼克松访华改善中美关系,这是出于中美地缘政治上的统一性,而此前美国对中国的封锁包围,则出于中美间在地缘政治上的矛盾性。但在相当的程度上,“民族的美国”不是中国在新时代的首要敌人;在相当的层面,它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道路上有校多合作面,因而是可以争取与团结的力量。关于这个认识,1966年8月21日,毛泽东在会见赞比亚友人时说:“美帝国主义是我们的对头。我们对美国的了解也是逐步的,就像你们了解英国一样。”
事实上,在毛泽东“三个世界”的语境中,“美国”也是有三分法的。“美帝国”与“美国”是有原则区分的。1961年8月18、19日,毛泽东在杭州会见巴西友人。谈到美国时说:“我说的美国人,指的是美国政府、垄断资本,不是讲美国人民。美国垄断资本不仅对中国人民不友好,对世界各国人民也是不友好的。它不仅压迫社会主义国家,也压迫民族主义国家或争取民族独立的人民。”在谈到中国和巴西的关系时,毛泽东说:“现在障碍只有美帝国主义。”在谈到巴西发展时,毛泽东说:“为什么北美能有一个美国,南美就不能有一个‘美国’,我讲的不是帝国主义,是讲经济、文化上强大的巴西。”1965年11月25日,毛泽东在接见外宾时说:毛泽东说:“我们反对美国帝国主义,只是限于反对帝国主义分子,一定要把美国帝国主义分子同美国人民划分清楚。现在美国人民起来反对他们政府的侵略政策,我们表示高兴,表示欢迎。”
毛泽东一直是将垄断资本统治的美国与人民的美国区别看待的。1965年美国记者爱德加·斯诺与毛泽东谈话结束时说:“请主席向美国人民说几句话,美国人民对中国是有好感的。”毛泽东一针见血地回答说:
祝他们进步。如果我祝他们获得解放,他们有些人可能不大赞成。我就祝那些认识到自己还没有解放的、生活上有困难的人获得解放……美国人需要再解放,这是他们自己的事。不是从英国的统治下解放,而是从垄断资本的统治下解放出来。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美国摆脱欧洲的“跟班”身份,以独立的姿态转入帝国主义形态。在此后的历史中,美国从20世纪初的列宁说的“金融帝国主义”,在20世纪末演化为“高利贷帝国主义”。健康的金融力量将曾是健康、向上和反欧洲压迫的工业化的美国推向世界巅峰,不健康的金融力量又将美国在20世纪末从军工帝国主义推向野蛮堕落的高利贷帝国主义,而21世纪20年代初的蔓延全球新冠肺炎疫情的暴发和随后西方美英等国家默认的基于纯生物学意义的“群体免疫”政策及由此造成的一年中近三百万人因新冠肺炎死亡的惨剧,就是高利贷美帝国主义时代资本主义的没落性即反自然、反人类、反文明性的赤祼祼的表现。正如马克思深刻地指出“高利贷资本有资本的剥削方式,但没有资本的生产方式。”马克思说,这种资本是“洪水期前的资本形式” ,而21世纪初的美国帝国主义就是这种“洪水前期的资本形式”的返祖。
需要说明的是,马克思时代的高利贷多是私人或法人的个体行为,今天的美国的“高利贷帝国主义”与马克思所说的历史上的“商人资本”或“高利贷资本”不同,与20世纪初被列宁称为“高利贷帝国主义”的法国相同,已是一种国家行为。与马克思说的单向贷出的高利贷不同,今天的美帝国的高利贷具有双向剥削特的点,它一方面紧附在作为民族国家的美国身上的国际垄断财团以高利贷的贷入(比如美国国债等)形式剥削美国和高利息贷贷出的形式剥削世界其他国家。
在这样的剥削形式下,目前的“美国”概念中的“美帝国”就是我们中国人民、世界人民以及美国人民的压迫者,因而也是包括中国人民和美国人民在内的世界人民的敌人。而作为美国人民的“美国”则是我们的朋友甚至是《国际歌》语境中的需要联合起来的同一个阶级。而作为民族的“美国”,则与中国可以在反对华尔街统治的“美帝国”的斗争中结成统一战线,在与中华民族的地缘政治(比如在台湾问题上)的矛盾中,又是我们斗争的对象。总之,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并不排斥美利坚民族的伟大复兴,因为美利坚民族的伟大复兴的前提与中华民族复兴的前提一样,是华尔街大亨(国际垄断资本)为政治核心“美帝国主义”退出历史舞台。届时美国还在,正如英帝国已退出历史,英国还在一样。
“9·11”事件和各式“占领华尔街”运动表明,今天世界的南北矛盾已激化,与列宁时代相比,今天的“压迫民族”内部也已严重分化,民族压迫已不局限于南方国家,它正在加速向北方国家蔓延;准确地说,新时代中国外交的主要对手已不是一般的民族资本主义,而是带有垄断资本特点的“金融帝国主义”。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我们要用毛泽东“三个世界”的理论认识新时代面临的国际形势,用列宁“帝国主义”的理论将作为垄断资本的大本营的“美帝国”与作为民族国家的“美国”区分开来,以认清新时代中国外交面对的真正的敌人。新时代,我们的外交还应当遵守“利用矛盾,争取多数,反对少数,各个击破”和“有理,有利,有节”的策略。只有如此,我们才能避免“在林林总总、纷纭多变的国际乱象中迷失方向、舍本逐末”,以至出现“行百里者半九十”的失误;只有如此,我们才能制定出一条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的,因而是科学的外交路线。毛泽东在《中国社会各阶级分析》全篇结束时的策略思想可作为当前中美斗争时的指导思想:
综上所述,可知一切勾结帝国主义的军阀、官僚、买办阶级、大地主阶级以及附属于他们的一部分反动知识界,是我们的敌人。工业无产阶级是我们革命的领导力量。一切半无产阶级、小资产阶级,是我们最接近的朋友。那动摇不定的中产阶级,其右翼可能是我们的敌人,其左翼可能是我们的朋友——但我们要时常提防他们,不要让他们扰乱了我们的阵线。
如果将毛泽东同志的策略用于当下的中美斗争,我们就可以这样表述:
一切勾结以华尔街为代表的国际垄断资本集团的帝国主义的官僚买办势力以及附属于他们的一部分反动知识界,是我们的敌人。中国及一切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国家和人民是当前世界进步力量。美国的一切半无产阶级、小资产阶级,以及实体经济尤其是用于民生的实体资本家是我们最接近的朋友。那动摇不定的美国中产阶级,其右翼可能是我们的敌人,其左翼可能是我们的朋友——但我们要时常提防他们,不要让他们扰乱了我们的阵线。
总之,在反对“美帝国”的斗争中,“民族的美国”是我们可以争取的伙伴,“人民的美国”是我们政治上的朋友。在与民族的美国矛盾中,人民的美国是我们的可以团结的朋友,我们也是美国人民“从垄断资本的统治下解放出来”的正义斗争的坚定支持者。
如果不是采用这样策略,我们就会“‘为渊驱鱼,为丛驱雀’,把‘千千万万’和‘浩浩荡荡’都赶到敌人那一边去,只博得敌人的喝采”,将本不愿紧跟华尔街统治的“美帝国”美国人民群众推向我们的敌人,使我们面临的形势更为困难。
与1927年在前国共合作中的在左翼和右翼间摇摆并最终投入右翼阵营的蒋介石一样,今天的特朗普为美国的国家利益与华尔街产生了冲突,其焦点是要一个工业化的美国还是金融——实则是高利贷——化的美国。在这方面我们在警惕特朗谱右翼化的同时,应当选择性地支持特朗谱振兴美国国内实体经济的政策并为此反对华尔街的斗争;在支持特朗普振兴国内实体经济的政策中,偏重支持其有利于长期和平发展的民生实体经济、警惕和反对其强化实体经济中不利世界和平发展的军工经济的路线,团结美国一切爱好和平的人士摆脱早在20世纪50年代美国总统艾森豪威尔警告过的“军工复合体”操纵美国的努力,最终还美国人民一个基于“共同富裕”原则的日益接近“自由人联合体”理想的美国,并以此推进马克思在《共产党宣言》预见的“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以实现共产主义伟大理想的“人类文明新形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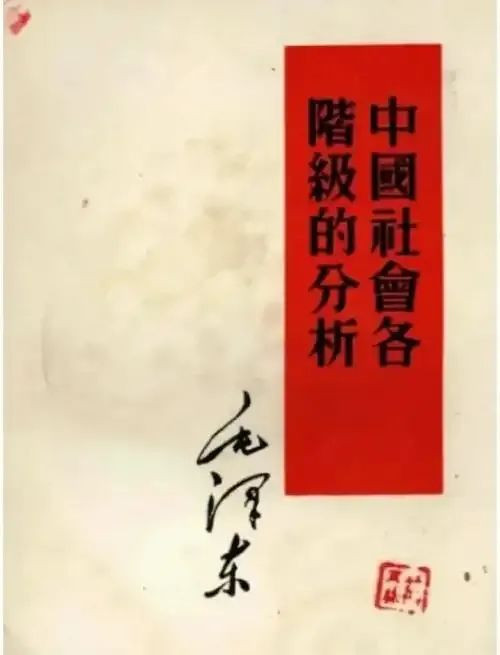

微信扫一扫|长按识别,进入读者交流群

|
|
|
|
|
|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