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树华:慈善掩护下的毒酒:索罗斯与俄罗斯私有化

当今世界,“全球化”的程度愈来愈高。伴随者经济“全球化”的步伐,世界各国包括发达国家与后进地区之间的联系也愈显密切。“全球化”趋势的加强,各国各民族之间的多样性也愈发明显。这些表现出来的多姿多彩有时也体现在对某一事件、某一行为的评价上。一个人在某些国家本是人人羡慕的成功明星,而在另些国家,则可能被视为盗贼兼恶徒。近些年国际金融市场上赫赫有名的投机资本家——乔治·索罗斯正是这类人物。
7英镑的工资和未圆的哲学家之梦
1997年,东南亚各国先后出现货币危机,引起国际社会的强烈关注。美国头号国际金融投机家索罗斯,被马来西亚总理马哈蒂尔三度公开责骂为“罪魁祸首”。由于马哈蒂尔的公开点名叫阵,1997年间,索罗斯已成了媒体上评价呈正负两极的名人。然而索罗斯在包括俄罗斯在内的东欧国家却声名显赫,一派慈善家的形象。索罗斯到底是何许人也?近些年,他在俄罗斯及东欧国家都作了些什么?
1930年,乔治·索罗斯出生于匈牙利布达佩斯的一个犹太人家庭。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夕,为了逃避德国纳粹分子的迫害,而随全家迁至英伦三岛。而后进入“伦敦经济学院”攻读哲学。毕业后,苦于没有工作,只好充当百货推销员。后来,他又到一家小银行工作一段时间。稍后利用犹太人之间的渊源,他结识了一位名叫陶布的犹太商人。当时陶布正在有若“欧洲最大银行家”之称的“罗斯柴尔德家族”里负责投资事务。年轻的乔治·索罗斯从陶布身上学到了各种金钱游戏的手法。不过,那时索罗斯的工资每周只有7个英镑。
1956年,索罗斯离开英国到美国纽约。身上带着一本他写的哲学手稿《意识的负担》。他想要用这本书敲开出版社或大学哲学系的大门。但无奈却找不到愿意出书的出版社,当然也无法到大学教哲学。于是他遂放弃哲学,不再恋心学问,改业为投资理财。
用头脑和智慧铸造金融“无敌战舰”
从60年代中期开始,他建立了一家名为“量子期货基金”的海外基金会。为了方便基金会的顾客减税节税,索罗斯将基金会的注册地点选在委内瑞拉的一个度假小岛——库拉索。索罗斯的投资本领确实高人一筹,若1969年一个人投资他10万美元,通过基金会的炒作,到了1995年已能够累增到1300万美元。
在金融市场上,索罗斯赚钱的格言是“逆向思维、不相信人情”。索罗斯指出,证券和货币交易中往往是“感情用事”,金融领域最“缺乏理智”。金融市场的混乱无章和无政府状态使索罗斯聚敛了大笔的财富。然而令人不解的是,他竟然呼吁各国政府整顿秩序,以避免类似他这样的投机家“钻空子”。
1992年,索罗斯抓住英镑对美元和德国马克的不合理的比价,出击炒作英镑。他以百亿美元的财力,硬是将英镑压得崩盘。而后,英镑不得不被迫贬值12%,并宣布退出欧洲货币区。而狙击手——索罗斯则全面胜利,在一个月的时间里,至少获得了10至15亿美元的投机利润。1992年的9月16日因此被称为“黑色的星期三”,而索罗斯也就有了“国家金融坏孩子”的绰号。
1994至1995年墨西哥金融形势动荡,“比索”出现危机。索罗斯当机立断,不失时机。他一次炒作,又赚进了10亿美元以上。
索罗斯写过一本书,名为《金融炼金术》。书中最核心的观念是,金融市场乃是一个不理性的市场,永远会做出“过度反应”。而这个“过度反应”的空间,也就是国际大腕投机者得以纵横赢利的场所。而他用自己的成功证明了这点。索罗斯有美国政府的支持,有国际金融资本集团的相互传递消息和协同炒作,因此每当他下决心对某一国货币进行“出击”时,决不可能轻易空手而归。
1997年7月中旬起,泰国、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菲律宾等国的货币对美元的比价短时间里狂跌。比价不合理,加上经济结构的脆弱,给金融投机提供了绝好的机会。索罗斯不失时机,策划并参与。据估算,此次索罗斯一行又没有空手而归,又有50亿-100亿美元的进项。
不过,索罗斯在英镑、比索、泰铢这片金融大海里充当“金融海盗”,而在东欧则扮演“开明慈善家”。
金融游鳄的外交游戏与政治投资
索罗斯在1990年之前,活动的范围只限于各种投资事务上,对其他事情则采取低姿态。但1989和1990年间出现“苏东国家剧变风波”。结果苏联瓦解,而东欧国家则脱离苏联的束缚,开始痛苦的道路选择。此时起,是思乡的情缘,还是在追逐理想?总之,索罗斯不时地将视野转向大西洋彼岸的前苏东国家。挟带着巨大的财势,或慈善布施,或出资赞助,或幕后策划,或……
索罗斯在美国对俄以及对前东欧国家的外交上,扮演了差不多和政府一样的角色。实际上,索罗斯与美国政府早就配合默契。索罗斯参与美国内政,开始他大力支持克林顿参加大选。在克林顿当选后,他即以个人财力,倾力配合美国的外交政策,也同时宣传、推广自己的社会理念。
美国原副国务卿塔尔博特说到:“克林顿政府将索罗斯视为一项国家的资源和宝藏”;“我和索罗斯的合作,有如和一个友好的独立盟邦合作。我们和德、法、英,再加上索罗斯,对前共产党国家展开同步的工作。”
90年代初期,索罗斯以自己的大名设立了一个基金会。于是,在索罗斯的金融帝国里,除了有“量子期货基金”外,又出现了另外两个有着政治色彩的组织,一个是“索罗斯基金会”,另一个是“开放社会研究所”。主要面向世界上一些正在走向“民主”的国家。而对于原苏联和东欧国家,“基金会”的宗旨是通过对人文、科技界的赞助,促进上述国家走向索罗斯所崇尚的“开放社会”。
几年的时间里,“索罗斯基金会”对前苏东地区国家大量捐款,陆续捐赠的金额总数达6亿美元以上。覆盖了西起中东欧的捷克、波兰、匈牙利、马其顿,东至中亚地区的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等国家。俄罗斯、乌克兰等也包括在内。仅在俄罗斯,“索罗斯基金会”先后出资达3亿美元之巨。除此之外,索罗斯还积极利用自己的影响,想近办法帮助年轻的“民主国家”。例如,乌克兰向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申请贷款,索罗斯亲自出马,广泛动员游说,最后,乌克兰获得了这笔40亿美元的贷款。索罗斯积极活动主要目的是防止这些国家重回俄罗斯的怀抱。
为什么索罗斯突然钟情起“善事”来了呢?美国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会主席阿布拉维茨说过:“索罗斯是美国惟一有自己外交政策的个人,并且他有能力去执行和推行。”很多年来,索罗斯对东欧国家所作所为,是在帮助美国做政府想做而不能做的工作。
索罗斯的这种角色,让人联想到他的投资祖师“罗斯柴尔德家族”。这个家族原来乃是来自法兰克福的犹太银行世家。早年英法争霸欧洲,拿破仑企图封锁英国。罗斯柴尔德家族动员一切力量,甚至贿赂法军,进行海上走私,因而突破了法军的封锁,促使英国得以打败法国。而后,苏伊士运河的开凿,也由他们家出面聚资。他们家族对英国的效忠,得到的即是永远的回馈。大商人玩的是国家级的政治,索罗斯玩的就是这样的游戏。
这样的游戏,需要大量的金钱用来运作。然而对于90年代的索罗斯来说,却无匮乏之虞。
也正因为如此纵横四海,因此索罗斯遂在一次访谈中说:“我有一种当超人的感觉。”他说:“我以前只是纽约的一个小人物,现在心理才觉得比较平衡。”
人们不知索罗斯所说的是什么样的一种“心理平衡”,是“狂赚之后的酣畅”,还是有钱又找回了年轻时“哲学梦想”?索罗斯——这位西方世界中的金融家、“坏孩子”,在东欧,却变成了“慈善家”和“救世主”。
投资者、慈善家?
在俄罗斯,苏联的解体,经济的倒退,使得过去计划体制下“悠哉悠哉”的科学文化工作者陷入了极其困难的境地。国家对科研的拨款不足,科研经费入不敷出,大批科研人员无用武之地。科技人员收入菲薄,且工资被拖欠严重。一些研究所和学校连续几个月不发工资。许多院所面临着“关、停、转”的悲惨命运。仅1992年就有4500多高级科学家离开俄罗斯,移居西方国家。1993年人才流失的现象更加严重,不少俄罗斯科技界的精英前去美国、德国和以色列,外流人数占科研人员总数的25%。
文化教育的境遇也是如此。经费短缺,惨淡经营。
正在此时,救星到了。索罗斯向美国政府进言,500美金就能解救一名原苏联科学家。与其让这些“冷战”时期的科研精英苦苦挣扎,不如救人一命,使其为美国、为人类服务。特别是,要防止那些掌握核技术的专家被“危险国家”买走。
索罗斯说到做到。年轻时没能圆自己的“哲学之梦”,现在则以救世主的身份解救大批处于危难之中的哲学家、学问家。
短时间里,“索罗斯基金会”在原苏联大地遍地开花。基金会出资赞助俄罗斯学校教科书的出版。重新编写教科书,给年轻的一代以全新的知识,使他们树立“开放社会”的观念。据统计,基金会赞助出版的新教科书达1000多种。先后有几万名俄罗斯科研工作者接受了“索罗斯基金会”的美元资助。
在其他原苏联势力范围国家,“索罗斯基金会”更是畅行无阻。“索罗斯基金会”的影响日益增强,美国的思想和观念得以传播。进行着哲学思索的索罗斯拆卸着“意识形态的负担”,完成着自己“开放社会”的构想。此时,仍像在狙击金融市场上一样,他依旧沉着且不露声色。然而既是这样,也终究引起了俄罗斯国家安全机构的警觉。
还是俄罗斯原外长普里马科夫领导反间谍总署期间,俄罗斯情报机构已经开始注意“索罗斯基金会”在各地的活动情况。后来形成了一篇长长的秘密报告,报告中称,“索罗斯基金会”渗入俄罗斯科研机构,赞助一些研究课题,吸引研究力量,为某外国服务。在人文社会科学界,该基金会推行“有选择”的资助,扶持亲西方的自由流派,研究课题具有鲜明的意识形态色彩。报告最后还向俄罗斯杜会各界发出警告,呼吁人们注意“基金会”后面的“背景”。然而类似的警告根本无济于事。有的泰然处之,也有的认为这只不过是“克格勃式的虚张声势”而已。
就在俄罗斯安全部门发出对“索罗斯基金会”指责的同时,索罗斯正从俄罗斯的远东地区出发,乘坐“东方列车”,一面检查各地“基金会”的工作,一面在俄罗斯广袤的大地上巡视、畅想。
多年来,索罗斯一直向世人宣称,当今的俄罗斯是“最野蛮、原始的资本主义”。1997年8月,索罗斯在莫斯科接受了俄罗斯《生意人周刊》记者的独家专访。谈话之初,索罗斯称,在俄罗斯,他一直遇到一个令自己头疼的问题——不知怎样处理“行善”和“赚钱”两者的关系。
1997年7月,随着俄罗斯大型国有企业“电信投资”股份拍卖的捶声落定,索罗斯“慈善家”的面目又变成了地道的“商人”模样。“电信投资”25%的股份拍卖成交总额为l8亿美元。这样巨额的投标将其他竞争对手打得一败涂地。俄罗斯社会惊愕之余,又发现了索罗斯的“背影”。18亿美元的巨资,10亿正是出自索罗斯之手。
同时,索罗斯也承认,除去无偿的资助外,他和他的同事们先后在俄罗斯共投资近20亿美元,主要用于购买俄罗斯政府发行的债券,也有一部分投到股票市场。“以钱生钱”一贯是索罗斯的生意准则,投资生产领域不是他的兴趣所在。
索罗斯相信,这10亿美元自他出手的那一天起,就已升值。他投资的“电信投资”公司,乃是俄罗斯私有化5年以来最大的一桩拍卖案。俄罗斯“电信投资”公司是俄罗斯通信产业的“龙头”,控制着俄罗斯广播电视节目的信号转播。与索罗斯有关的人士透露,经过组合后的“电信投资”公司,市场价格将上扬5倍。
然而,由于“电信投资”公司是私有化过程中的一块“肥肉”。在这次私有化竞拍过程中,索罗斯的主要合作伙伴是近几年俄罗斯金融资本界的“黑马”——“联合进出口银行”(即“奥奈克西姆银行”)。
众所周知,该银行的总裁是波塔宁。在叶利钦第二次当选总统后,曾一度出任政府副总理。以“联合进出口银行”为主的财团与俄罗斯主管私有化的主要官员往来密切。不知是聪明过人的索罗斯先生选中了对象,还是俄罗斯财团实力不济而求到索罗斯“门上”。总之,钱、权、关系结合,注定了这一方必胜无疑。索罗斯和他的合作伙伴的胜利引起了竞争对手的强烈不满。
过不多久,东窗事发。10月和11月份先后两次揭露出俄罗斯主管私有化的政府高官,借写书之名,收受贿赂。接着,俄罗斯政府多名部级以上的私有化官员因“稿费丑闻”而被解职。其中每人高达9万美元的稿酬便是出自“电信投资”竞标获胜一方。而后接连不断的丑闻暴露,给这桩俄罗斯私有化历史上最大的国有企业股份拍卖案蒙上了阴影。“慈善家”、“金融家”乔治·索罗斯先生也因此在俄罗斯舆论面前显得不甚光彩。
按约定,索罗斯掌握的俄罗斯“电信投资”公司的股份两年后才能出手或转让。对手指责索罗斯只会顾及短期的收益,炒卖“电信投资”公司,而不会关心公司的长远利益。面对来自对手的批评,索罗斯的回答干脆而简单,吃不到葡萄说葡萄酸。
正像对待马来西亚总理马哈蒂尔的指责一样,索罗斯从不作更多的解释。而是全神贯注,屏注呼吸,以敏锐的目光巡视着下一个“猎物”。在俄罗斯,索罗斯已经看好了即将付诸拍卖的国有大型企业——“俄罗斯石油”公司。索罗斯通过媒体,向俄罗斯政府发出信息,若将“俄罗斯石油”公司公开透明地拍卖,他愿拿出10亿美元,以帮助俄罗斯政府解燃眉之急——补发拖欠的工资。
下一次,索罗斯是否能再次得手?舆论认为,将来大概不是决定于索罗斯,而是更多地取决于各国政府,取决于政治家的计划和决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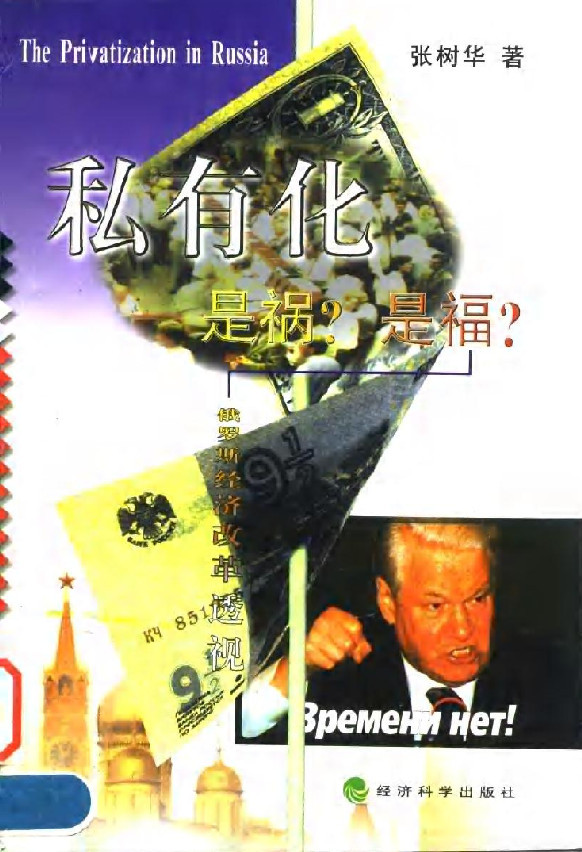
(本文原载张树华著、济科学出版社1998年11月出版的《私有化,是祸?是福?——俄罗斯经济改革透视》一书。)

微信扫一扫|长按识别,进入读者交流群

|
|
|
|
|
|
|
|



